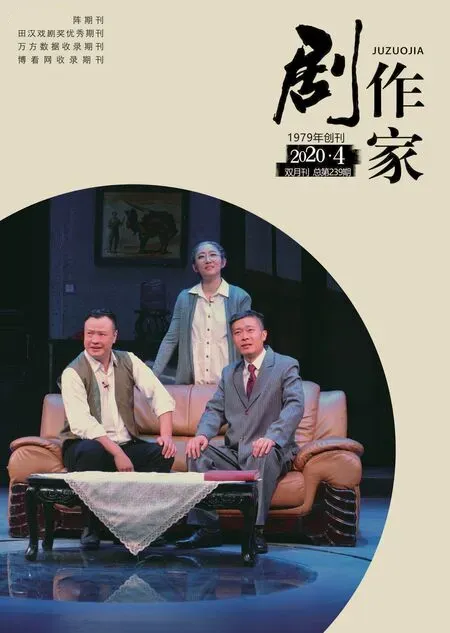傳 統 與 創 新
——關于泗州戲作曲與演奏雙修的思考
■ 張峻峰
安徽地方劇種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有徽劇、黃梅戲、廬劇、泗州戲,簡稱:徽黃廬泗。泗州戲是安徽省四大劇種之一,又名拉魂腔,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泗州戲的唱腔委婉動聽,悠揚高亢,為淮河流域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
蚌埠市的安徽省泗州戲劇院是個歷史悠久、人才輩出的劇院。早在五十年代,院里主演李寶琴、霍桂霞等老一代藝術家們就譽滿大江南北淮河兩岸,曾代表安徽省三次進京到中南海懷仁堂為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及中央多位領導人進行專場演出。
像演員一樣,我把自己“歸門歸檔”為泗州戲的柳琴(主胡)演奏。我少年從藝,跟隨父親學習柳琴演奏,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父親的嚴格訓教,讓我在柳琴演奏這圈子內暫露頭角。進入劇院時幾乎所有的泗州戲傳統音樂都能爛熟于心,不但能嫻熟地彈奏老一輩藝術家李寶琴、霍桂霞等的唱腔,而且分得清每位老藝術家的演唱特色與技巧。可以這樣說,我是在泗州戲的傳統音樂里泡大的。從任何一個方面來講,我都是泗州戲音樂老傳統的繼承者和守衛者。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加強現實題材創作,要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讓泗州戲綻放出新時代的光彩,是我們這一代泗州戲人的責任。安徽省這些年緊抓機遇,乘勢而上,我們蚌埠也緊跟時代步伐大抓狠抓戲劇創作,特別是現代題材的戲劇創作。五年來,除小型戲曲外,劇院共排練演出了五本大戲。我這個本想一輩子當好柳琴伴奏演奏員的人誤打誤撞地走到作曲隊伍里來,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創作劇目的作曲。
作曲與演奏本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行當,本人如今從一個傳統的繼承者、守衛者轉身而變成作曲——改革者、創新者。
其實,傳統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進程,今天我們所認定的傳統換個角度來說就是昨天的創新,昨天的創新就是我們今天的傳統。由此可見,傳統與創新是辯證的對立統一,是事物的一個發展過程。如果傳統一成不變,沒有創新的延長和彌補,抱殘守缺,固步自封,傳統就會中止;而創新離開了傳統這個根本,也必定會迷惑甚至變種,胎死腹中。我從一個泗州戲主弦伴奏到泗州戲的唱腔設計,在專業雙修的歷程中,始終把傳統與創新的基點把握作為我的最高藝術追求。
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曾說:“中國人最關切的是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繼續和統一。”我們要繼承傳統,要在創新的基礎上繼承;要跟進時代的步伐,要有創新,但一定要在傳統的基因里創新,不變種。前些年有個笑話:有人拿一段唱腔給常香玉先生聽,常香玉先生聽完以后,一疊連聲說了幾個好聽好聽。就在大家如釋重負之際,常香玉先生問道:這是哪個劇種的聲腔。這一問,現場氣氛的尷尬可想而知。常香玉是豫劇的開創者之一,是四海揚名的聲腔大師,卻聽不出劇種特色,只說好聽不知道劇種。這雖然說的是一段小笑話,但是這段笑話警醒我們的從業者,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線,不能不講規矩地逾越傳統與創新的辯證關系,生產出許多“四不像”的作品。
2015 年我們泗州戲劇院創作演出的泗州戲《綠皮火車》進京,首演于北京長安大戲院,參加了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會演。泗州戲第一次進京還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事,時隔六十年,泗州戲又一次進京,雖然是一次藝術活動,但更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任務。前幾屆都是黃梅戲,這一次我們泗州戲覓得戰機,代表的是安徽省。我是全劇主弦又是作曲,心頭的壓力可想而知。人往往都是這樣,沒有退路時,壓力就是動力。
為泗州戲《綠皮火車》作曲與給傳統戲編曲不同。圈內人都知道,雖然說泗州戲有著兩百多年的歷史,但泗州戲不像京劇那樣的博大精深、自成體系。泗州戲在一百年之前還是個說唱形式,連正規的樂隊伴奏都沒有形成,更談不上什么作曲了。再說,后來漸漸形成了本戲,也是小打小鬧。直到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后,泗州戲才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即使到今天我們傳統戲的故事都是單線條的,唱詞也都是套路,方便流動演出,演出時做套路放水詞,不是七字句頭就是十字句頭。而《綠皮火車》的劇本結構顯然是現代產物了,首先在文本結構上就不同于傳統戲,它是雙線結構,十分講究烘托場面場景,人物性格、人物情緒,有著大段大段唱腔,還有不少對唱、群唱、合唱及邊舞邊唱。這些在傳統戲中是不曾有過的。最令我頭痛的是編劇寫的唱詞多是不規則的長短句,上句下句不一樣,有的上句五個字,下句十幾個字;有的上句十幾個字,下句四五個字。按照傳統的泗州戲音樂曲牌根本就套不上去,想去與編劇交流溝通要編劇對唱詞進行改動,編劇找出一萬個理由婉言拒絕。在茫然與陣痛中我必須自創一條新路,這條新路是不忘傳統,又必須讓傳統在此處有所突破,而突破的過程又必須堅守泗州戲的“移步不換形”,寫出來的曲子不能讓別人說好聽是好聽就是不像泗州戲。吃力不討好事小,萬一進京演出打不響,辜負了各級領導的信任,丟了泗州戲拉魂腔臉面,那真就是萬死莫贖了。
我在創作中除最大量使用泗州戲的傳統音樂曲牌之外,還將花鼓燈音樂當作一抹悅耳的色塊用來加強淮河流域的文化特色。幕未打開,泗州戲的旋律融匯著花鼓燈的背景音樂一下就會把人帶入淮河兩岸,體會到那一方水土的風土人情。在創作中找到感覺,寫出旋律,自己彈出來,再唱出來,一彈一唱,熟悉了自己寫出來的旋律,加上自己的主弦彈奏與作曲家在鋼琴上“試譜”,傳統質感兼具,這樣更方便我的反復修改,也可以說這是作曲與伴奏雙修的互惠互利,真的是“近水樓臺先得月”了。
現在想起來作曲與寫文章是一樣的道理,許多有建樹的名家都說過好文章都是一遍一遍改出來的。通過泗州戲《綠皮火車》的創作,我對這句話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反復地彈,反復地唱,廣泛地征求編劇、導演、演員的意見,有時候編劇導演不在一起,我會用微信把自己試唱的錄音發給他們,盡我所能做到極致。
《綠皮火車》所到之處,觀眾對音樂高度認同,紛紛贊譽泗州戲好聽,是對我最大的慰藉。
《綠皮火車》最后獲得了第五屆少數民族會演銀獎,網絡評選入選最受歡迎的十大劇目之一,還獲得了中國人口文化獎和安徽省“五個一工程獎”,2019 年代表安徽省參加了在西安舉辦的第五屆國際藝術節,并獲得特別貢獻獎。2019 年,本人由省文化廳推薦到北京參加了文旅部舉辦的“千人計劃”培訓班作曲班,進一步開拓了眼界。通過泗州戲《綠皮火車》的成功上演,我對泗州戲的作曲和伴奏提高了認識。戲曲要講究一棵菜精神,個人技巧要服務于全劇這個大局。
從主弦伴奏到泗州戲作曲,從看著曲譜演奏到自己演奏自己創作的曲子,付出的心血不一般,心里的感覺也不一樣。以前是作曲者寫好樂譜,上面什么樣的音符,什么旋律,我們只要看著指揮手勢(節奏)伴奏,伴奏任務完成,收拾“家伙”回家。作曲就不一樣了,最早進入主創班子,第一個要直接打交道的是編劇。拿到劇本不但要反復閱讀,而且得反復斟酌研究,情景音樂描寫、唱腔設計,先得在心里打成腹稿,再與編劇進行溝通,尤其是主要人物的音樂形象塑造、性格刻畫等等。正如著名編劇汪曾祺先生所言,編劇的語言節奏決定于情緒的節奏。語言的節奏是外部的,情緒的節奏是內部的。二者同時生長,而又互相推動。情緒節奏和語言節奏應該一致,要做到表里如一,契合無間。作曲不懂編劇的良苦用心,必然會自作聰明刪改劇本唱詞,這是編劇與作曲之間的大忌。我在為《綠皮火車》一劇作曲時做到了每改文本一個字需與編劇進行溝通交流,凡編劇不同意修改的,就自我消化。
在個人技巧服務于全劇大局的創作流程中,必須做到成竹在胸。圈子內有一句行話,戲曲戲曲,沒有曲子就沒有戲,可見一部戲的成功,曲子(當然包含唱腔)是何等重要。
后來在泗州戲《夙愿》《淮水情》等大戲的創作中,由于有了《綠皮火車》的創作經驗,便從容成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