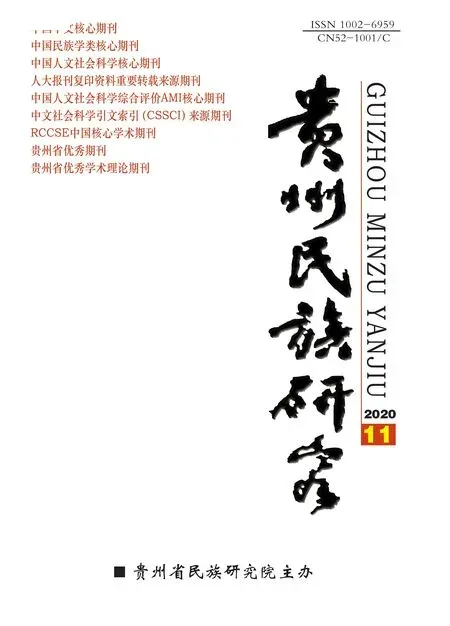百川歸海:百越文化融匯于中華文化的歷史圖景
李富強 衛彥雄 呂 潔
(1. 廣西民族大學 民族研究中心,廣西·南寧 530006;2. 廣西民族大學 東南亞語言文化學院,廣西·南寧 530006)
越人是中國上古時期至漢代活動于中國南方的一個土著族群。“越”作為一個族稱,大概始于商周時期。《逸周書·卷七·王會解》:“東越海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遇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其人玄貝,海陽大蟹……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鱉。其西魚復,鼓鍾,鍾牛。蠻楊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余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眾皆北向”。“伊尹受命,于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十蠻、越漚,剪發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其中有“東越”和“越漚”之族稱。 《竹書紀年》: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019年) “于越來賓”。其中有“于越”之族稱。
將越人稱為“百越”,大概始于戰國時期,《呂氏春秋·恃君覽》:“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此后,《漢書·地理志》載:“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不僅記錄了“百越”的分布狀況: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而且說明了稱為“百越”的原因: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根據史籍記載,這些“各有種姓”的百越族群大致包括了“句吳”“于越”“東甌”“西甌”“閩越”“南越”“駱越”“滇越”“山越”等不同支系,它們都先后建立了割據于中原王朝之外的“王國”文明。
東漢之后,越人逐漸少見于史籍記載,盡管在閩、浙、皖、贛之交仍有稱為“山越”之人,但卻是比較零星、分散的人群了。總的來說,百越族群或逐漸消融于華夏-漢族之中,或在與華夏漢族的互動中逐漸演變為壯侗語民族。不論是演變為漢族,還是演變為壯侗語民族,其后裔都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百越文化也融匯于中華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猶如《淮南子·氾論訓》所云:“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這是百越民族文化的一個歷史圖景,也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史的一個片斷和側影。
一、百川異源:百越文化是發源和成長于中國南方的獨特文化
“百越”族群支系繁多,各有地望。據老一輩學者羅香林考證,百越各支分布如下[1](P39-100):
于越,初以會稽為中心,及勾踐初年,北起今浙江崇德,東至浙江定海,南達閩浙交界,西及鄱陽湖東岸。
甌越(亦稱東甌),以今浙江南部之甌江流域為中心。
閩越,以今閩江流域為中心,東及今臺灣澎湖列島,西達贛東北。
揚越,今漢水流域。
南越,東及閩越地,南盡海南島等地,西達廣西、越南,北至衡陽。
西甌,今廣西柳江以東,湖南衡陽西南,下至蒼梧封川,北達黔桂界上。
駱越,東自廣西南寧西南,下及廣東雷州半島及海南島,達越南東北部和中部。
滇越,今云南滇池一帶。
羅香林對于百越的考證和研究,一直被學術界奉為經典。現在學術界對于百越各支系分布地的觀點大多與羅香林的觀點大同小異。如按照胡紹華的觀點,百越各支系分布如下:
句吳,大致分布在今蘇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帶地區;
于越,大致分布在今浙江的杭嘉湖平原一帶、寧紹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帶;
東甌,大致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甌江流域;
閩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省及贛東部分地區;
南越,主要分布在今廣東省及廣西部分地區;
西甌,大致分布在今廣西桂江流域河西江中游一帶;
駱越,大致分布在今廣西左江流域、海南省和越南紅河三角洲一帶;
滇越,分布在今云南省西南部地區及緬甸北部地區[2](P292-293)。
“各有種姓”的“百越”雖然各支系的文化各有差異,但亦有共同特征,自成體系。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羅香林歸納為:“擅于制造和使用鉞和銅劍、善于制作舟楫和行舟、精于制造和使用銅鼓、好紋身習俗。”[1](P127-156)
林惠祥概括為:“斷發文身、契臂、食異物、巢居、語言、使舟及水戰、銅器。”[3](P112-115)
凌純聲總結為:“祖先崇拜、家譜、洗骨葬、銅鼓、干欄、龍船、鑿齒、文身、食人與獵首、洪水傳說。”[4](P389-408)
陳國強等人歸納為以下特征:“水稻種植、喜食蛇蛤等小動物、發達的葛麻紡織業、大量使用石錛,有段石錛和有肩石器、有極其精良的鑄劍術、善于用舟,習于水戰、營住干欄房屋、大量燒用幾何印紋陶器和原始瓷器、操鮮明特點的語言、流行斷發文身及拔牙風俗、留有濃厚的原始婚俗、崇拜鬼神、迷信雞卜、實行崖葬、崇拜蛇、鳥圖騰。”[5](P32-70)
胡紹華歸納為:“相同的語言——越語,共同的農耕經濟生活——稻作農業,共同的宗教信仰——崇拜鬼神、迷信雞卜,相同的生活方式,文身斷發習俗,不落夫家習俗,打牙習俗,行船棺葬及懸棺習俗,使用銅鼓的共同習俗。”[2](P293-297)
吳春明則歸納為:“擁有海洋人文的價值取向——舟楫,特殊的聚落形態——干欄居和洞居,特殊而多樣的喪葬形式,特殊多樣的裝飾藝術,復雜的自然崇拜,廣譜的經濟活動以及南島底層方言系統。”[6](P79-86)
還有不少學者對百越文化的特點做過歸納和闡述。盡管觀點不盡一致,但大多認為,百越文化既有多樣性,也有統一性,百越文化自成系統,是一種迥異于中原華夏文化的獨特的文化體系。
獨特的百越文化是中國南方的土著文化。盡管《史記》 《尚書》 《淮南子》 《越絕書》 《吳越春秋》等中國古籍常將越人的根源追溯到大禹,謂之為“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7],相當一些老一輩學者如羅香林等也據此認為“越族源出于夏民族”[1](P1-8),但隨著資料的積累和研究視野的拓展與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這種觀點不過是由根深蒂固的華夏—漢人中心主義立場帶來的偏見和誤解。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曾騏就曾將百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與百越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從而認定這些新石器時代文化為“先越文化”[8]。現如今,考古發現,在中國南方和中南半島,新石器時代曾廣泛存在以幾何印紋陶和有肩石器、有段石錛共存的眾多遺址,這些遺址的遺物遺跡透露出其主人的許多文化特征,如干欄建筑、善于用舟、稻作農業、斷發紋身、鑿齒拔牙、蛇崇拜、懸棺葬或崖洞葬等,這些正是百越人獨有的文化特征。日益豐富的證據表明,百越族群實際上就是由當地史前人類演變而來,百越文化就是當地土著文化。從“先越文化”到“百越文化”、從“先越民族”到“百越民族”,其間無論從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考察,都有一個繼承、發展和變化的過程[9](P10)。
二、百川朝海:百越文化融匯于中華文化的歷史寫照
漢代焦贛《易林·謙之無妄》 云:“百川朝海,流行不止,道雖遼遠,無不到者。”這正是百越文化融匯于中華文化歷史過程的寫照。
百越文化融匯于中華文化是“先越文化”與中原華夏文化交流的繼續。據有關學者研究,東南沿海史前文化序列中即有中原北方的文化因素傳入與融合。舊、中石器時代,有細、小石器工業群的介入;新石器時代,來自北方的新石器、早期青銅文化的影響接踵而至,尤其是龍山文化和夏商文化的強勁影響,盡管從整體上來說,這類影響只是局部的和短暫的,沒有形成擴展和持續之勢,沒有改變這一地區新石器文化的土著傳統,具有鮮明本土傳統的器群組合仍是東南新石器文化的主流[6](P273-290)。而自新石器時代之后,中原北方文化影響南方的勢頭持續加強。夏商時期是以華夏族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形成與初步發展的關鍵時期,夏商王朝將青銅文化傳播、影響到南方。兩周時期,中原華夏文明傳播和影響到了整個南方地區。
中原華夏文明與百越文化的交流可能自東而西有早晚強弱的不同。東部的“句吳”“于越”等融匯于華夏的步伐最快。從考古發現來看,太湖至寧紹平原的湖熟文化、馬橋文化、高祭臺類型和贛鄱流域的吳城文化和萬年類型,都表現出濃厚的夏商青銅文化特征。可見,在龍山文化深刻影響的基礎上,東南北部的湖網平原地區的土著文化已經受到夏商青銅文化的深刻影響,表現出初步的“華夏化”態勢[6](P345)。西周時期,華夏族群可能已經成規模地遷徙到了江南湖網平原地區。《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季歷賢,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立為吳太伯。”[7]這一記載可能反映了華夏族群遷徙至東南北部的事實。與之相印證的是,在從蘇皖南至浙贛地帶的吳、越土墩墓文化中,中原華夏文化因素多見,如繩紋陶系的鼎、袋足甗、鬲和青銅禮器類的鼎、鬲、簋、尊、卣、盤及成套的青銅兵器等,代表中原華夏文化的器物成套出現。由于“句吳”在“于越”之北,其與華夏交流更早、更甚,也更多地接受了華夏文化。《史記·吳太伯世家》曾載:“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于是始通于中國。”[7]公元前544年,吳王壽夢第四子季札出使魯國,已能從華夏文化的角度審視詩三百,并逐一評論之。此后,季札又游歷齊、衛、鄭、晉等中原諸國,帶回了許多華夏文化,使吳國逐漸華夏化。“句吳”之民并入越國也進一步推動了“于越”的華夏化。
“于越”與華夏交往交流的起點自然也是十分遙遠的。據研究,“先越文化”的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良渚文化的創造者與夏商周時代的人們在宗教信仰上一脈相承,夏商周文明中的宗教信仰來源于良渚文化;商的青銅文化對越國有強烈的影響,周文化則通過吳國而影響越國[10](P1-10)。據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來賓”。說明至遲在公元前11世紀末,于越已與中原王朝交往交流。此后,春秋、戰國時期,越國與中原各國爭霸,文化交融隨著交往交流的日益頻繁而發生,越地出土的青銅禮器,尊、鼎、爵等,越來越具有中原華夏文化特征,越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等沿襲、仿效商周舊制的色彩越來越明顯。華夏化明顯的“句吳”并入越國無疑加速了越國人“于越”的華夏化。越滅吳后,勾踐為了爭霸中原,于周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 遷都瑯琊,這也是于越民族的一次大遷徙,于越從此更加接近中原華夏人,交往交流更加便利。雖然此后越王翳因國勢衰弱難以立足北方而南返于吳都,越王無疆敗于楚之后回走越人基地——“南山”,即會稽山和四明山一帶的南部山地,但越國之民不可盡返,滯留北方者當不在少數。公元前306年,即楚懷王二十三年,楚國聯合齊國滅了越國。“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7]。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7]。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為防止越人重新聚集以傾覆秦王朝,秦始皇為“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彰。因徙天下有罪適(謫) 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11]。以謫徙民,與越雜處。于越大部被華夏化,只有小部分逃入高山叢林之中的成為“山越”,逃往海外諸島的成為“外越”。
“百越”的其他支系,如閩越、東甌、南越、西甌、駱越、滇越等,雖然自夏商以來即與中原華夏交往、交流不斷,但華夏文化對它們的影響遠遜于對“句吳”“于越”的影響。
閩越,主要分布在閩江流域。先秦時期,受中原華夏文化影響不深。至秦始皇統一中國,在閩越之地設閩中郡。秦末,閩越王無諸助漢滅秦,漢王朝以羈縻制治之,以無諸為閩越王。到漢武帝時,閩越坐大,漢武帝遂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 派兵攻打,殺閩越王余善,結束了地理格局中的閩越國局面,并“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7]。被遷徙至江淮的閩越此后逐漸漢化,成為漢民族的一部分。
東甌,主要分布在甌江流域。秦時,臣服于秦王朝。秦以羈縻制實行統治,利用東甌王搖統治東甌舊部。秦末,諸侯叛秦,東甌王搖“從諸侯滅秦”,并在后來的楚漢相爭中“不附楚”,而“率越人佐漢”,故在漢初被漢王朝封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12]。但隨著漢王朝政權的鞏固,劉邦開始消除異姓王,東甌遂與中央王朝發生矛盾,及至漢景帝時參加了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之亂。但“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7]。漢武帝接到東甌的求援,“遂發兵浮海救東甌”,盡管“未至,閩越引兵而去”[7],但東甌與閩越從此結怨,東甌王為求自保,便請求歸附漢朝。漢武帝接受了東甌王的請求,將東甌遷至江淮間與漢民雜處。東甌也在此后的歷史進程中逐漸漢化,成為了漢人。
南越,主要分布在今廣東省及廣西東部部分地區。據研究,其在商周時期受中原華夏文化的影響較閩越深刻,在嶺南地區石峽上層類型的夔紋陶文化中,發現有閩越地區沒有的青銅盉、鼎、鐘等周式禮器[6](P346)。秦統一六國后,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 派尉屠睢率50萬大軍,揮戈南下,略取嶺南,雖遭遇頑強抵抗,損失慘重,但歷經艱難,終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統一了嶺南,即于嶺南設桂林、南海、象郡。盡管秦統一嶺南后不久便亡,實際上對嶺南沒有多少直接的治理,但秦始皇先后5次強行遷徙各色“中縣之民”或“中縣人”至嶺南,“與越雜處”,強迫越人同化[13](P52-53)。
漢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行南海郡事的趙佗建南越國,都番禺。他一方面“和輯百粵”,依從越人風俗,任用越人為官,另一方面又堅持漢族文化,實行秦漢的政治、軍事、文化制度和禮制,推廣漢族的語言文字,倡行越漢通婚,使漢文化得到了全面而廣泛的傳播,為越漢兩族的融合奠定了經濟、思想和文化的基礎。及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由于南越國不用漢法,丞相呂嘉謀反,攻殺南越王興及太后和漢使者等,漢武帝發兵10萬,分5路直指南越國。翌年冬,平南越國,于其地置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嶺南重新置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雖然其間或有“以其故俗治”等統治政策,但終究從此在嶺南與中央王朝間更無阻梗,兩地間的交往、交流更加頻繁。至東漢末年,廣東境內番禺、廣信等地越漢融合的結果,越已不復為越,而形成了一個操粵方言的群體,這就是漢族廣府民系的先民[13](P100-101)。
西甌、駱越,大致分布在今廣西境內。由于在秦漢時期的史籍中,有時單稱甌或西甌,有時單稱駱或駱越,有時又連稱甌駱,致使后人對于西甌和駱越到底是兩支不同的越人,還是同一支越人的問題見仁見智。有人認為,西甌和駱越是同族異稱;有人則認為,西甌和駱越是不同的兩支越人。這是一個自古以來就爭論不休的問題,至今未有共識。但不管西甌、駱越是一族還是兩族,他們與南越一樣,自秦漢以來,經歷了一個與漢文化交流交融的過程。然而,或許是廣西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的緣故,西甌、駱越的主體并沒有演變成為漢人,而是在東漢之后演變成為烏滸、俚、僚,到宋、明之時,演變成為壯、布依、黎、侗、仫佬、毛南、仡佬、水等民族。
滇越,大致分布于今云南西南地區一帶。《史記·大宛列傳》曰:“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7]可見當時滇越與中原漢人已有往來。但時至東漢,滇越之名消逝,而“撣”之名出現。在后來的歷史過程中,撣在受漢文化影響的同時,也受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強烈影響,而逐漸演變為傣(泰)族[14](P192-196)。
總體來看,百越文化在融匯于中華文化的歷史過程中呈現出兩種形態或結果:
第一,越人漢化為漢族。從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滅亡,歷秦始皇統一嶺南,至漢武帝平閩越和南越,為漢人族群大規模南遷進入百越地區,越漢文化的交融奠定了基礎。至秦漢時期,百越地區漢民人口大幅度增加,漢文化傳播勢頭強勁,區域文化達到了高度的漢化:戰國前后,句吳、于越已完全融合于華夏族,其所操語言亦融合成華夏語(漢語) 的方言之一——吳越語。東甌、閩越被遷至江淮間的,旋即被漢化,留在原地的也在與漢人的互動中于東漢中晚期融合成為漢族的一支——潮汕民系[13](P107-108)。
第二,越人演變為壯侗語各民族。未漢化的越人,亦在與漢人交往交流交融中,演變成為新的族群——(烏滸) 俚、僚。兩漢之后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戰亂頻仍,為逃避戰亂,漢人持續大量南渡,規模化移民高潮迭起,百越地區人口驟增,漢文化成為了主體和主流文化。至唐宋之后,越漢文化交融的結果,一是大量的俚、僚被漢化,成為了漢人;二是部分俚、僚在宋元明時期演變成為壯、侗、黎、布依、仫佬、毛南、水族、仡佬、傣、京等少數民族。
三、長留風雨在江東:百越余韻為中華文化增色添彩
“一自百川歸海后,長留風雨在江東。”[15]清代毛奇齡的詩句形象地反映了百越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影響和貢獻: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其實就是中原華夏-漢人與邊疆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個復雜的歷史文化過程。一方面,中原華夏-漢文化在同化百越民族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百越民族的文化成分,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漢文化;另一方面,一些未漢化的百越族群后裔在經受了華夏-漢文化的洗禮之后,也以少數民族群體的身份,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這些少數民族文化也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不論如何,總的來說,百越文化匯入了中華文化的海洋,百越文化的積淀大大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百越文化的余韻為中華文化平添色彩。
(一) 百越故地的漢文化包含著豐厚的百越文化積淀
百越故地的漢人,不論是南來的漢人,還是漢化了的越人,都經歷過越文化的浸染、熏陶,因而具有越文化的因素,這些因素一代代傳承下來,成為了百越故地漢文化的特質。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百越故地的吳語、粵語、閩語、客家話等漢語方言,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百越先民的語言成分。羅美珍認為,客家話中的古越語成分不能看作“南島語底層”,只能看作是漢語受古越語的影響,這是一種借代關系,而閩、粵、吳方言中的古越語成分是“南島語底層”[16]。
第二,漢唐以來,特別是唐宋以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合浦、泉州、廣州等港口城市的興起及海外貿易的昌盛,是百越民族“便于舟楫”的文化傳統的傳承與發展。合浦港曾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始發港,極盛一時。由于兩漢時期,中原與嶺南交往十分頻繁,中原的產品蜀錦、絲綢、瓷器等經南流江從水路大量涌入合浦,而合浦的珠璣、犀、象、農產品也大量銷往中原一帶,隨著對外貿易的頻繁,印度及東南亞商人多從合浦港登陸,然后經合浦港沿南流江前往中原,因而合浦港迎來了發展史上的高峰期,直至唐宋之后,才讓位于廣州、揚州、泉州等大港口。從現在的考古發現來看,合浦發現有大批的漢墓,說明漢人已大量進入該地,而從出土的遺物來看,這些人顯然受到當地越文化的影響。如大量出土的建筑模型,就有干欄建筑的風格。受越人“便于舟楫”文化的影響,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而合浦不僅是連中原、抵交趾等地的中轉港,同時還是以盛產珍珠(南珠)而聞名的商港。長期以來,合浦沿海居民“賴以采珠為活”,這是越人“陸事寡而水事眾”[17]的繼承。唐宋之后,廣州、揚州、泉州等大港口的興起,海外貿易的興盛,也是百越民族“便于舟楫”文化基因的遺傳。
第三,百越故地漢人的干欄式建筑、喜食水產、嚼檳榔、不落夫家、鑲牙、崖洞葬、船棺等日常社會生活習俗是百越文化的繼承。如百越的干欄式建筑自新石器時代便已發源,河姆渡遺址[18]、廣東高要茅崗遺址[19]都發現了干欄式建筑遺存。這個傳統大概在漢代就已為當地的部分漢人所接受,廣西、廣東、福建、江西等地漢墓發現了不少的干欄式建筑模型,說明干欄式建筑在當時漢人社會中也很流行。又如,南方漢人自古以來喜食水產,這也應是受“越人美贏蚌”[20]影響的結果。而至今南方漢人常見的二次葬習俗以及崖洞葬、船棺葬等習俗亦是源自于越人。
第四,百越故地漢人對媽祖、蛇神等的崇拜,是百越民族原始宗教的傳承與延續。據研究,中國東南漢人所信仰的媽祖是越人的后代[21];華南漢人的蛇神崇拜源于越人的蛇圖騰文化。華南漢人對“媽祖”和“蛇神”等的崇拜,不但凸顯了華南土著文化的傳承與基層特征,更透露出華南漢民社會文化的復雜性,不管華南漢民是越人的漢化還是越化的漢人,他們身上濃重的媽祖崇拜和崇蛇文化,表明他們并不是中原漢民簡單的“衣冠南渡”,而體現了華南文化史上漢越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混雜局面[6](P401)。
(二) 百越后裔民族文化傳承著百越文化基因
作為百越后裔的壯侗語各民族傳承著百越文化的基因,最顯著的主要有三個方面。
1. 語言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壯語與亻良語相似,民國《天河縣志》云:“俍語與僮略同,而聲音略勁”。而“俍”與“僚”有嬗遞關系,“俍”乃由“僚”演變而來[22]。俚僚語,柳宗元說是“殊音”,周去非亦“不可曉”,異于漢語無疑,但俚僚呼其所尊者曰“都老”或“倒老”,與壯族無異,直至解放前,壯族仍稱“寨老”“鄉老”為“都老”,稱年長的男人為“都齋”,年長的婦女為“迷都”或“都伯”,“都”有“人”的含義,乃人稱冠詞,說明俚僚語與壯語相似。不僅如此,我國學者將今壯語拿來同古代“越人歌”進行比較研究,結果證明今壯語同古越語基本一致[23]。
據《廣西通志》引《慶遠府志》記載僚人語言的基本詞匯,用來與侗語基本詞匯進行比較,是基本相同的。例如,僚人稱母親為“乃”,侗族也叫“乃”,有的則叫“埋”,僚語稱兄為“懷”,侗語則叫“吠”。弟,還有許多基本詞匯完全相同。如,僚語和侗語都稱弟為“儂”、穿衣為“登苦”、吃飯為“誼歐”、飲酒為“該考”、吃肉為“誼難”等。往上追溯,有學者將西漢劉向《說苑·說善》 中的《越人歌》 與侗語進行比較研究后,認為:“侗語似比壯語更接近于《越人歌》原意”[24];或“似可認定這首《越人歌》是古人侗歌”[25];或“《越人歌》 是古代百越支系的民歌,它與侗族早期民歌有直接的淵源關系”[26]。這充分說明了侗語與古越語的親緣關系。
仫佬族語保留的伶族稱,是對僚、俚、駱越、西甌族群稱謂的記錄和詮釋。仫佬族地名峒、駱(羅、樂),與駱越的駱有關。仫佬族稱“我們”為“饒”,正是古“西甌”切音。仫佬族自稱“伶”難詳其義,但其音卻是“僚”失去m韻尾的語音,“僚”復原m韻尾,即是“伶”,其語音可以追溯到古駱越民族的源頭。仫佬語與俚語、僚語是相通的,俚人、僚人的一些稱謂可用仫佬語來破解。如俚人的“倒老”,仫佬語稱為“冬老”,是“寨老”的意思。又如“郎火”,《炎徽紀聞》載:“撩人,古稱天竺……無版籍部勒,每村推其長有智者,役屬之,號曰郎火。”“郎火”即“頭人”“首領”的意思,現在仫佬族仍稱“頭人”為“郎火”。仫佬族語與壯語、侗語也很是接近。范宏貴在比較了壯、侗和仫佬族語言后,認為仫佬語是壯語和侗語之間的一個過渡。
毛南族的語言與緊鄰的黔南水語很接近,與侗語、仫佬語有半數基本詞匯相通,也與壯、布依語有密切的親屬關系。
水語與同語族中的侗語、毛南語、仫佬語、布依語、壯語有親緣關系,尤其與侗語的關系最為密切[27]。
而李錦芳通過研究發現,仡佬語屬于侗臺語四大語支(臺語支、侗水語支、黎語支、仡央語支) 之仡央語支。侗臺語言起源于廣西一帶,黎、仡央兩語支是較早遷出的部分。仡央各支系與古夜郎關系密切,西漢夜郎國降漢之后,其地置牂牁郡。牂牁系倉吾之延續,因其地多原倉吾越人,遂稱牂牁。上古音倉吾與牂牁相通。倉吾系最古老的越人部族之一,商周時期是越人的強盛部落。倉吾在今桂東北一帶,夜郎可能是其向西擴張的后裔。仡央語支與古越語關系密切。仡央先民當是與其他侗臺先民共居嶺南,后來才西進貴州高原,建夜郎國,至漢代他們仍與同種同言的南越保持密切聯系。仡央語支與相距遙遠的黎、臨高語有許多同源詞,有的與侗水語支同源而與臺語支不同,說明雙方仡央先民在黎、臨高人遷離大陸以前具有密切關系,他們共同生活的地區可能在桂東粵西,即古倉吾部及其以南地區[28](P45-56)。
2. 習俗
如越人居住干欄的習俗,在壯侗語民族中得以傳承。繼越人之后,僚人亦住“干欄”房屋。《北史·僚傳》載:“僚者,蓋南蠻之別種,散居山谷,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唐書·南平僚》則更進一步說:“南平僚者……部落四千余戶,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樓居,登樓而上,號曰干欄。”僚人的“干欄”比越人的“干欄”有很大進步,已明確人住樓上,必須“登梯而上”。繼僚之后壯侗語各族的房屋也是“干欄”。直至現代,在壯侗語民族地區的農村里,這種樓上住人,樓下養家畜和置放農具的“干欄”式房屋,仍到處可見。
越人有“椎髻”“鑿齒”之俗,于古籍記載頗多。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 說:“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俗。”《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載:南越王趙佗也行“椎髻箕踞”之俗。《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也說:“凡交趾所統……項髻,徙跣,以布貫頭而著之。”近年在湖南、廣東、廣西出土的越墓中,都有“椎髻”發形。文獻和考古資料證明,越人“斷發”和“椎髻”是并存的。“鑿齒”又稱“打牙”,就是拔去一、二顆牙齒。《淮南子·墜形訓》說:“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南至東南方……鑿齒民。”《戰國策·趙策》也說:“黑齒雕題,鰻冠林縫,大吳之國也。”所謂“鑿齒”“黑齒”都是拔牙的習俗。“椎髻”“鑿齒”之俗被僚人繼承了下來。《博物志·異俗篇》說:“荊州極西至蜀,諸蠻曰僚子……既長,皆拔出上齒各一,加狗牙各以為華飾。” 《太平寰宇記》 載:“蠻僚之類……椎髻、鑿齒、穿耳。”在壯侗語民族的婦女中,長期盛行椎髻發型。乾隆《柳州府志》 載:“……峒人,椎髻,首飾雉尾,卉衣。” 《老學庵筆記》 稱:“在辰、沅、靖州等地,有仡伶、有仡欖,男未婚者,以金雞羽插髻。”至于“打牙”,在1950年前,有些青年男女,喜將一二顆門牙鑲成“金牙”或“銀牙”以為華飾。還有的壯侗語民族地區在人死后,如果牙齒尚齊全,必須敲掉一顆門牙以后,才能入棺埋葬。
越人篤信鬼神、盛行雞卜的習俗,在壯侗語民族文化中有所體現。 《史記·封神書》 記載:“是時既滅南越……乃令越巫立越祝詞,安臺無壇,以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漢書·郊祀志》也有粵人信鬼,“而以雞卜”的記載。漢代以后,雞卜之俗仍在越人后裔中流行。唐代柳宗元《柳州峒岷》 詩云:“鵝毛御臘縫山廁,雞骨卜年拜水神。”宋人周去非《嶺南代答》對雞卜的方法有具體的記載:“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未孽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祈禱,所占而卜殺之,取腿骨洗凈,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號,伴兩腿骨相背于竹挺之端,執挺再禱。”“乃視兩骨之則,所有細穴,以細竹挺長寸余者遍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兇。”以雞卜定吉兇的習俗,從越人至僚人一直流傳到現代壯侗語民族。《貴州圖經新志·黎平府》記載:“洞人病不服藥,惟于古木水邊祭鬼,以雞以卜吉兇”。《平樂縣志》說:侗僚“婚葬用五行,以雞骨卜吉兇。”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在壯侗語民族地區,尚能見到“雞卜”與“蛋卜”的活動。
3. 宗教信仰
體現越人生活在水網地區、從事稻作農業等特征的宗教信仰在壯侗語民族中得以傳承。
(1) 太陽崇拜。左江流域巖畫中,體現越人太陽崇拜的遺跡主要有3處:一處是寧明花山第二區第二組巖畫,這是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及其下方3 個頂禮膜拜虔誠歌舞的圖像[29](P39);一處是崇左銀山第二處第二組巖畫[29](P144-145),畫面上方是一個太陽圖像,下方為一群舉手歌舞的膜拜者圖像;一處是扶綏縣吞平山第一組巖畫,畫面上有2個正面人像,其中一人身軀高大,另一人較矮小,其左上方有一太陽圖像,可見7道光芒線條[29](P183)。太陽崇拜一直在越人后裔中傳承。北齊魏收《五日》詩云:“因想蒼梧郡,茲日祀東君。”蒼梧乃廣西東北部,東君便是太陽神。屈大均《廣東新語》亦曰:“蓋南人最事日,以日為天神之主,炎州所司命,故凡處出山者,登羅浮(山)以賓日;處海者,臨扶胥以浴日,所謂戴日之人也。又日之所中,在其首上,故日戴。”在壯侗語民族所鑄造的象征財富和權力的寶貴重器銅鼓上,無一不鑄有光芒四射的太陽紋[30](P115-119)。直至現代,太陽崇拜的現象仍可見于左右江地區。如在南部方言的壯族普遍認為太陽是天的眼睛,日蝕時,人們要打鑼,把掃帚往天上捅,以防狗把太陽吃掉。云南西疇革機屯的壯族,每年春節期間都要由族長帶領族人到一固定的小山頭上祭拜太陽。大年初一清早,族長帶領族人到山頭上,在一塊大石上擺上供品,朝太陽升起的地方朝拜。太陽升起的時候,族長帶領族人,繞著大石頭轉圈,祈求一年的平安、豐收。
(2) 月亮崇拜。據分析,左江巖畫上的圓形圖像第一型第一形、第十一形,第二型第一形、第九形,第三型第一形及第四型各形有可能屬于天體圖像[31](P168)。這反映出越人除了太陽崇拜外,還有月亮崇拜。崇拜月亮的習俗在左右江流域至今流傳。如桂西的靖西、德保、那坡、大新、天等一帶,流行一種祭月請神活動。這一活動當地俗語稱為“請囊亥”,翻譯成漢語即請月姑娘之意[32](P1698-1701)。分析祭月請神活動的整個過程和全部內容,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雖然摻入了不少巫、道的成分,但其本質無疑是源于自然崇拜之一——對月亮的崇拜。
(3) 銅鼓崇拜。《后漢書·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水經注·溫水》載:“……蓋籍度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其名。”與文獻記載相印證,百越地區出土銅鼓甚多,在左江流域巖畫中銅鼓圖像也甚為常見。銅鼓在越人后裔心目中是權力和財富的象征。《隋書·地理志》載:“自嶺以南二十余郡……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為雄。……諸僚皆然,并鑄銅為大鼓。初成,懸于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富豪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號為都老,群情推服。”《太平御覽》:“有鼓者,極為豪強。”《續資治通鑒長編》:“家有銅鼓,子孫秘傳,號為右族。”。談遷《國榷》卷六九:“藏鼓二三,即雄長諸蠻。”朱國楨《涌幢小品》卷四:“藏(銅鼓) 二三面者,即得僭號為寨主矣。”《明史·劉顯傳》也說:“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于此下貪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曹學銓《蜀中廣記》引《上南志》:“銅鼓,有剝蝕,聲響者為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差等。”明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一二:“仲家,范銅為鼓,其制類鼓,無底。遇死喪,待賓客,擊以為樂。相傳諸葛武侯之所鑄者,價值牛馬或以百計,富者傾產市之,不惜也。”田汝成《行邊紀聞·蠻夷》中載:仲家“俗尚銅鼓,擊以為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即夸張言諸葛武侯所載者,富家爭購,即百牛不惜也”。明鄺露《赤雅》:“銅鼓,……重貲求購,多至千牛。”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六載:“瓊州有黎金,似銅鼓而扁小,上三耳,中微其臍,黎人擊之以為號,此即鐺也。古時蠻部多以銅為兵,以銅為器,富者鳴銅鼓,貧者鳴鐺,以為聚會之樂。”時至現代,銅鼓在壯侗語民族中依然是神圣之物,據不完全統計,廣西河池市現藏傳世銅鼓1400余面,崇左市和百色市幾乎每個壯族村落都有,逢有重大節日慶典,可拿出來使用。更重要的是,在左、右江地區很多有關銅鼓來源的神話傳說依然流傳,銅鼓的平時管理有制度,銅鼓的啟用及收藏有一定的儀式和風俗,銅鼓依然發揮著娛樂、神器、重器和集眾的功能[33](P12-22,206-220)。
(4) 雷神崇拜。在古代文獻中,有越人及其后裔祭祀雷神的記載很多。如《太平廣記》 云:“唐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為海康郡,……其事雷畏最甚謹,每具酒肴奠焉。”《鐵圍山叢書》曰:“獨五嶺之南,俚俗猶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謂之天神。”《嶺外代答》卷十亦曰:“廣右教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畏。圃中一木枯死,野處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禳之。茍雷震其地,則又甚也。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豐,末年盛祭。每祭,則養牲三年而后克盛祭。其祭也極謹,雖同里巷,亦有懼心。一或不祭,而家中偶有疾病官事,則鄰里親戚眾憂之,以為天神實之災。”對雷神的頂禮摸拜,在唐宋朝的時候,似是廣南西路人們的地區性行為。宋朝廣南西路,包括今廣西、廣東高州縣以南的粵西南及海南省。在這些地區內,越人后裔廣建雷廟或雷王廟。比如,《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職方典》卷一四三三《梧州府祠廟考》載:“雷神祠,本邑各鄉俱有,每三年用特牲祭。”唐朝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雷塘廟開祭之日,也到廟中讀禱雨文,祈求雷神叨念民艱,降下雨水急民之急[34]。左江流域巖畫眾多的銅鼓圖像充分說明《蠻司合志》所說的“是鼓有神”,因為它是通神之器。此神即為雷神。《廣東新語》稱銅鼓“雷人輒擊之,以享雷神,亦號之為雷鼓之。雷,天鼓也。……以鼓象其聲,以金發其氣,故以銅鼓為雷鼓。”在出土的眾多銅鼓上,多飾有云雷紋,按照“雷取其奮豫,云取其濡澤”的記載,云雷紋與風云雷雨有關。因此,銅鼓的出現和使用是雷神崇拜的反映。而在壯族神話中,雷神被尊為壯人早期四大神(雷公、布洛陀、蛟龍、虎)之首。雷王的生動形象:雷王住在天上,有一副青藍色的臉,燈籠般的眼睛,鳥類的嘴,并長著一對翅膀;他左手可以招風,右手可以招雨,兇惡威嚴;他主宰著人間風雨,生死禍福,既可使人間風調雨順,又可使天旱地裂或洪水滔天[35]。在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壯侗語民族中也有雷神崇拜的現象[36]。
(5) 水神崇拜。由于越人及其后裔生活于河流縱橫的江南地區,他們“仰潮水上下”而墾食“駱田”[7],或“射翠取毛,割蚌求珠”[37],因而“陸事寡而水事眾[17]”。大量貝丘遺址表明,百越先民大多背山靠水而居,漁獵一直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們與水結下了不解之緣。水中有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源,而水又可以給他們帶來災難,因此對水的崇拜在越人中占有比較重要的位置。紋于銅鼓之上的龍舟競渡習俗,至今仍流傳于我國南方各地。龍舟競渡雖系托“救屈原以為俗”,其實早在屈原之前的春秋時期便已存在于越人之中,其原始的性質就是祭水神的禮儀節目。正如聞一多在《端午的歷史教育》中指出,端午節是斷發紋身的越人,為祈求生命得到安全保障而舉行的祭節,所進行的龍舟競渡,便是這種祭祀中的娛樂節目。有人認為,左江流域巖畫與水神祭祀有密切的關系,整個巖畫就是祭祀水神的生動畫卷[38]。越人祭水神的習俗薪火相傳。唐柳宗元《柳州峒氓》詠道:“鵝毛御臘縫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溫庭筠《河瀆神詞》曰:“銅鼓賽神來,滿庭幡蓋徘徊,水村江浦過風雷,楚山如畫煙開。”孫光憲《菩薩蠻》云:“木棉花映叢祠小,越禽聲里春光曉,銅鼓與蠻歌,南人祈賽多。”許渾《送客南歸》詩亦云:“瓦樽留海客,銅鼓賽江神。”這些材料都描繪了當時駱越后裔祭水神的盛舉。直至近現代,壯族人還認為有一種叫“圖額”的神,住在水深的河彎或深潭中,因而他們在戽水捉魚時,要對“圖額”燒香、禮拜和上供[35]。所謂“圖額”,就是鱷魚,是壯族先民及壯族心目中水神的具體形象。在壯侗語民族心目中也有自己的水神崇拜。
(6) 蛇崇拜。百越民族蛇崇拜的文化特點十分突出。《說文解字·蟲部》曰:“南蠻,蛇種。”《說文解字·閩》:“閩,東南越,蛇種。從蟲,門聲。”《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器時代,百越地區普遍發現幾何印紋陶,據研究,其紋飾是蛇形、蛇皮鱗紋的簡化,起源于古越人的蛇圖騰崇拜[39]。華南、東南和云貴高原越系青銅文化中,蛇形、蛇紋的青銅器也很多見。這種崇蛇文化在壯侗語民族中傳承,表現為壯侗語民族的“蛇祖”“龍母”“蛇母”崇拜[6](P373-391)。
(7) 青蛙崇拜。在左江崖壁畫中,每個人的形象都是叉開雙腳,兩手拱起,手指和腳趾叉開[31](P158-162),分明是在模仿青蛙的造型。這是駱越人崇拜青蛙的反映。反映越人青蛙崇拜的材料很多。首先,反映在族稱上,據研究,越人之“越”為“雩”的同音變異,而“雩”為古越語謂“蛙”之音。所以,“越人”其實就是“蛙之人”的意思[40]。反映在考古發現上,越人及其后裔鑄造和使用的銅鼓的鼓面大多飾有立體青蛙,有的是單蛙,有的是迭蛙,數量從1只、4只至6只不等[30](P81)。這包含有深刻的信念內容。人們之所以在銅鼓上鑄造青蛙是因為他們相信青蛙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能給他們以幫助和庇護。青蛙崇拜流傳至今。特別是在左右江流域壯族文化中,得到了較好的傳承。壯族的民間文學以聽覺的形式表現了壯族對青蛙的崇拜之情。壯族關于青蛙的神話很多,如《螞蟲另歌》[41]《祭青蛙》[42]等,都把青蛙說成是上天下來的神物,具有非凡的本領。一些地區的壯族還相信日蝕、月蝕的發生是由于蛤蟆吞食日月所致[43](P24)。另外,《螞蟲另仔成親》[44]《青蛙姑娘》[45]和《蟾蜍的故事》[46]等神話故事還描述了蛙蠅變成人與人類結親的情節和內容。不僅如此,東蘭、鳳山和南丹一帶的壯族至今流行一個規模盛大的祭蛙節日——螞蟲另節。螞蟲另節又稱“蛙婆節”或“埋螞蟲另”,這是一個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典禮。
(8) 犬崇拜。古代越、僚人對狗非常尊寵。《國語》卷二十《越語上》載:越國君王勾踐為了鼓勵生育,增強國力,曾下令:“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以狗獎勵生男孩,以豬獎勵生女孩,可見狗在當時越人心目中的分量。 《太平御覽》 卷七八〇《敘東夷》 引《臨海水土志》說,“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棧格上,似樓狀。……父母死亡,殺犬祭之”。《臨海水土志》是三國時代沈瑩所撰,安家之民就是當時居住于今閩、浙之界的越人。他們殺狗祭祀死去的父母,逝去的父母可以得到慰藉,靈魂可以因狗而逸升天際。直至近現代,廣西崇左一帶的壯侗語民族,春節時仍結草為狗像,并在其身上披掛彩帶而立于村口供奉;有的地方則鑿石為狗,立于村口供奉,以期驅鬼禳災,保佑村寨平安。
(9) 鳥崇拜。廣西左江崖壁畫的扶綏岜賴山第一處、后底山第二處和龍州沉香角第一組,共有4 只鳥類圖案。其中除龍州沉香角一只位于正身人像的旁側外,其余3只均處于正身人像的頭頂上[31](P164)。雖然這幾只鳥的特征不很明顯,但左江崖壁畫作為駱越巫術文化的遺跡,畫上這幾只鳥是有深刻含義的。它很可能是傳說中的“雒鳥”,是駱越人所崇拜的圖騰。越人的鳥崇拜在其先民的神話傳說中有所表現。 《越絕書》 卷八載:“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何故也?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因病亡死,葬會稽……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吳越春秋》 《水經注》 《博物志》等書,也錄有這則東南越人“鳥田”的神話故事。而中南的駱越同有“駱田”的記載:“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駱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駱民。”[47]按照《說文解字》 的解釋,“駱田”即“雒田”,“雒”為“鵒其鳥”,意為“小雁”,因而“雒田”這個詞本身已包含著一個“鳥田”的傳說[48]。正因如此,駱越因鳥得名“駱人”,即“鳥人”之意。越人銅鼓上的紋飾以實物的形式直觀地反映了駱越的鳥圖騰崇拜。廣西出土的石寨山型銅鼓上,身飾羽毛、頭著羽冠的羽人圖像比比皆是。如貴縣羅泊灣銅鼓[49]和西林普馱銅鼓[50]的腰部都有羽人圖案。這與古代文獻中稱我國南方有“羽民國”的記載是一致的。《山海經·海外南經》曰:“海外自西南陬又至東南者……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同書《大荒南經》又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淮南子》卷四亦言南方有“羽民”國。其實,“羽人”是所謂“人的擬獸化”。它顯然是源對與鳥認同的心理,即鳥的圖騰崇拜。因為在廣西出土的銅鼓上,鳥的形象十分常見。貴縣羅泊灣銅鼓羽人圖案的上空有鳥口中刁魚、展翅飛翔,船頭還立有銜魚的鳥[49]。這種鳥是一種生活在海邊的水鳥或候鳥。《淮南子·本經訓》云:南方人“龍舟益鳥首”。高誘釋曰:“益鳥,水鳥也。畫其像著船首,以御水患。”這種水鳥就是傳說中的雒鳥,正是銅鼓主人駱越的圖騰鳥[51](P131)。越人的鳥崇拜在壯侗語民族中得到了傳承。在壯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的神話中,他們共同的始祖母被稱為“姆六甲”,始祖公被稱為“布洛陀”,這兩個名字分別是“六甲鳥之母”和“鳥首領”之意。此外,他們崇拜的布洛陀的兄弟雷王,也按鳥的形象來塑造:人身、鳥喙、鳥翼、禽爪[52]。壯族民間還流傳著許多人死后變成鳥的傳說。如民間故事《秧姑鳥》說,立夏前后,殷勤叫喚“勒谷勒啊”,提醒農民耙田插秧的秧姑鳥,是由美麗的壯族少女變成的[53]。《救哇鳥》[46](P164)《杜鵑鳥的故事》[54](P258-259)等也是此類故事。這些故事的內容與圖騰崇拜中人與圖騰同類的觀念是有關的。
(10) 田(地) 神崇拜。廣西寧明花山第一區第6 組巖畫中有一對男女在性交,其下排列著谷粒狀的點,旁邊還有銅鼓和人祭圖像。這是駱越人通過巫術將人的生產與農業生產聯系起來,祈求農業豐收的一個儀式場面。這個儀式場面祭祀的神是田(地) 神。對田(地) 神的崇拜在左、右江駱越后裔中一直得以傳承。由于壯侗語民族是稻作農業民族,田(地) 神崇拜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壯族十分常見社公祭祀,他們認為社公是全村的“主人”,主宰全村的禍福,因而各地都舉行一些儀式祭祀。
(11) 鬼神崇拜。關于越人及其后裔信巫祀鬼,古籍早有記載。 《史記·封禪書》 云:“是時,既滅兩越……乃令越巫立越祝詞,安臺立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史記》正義云:“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愿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形則吉,不足則兇。今嶺南猶此法也。”《北史·僚傳》:“僚人……喜則群聚……俗畏鬼神,尤尚淫祀,至有賣其昆季孥盡者,乃自賣以祭祀焉。”明王濟《君子堂日詢手鏡》云:“橫州專信巫鬼,其地家無大小,歲七、八月間,量力厚薄,具牛馬羊豕諸牲物,羅列室中,召所謂鬼童者五、六人,攜之楮造繪畫面具,上各畫鬼神名號,以次列桌上。以陶杖鼓,大小皮鼓銅鑼擊之,雜以土歌,遠聞可聽,一人或三、二人各帶面具,衣短紅衫,執小旗或兵杖,周旋跳舞。”清陸祚蕃《粵西偶記》載:“鬼魚似鱷,壯人仇殺取此魚祀鬼,輿人食之輒死,覺之請蠻人咒之立蘇。”現在壯侗語民族農歷七月十四日這個節日之所以名為“鬼節”,其源則起于越人及其后裔在這一天“祠厲”,即焚香燭、化衣,祭祀餓鬼、野鬼。農歷七月十四正是稻谷將熟不熟,青黃不接之時。鬼人相通。所以,“禾黃鬼出”[55],以及“十月禾黃鬼上村”[56]。鬼之所以活躍起來,是因為它們餓了,衣敝了,便上村來尋吃找穿。它們作祟于人,便出現了“稻田黃,睡滿床”的景況。為免除災難,人們便以七月十四日為鬼節,給餓鬼、野鬼們祭祀、化衣,滿足它們的要求,祈求它們不要傷害陽間的人群,送它們離開村子,由于七月十四日這一天,餓鬼、野鬼竄村入市,非常活躍,所以這一天人們便停止一切作業,不走村入市,連牛也關在家里不放養,唯恐撞上鬼。
以上論述,掛一漏萬,取直就簡,不論是百越故地漢文化,還是百越后裔的民族文化,其中不僅包含了百越文化的遺傳和底層特征,而且在傳承的過程中,漢文化與百越文化相互碰撞,其形態和內涵也在改造和整合中交融,從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局面。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格局便是這樣形成的。也正因為中華文化是海納百川形成的一體多元的對立統一體,才使得其始終生機勃勃,一直延綿不斷。通過百越文化融匯于中華文化的歷史研究,有助于深化對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