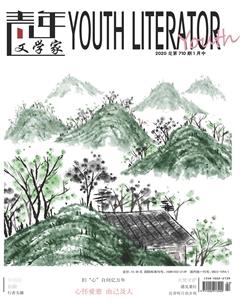遇見蕭紅


作者簡介:錢洪婷(1995.8-),女,漢族,海南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電影制作。
是在朋友力薦下,在《黃金時代》里認識蕭紅的。那夜,跟無數個在雷州的往常一樣,我臥躺在雷州的夜色里,靠著窗,感受透明窗外下車聲無盡的喧嘩和夜色的紛繁多雜,房間里被車燈反射得時明時暗,映在白色的天花板上,讓房間與我更加通透了。那夜,沒什么不同,但,又和之前的我所休憩過的夜,又似乎完完全全不同了。
(圖一,作者本人)
蕭紅的一生于大多數人而言,何其的短暫,但于她和認識她和像我一樣在后來偶然熟識她的人來說,又是完完全全完整的。于蕭紅本人而言,她臨終是這樣概述自己的“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對于時代,她沒有那么多的大是大非,生平的遭遇和長時間的情感寂苦,讓她更懂得去追逐一份安逸,或者說只需要給她一個在炮火中能提筆寫字的空間,寂寞和孤獨雖然纏繞著她,在街上的游走能暫時的讓她排遣。而,文字,是將她孤苦一一呈現的地方。
影片看到90分鐘后,我關了頁面,去瀏覽其他更加散碎和雜糅的東西來疏散我惶恐的內心,年長后,我很少于深夜落淚痛哭了,那夜,本該如此的,卻又多了一份堅韌并摻雜了多許冷漠和反世故。過了一會兒,又把手機放下,試圖把手靠近窗戶,遠離被窩,感受更為寒冷的地方,看著窗戶上隨著晃動的影子,又抽了回來。我想,某些時候,我和某個時間段內心孤楚的蕭紅,沒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在文學上,她更有文學的天賦和才氣了。
獨處雷州的時候,我變得比平常更為小心翼翼了,關門的時候隨時記得反鎖,插電的時候,反復擦干手,過馬路的時候,反復查看確定不會有危險再行走。我是懼怕死亡的,更懼怕死時的一事無成。我不想,赤裸裸的來到人間,體驗了一番苦楚,再如世間大多數人一樣,無人問津的離開,這是我的不甘。
(圖二,透過六樓窗戶看到的雷州某座房子的天臺)
那是個沒有工作的某日,我發現自己中毒了,一直有嘔吐感,煮了清面也沒吃幾口,整天窩在被子里,也不曾用電影和書籍來搪塞我的孤獨感。身體的不適,已經無法活動,大腦卻能更為敏銳和清晰的思考,我看著白晃晃的窗外和被風反復捶打的破布條,想來,雖只有23歲,在一眼能望到盡頭的人生里大抵如此了,我和那被雨反復洗禮,不斷翻轉蠕動的破布條終究是沒什么區別了。
那蕭紅呢,是不是也在某個時刻,能一眼望到自己人生的盡頭,也曾想過就此墮落過,就此過了一生。但幸好,她在有生之年相繼遇到了蕭軍,端木,魯迅以及崇拜她的駱賓基。蕭軍和端木的出現讓她有了情感的疏離,這于她,于她的創作都是有利的,這些情感的陸續出現,讓她的孤苦和清楚更加呼之欲出,但,她還是真的擁有過歡愉的日子,盡管痛苦占據了歡愉的極大多數。而,魯迅的出現,是給她創作上點燃了一盞黃暈的燈,對于二蕭的情感,魯迅和蕭紅的大多熟人一樣,放任自流,而在關于生活和文學上的交談,似乎更多。而在這樣舒適和愜意的交談中,那種文學上的氣息和相互纏繞的,魯迅既影響了她,她又成就了魯迅的一個小階段。如此,在魯迅逝世之后的歲月里,她才能在文字里替我們回憶起魯迅。
于當時的世界和蕭紅自己而言,按照她自己的揣測,她是受人摒棄的,呼蘭河畔寂寞紅,生死場里是無盡的死亡。
我是在23歲的年齡里偶然遇見蕭紅的,由此來愧嘆此前人生的荒遺。我每天向人高喊這我的人生志向,以此來排遣我對未來人生的惶恐和擔憂。我的熱情和意志已經日漸消磨,每次試圖用佯裝的忙碌來掩飾我的庸碌。
如果說關于我所衷愛的東西還有那么一絲殘存的意志,那關于我對世事的情感早就埋葬在家鄉的大龍潭的深潭里了。之所以不愿意返家,就可能因為故鄉回不去,而雷州小鎮又和故鄉酷為相似,我可以在這個絡繹不絕的人群中,聽著陌生的雷州方言,以更為窺探的視角,免去附加的情感去肆意地接受別人的善意和惡意,去打量這陌生的生活習慣和交談方式。
在23歲的時候,在陌生的地方,迎著初冬溫暖的太陽,任由日光照在臉上時,遇到蕭紅,是我人生一大幸事,或許今后的日子不會有太大改變,又或許與之完全不同,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31歲那年,她將與藍天白云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23歲的我會用自己的方式完成她遺留的那半部《紅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