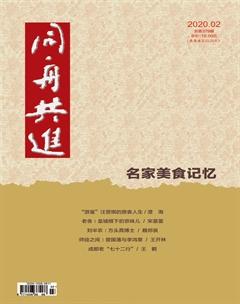江平先生印象
劉仁文
一
我雖然在1980年代讀大學期間就聽過江先生的講座,但真正和他認識還是在1990年上研究生之后。研究生期間我曾擔任中國政法大學的研究生會主席,多次為研究生會的工作去他家里。他那時就住在校門外一個普通小區里,經常騎自行車在校園里經過。記得第一次去江先生家,他正在看足球,這多少有點讓我失望,因為我是一個足球盲,而且當時他在學生眼中就是正義的化身,像他這樣的人物應當日理萬機才對呀,怎么會這么悠閑呢?后來我才知道,改革開放后先生確實是夜以繼日地工作,不過這并不影響他對足球和音樂的熱愛。其時,他不僅校內工作忙,社會活動也特別多,有時下課后在校外的面館匆匆吃過就出差去了。
江先生有一個天生患有智障病的女兒。這也是法學界許多牽掛他的人總是小心翼翼避開的話題。他一直對這個孩子懷有內疚感。多年后,他的自傳《沉浮與枯榮》面世,一時洛陽紙貴,在書里,身著古裝戲服的江先生和師母、女兒的合影被放在扉頁的顯著位置,這時我已完全能讀懂先生的慈父面孔了。以往還是學生時,每次去先生家,當他的女兒過來“干擾”我們談工作時,我心里總想,先生為何不把她支走呢?
1993年我研究生快畢業時,有一天在校園里見到騎車的江先生,他主動下車問我的去向,我告訴他自己聯系了中央政法委,他馬上說,他和時任中政委秘書長熟悉,他愿意幫我寫封推薦信。后來一切進展順利,快要報到時,卻因中政委當時暫時無法提供宿舍而作罷。后來我就到了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工作,沒想到,這一去,就從此扎下根來。江先生的熱心是出了名的,這些年來,他推薦過多少學生出國留學、推薦過多少學者出國做訪問學者,又給多少人題過詞、作過序、寫過推薦語,恐怕他自己也未必記得清楚。
1998年我們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近距離接觸的機會較多,我和先生還一起參加過哈佛大學、紐約大學等校的學術活動。先生經常去中國城買魚做飯吃(師母過一段時間才到),有時則跟我們去哥大附近一家中餐館吃便宜的自助餐,還跟大家請教要不要自己放回盤子,外國人戴戒指在哪個手指表示哪種含義等小事。后來他和師母回國時,自己叫出租車去機場,我們幾個為他送行,他雙手作揖表示感謝。當時國內一個副廳級學者“郁郁寡歡”,跟我抱怨說美方竟不安排人送她,我說這是文化差別,江先生也沒有人接送。
在美國期間,我跟江先生多次出游,他給我談過一些觀點,說實話,有的我當時接受不了,沒想到后來都慢慢有了同感。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往一個能俯瞰大海的坡上走,江先生說自己有恐高癥,就坐在路邊的椅子上等我們。還有一次我們在海邊散步,他說到幾年前在夏威夷,看到那海水,想到自己來一次也不容易,就取下了假肢,下海游了幾圈。
回國后我們時有往來。當時我們所的《環球法律評論》有一個名家訪談欄目,編輯部聽說我和江先生熟,還派我去對他做過一次專訪。這次訪談又得知了他的許多往事,對我也是一次人生洗禮。全文整理出來后,以“只向真理低頭——江平先生訪談錄”為題見刊,后來還被《永遠的校長》等多本著作收入。
先生的《沉浮與枯榮》一書影響超出法學界,榮登過許多圖書排行榜的前列乃至頭名。我深感意外和榮幸的是,書中他長篇引用了我的《法學家為什么沒有懺悔》一文。翻閱完這本書后,我給先生去了個電話,感慨他在前言中所說的:“我一生中真正能稱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幾乎沒有,這可能與我的人生信條‘君子之交淡如水有關吧……故友和至交逐漸離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我說看到這句話時,內心有種蒼涼感,誰能想到,大名鼎鼎、前呼后擁的江先生竟幾乎沒有故友與至交?電話那邊,沒有聲音,直到我岔開話題。先生是演講家,但與他有過近交的人應當也能感受到,他私下里話并不多,除非你主動提到某個話題或問他某人某事,否則有時甚至會出現較為尷尬的沉默。
二
2018年,社科院法學所老所長王家福先生榮獲改革開放先鋒稱號,江先生應邀參加座談會,并祝賀家福老師。我身旁一個名校法學院的院長對我說,很多人認為,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深度參與立法和司法、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體系做出過巨大貢獻的江先生也應當獲得這一榮譽,難能可貴的是,江先生對此毫不介意,光憑這一點就值得敬佩。前不久,家福老師離世,遺體告別那天,江先生早早趕到八寶山。我當時排在長長的隊伍后面,同事說,王師母看到江先生時十分激動,從輪椅上站起來抱著先生痛哭道:“您怎么也來了呀?您是兄,他是弟,您可以不來的。”
幾天后,我在一個與江先生同桌的餐敘中提及此事,先生說起當年自己在延慶期間,家福老師先后數次去邀請他來社科院法學所工作,并幫他辦理有關調動手續,就在辦得差不多時,傳來中國政法大學復校的消息,于是重回法大。江先生說,那時從城里去趟延慶可麻煩了,所以他特別感謝家福老師。這是我第三次聽他講起這段往事了,他雖然輕易不議論人的長短,但這次卻主動問起家福老師到底因何病去世、某某為何沒來參加遺體告別式等,使我深感這對上世紀50年代的留蘇同學由于治學理念相通,在坎坷漫長的歲月中所建立起來的彌足珍貴的深厚友誼。
江先生在許多人眼中已是一個近乎傳奇的人物。我曾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有崇拜他的年輕人在前往西藏求圣的途中,于青海高原路邊的石頭上刻上江先生的名言:“只向真理低頭”,并表示完成了此生的一個心愿。然而在我眼中,江先生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巴金在《隨想錄》的代序中說: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以我對江先生的了解,他骨子里應當是不希望別人把他看成神的,所以他也從不偽裝自己。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已經沒什么可迷信的了,剩下的就是:只向真理低頭”。然而到底什么叫真理?我曾向他提出這個問題,答案似乎并不明朗。
許多人感慨先生隨和,沒架子,對他的不卑不亢和寵辱不驚充滿敬意。在回顧人生時,江先生并不把自己看作英雄,他說他也有沉默的時候,好在從未昧著良心說過假話。他從不主動提起自己的輝煌經歷或頭銜,相反,對一些在別人看來似乎有礙他高大形象的事,他卻從不隱瞞、不回避。他曾在懷念謝懷栻先生的文章中表達出對謝老一流專業功底的景仰,“我也想到我自己,缺少像謝老那樣過硬的基本功”。他和謝老一起擔任仲裁員時,虛心得像個學生,“我在旁細心觀察他的態度,他的風格,他的問語,他的處理意見,似乎能想象到這位經過嚴格司法考試、司法訓練培養出來的法官當年斷案時的風采,甚至我在默默地禱愿,如果我們的仲裁員和法官都能有這么高的水平,那就是國家的萬幸”。看到謝老字斟句酌、反復修改仲裁裁決書,他自責道:“他那認真的態度,使我感到慚愧。”我曾問他,“呼格吉勒圖的墓志銘寫得真好,那是您自己寫的么?”我多么希望他回答“是”,但他卻說,“是我的學生王涌幫我草擬的”。先生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后來不幸夫妻離散,現在的師母是他后來找的。在迎來人生高峰后,無論何時何地,他都大方地介紹師母:這是我老伴。在《沉浮與枯榮》里,他還專門說過,改革開放后自己之所以能在事業上有所收獲,要多虧老伴和崔家人的支持(師母姓崔)。
先生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人。有一次,他所欣賞的學生張星水律師要我約江先生聚一下,我給他打電話,他說女兒在家沒人照顧,后來我說,那要是讓星水安排在他家樓下呢。他一聽就動了心,開始猶豫起來。但最后還是說:你們聚吧,我出去還是不放心。幾年前,他每到快過年,就因保姆要回家而犯愁,有段時間甚至與家人住進了養老院,他說養老院條件再好,也沒有家的感覺。現在,他終于找到了合適的保姆,也不用為過年到哪去而犯愁了,談起此事,先生喜形于色。
對人生有過深刻體驗后,江先生把世間名利看得很淡,為人很真誠。他的教授、博導頭銜在同齡人中解決得不算太早。當然,后來他當上校長和全國人大常委、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也在意料之外。他曾說,改革開放后的20年,他該得到的得到了,不該得到的也得到了,自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沒讀過幾本像樣的法學名著,更沒寫出像樣的法學專著。但他是一個法學教育家,培養出一批學生;他是一個社會活動家,積極參與立法和司法……
三
江先生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他從不記恨人,也不糾結于過去。他在自己70歲時,就想如能活到80歲已經是幸運了;80歲時,心想如能活到90歲就更是幸運了。如今90歲已悄然而至,看先生的心態與形態,我對他的長壽充滿樂觀。大概十年前,他曾大病一場,自從那次病后,先生遵醫囑不再進行重度科研工作了,但作為終身教授,還帶學生,也適度參加學校和社會活動。萬幸的是,他的語言表達能力迅速恢復,思維還是那么敏銳,對許多問題的見解仍入木三分。如今,他愛吃紅燒肉的習慣已經改掉了,換成吃牛羊肉了,胃口很好,我見過他連喝三碗羊肉湯呢。由于腿不好,年紀又大了,所以在家里安裝了健身器和按摩椅,每天堅持鍛煉和按摩。從昔日那種充滿激情的繁忙工作過渡到如今這種盡量減少外出的老年人生活,對于這一變化,他似乎已經習慣甚至享受。
先生把錢看得很淡。他是法學界第一個以個人名字設立基金會的人。在他70歲時,他把自己的積蓄幾乎全部拿出來,設立“江平民商法獎學金”,臺灣大學的王澤鑒教授等著名學者均捐款支持,可見江先生的人格魅力。如今,“江平民商法獎學金”已成為民商法學界含金量很高的獎項,每年頒獎,先生都會攜師母與會,并寄語莘莘學子。與他對公益的追求相比,他的生活卻簡單而樸素。有一次與他同席,當他得知那晚的套餐人均消費近200元時,他露出驚訝的神色:這么貴啊!
2014年《新京報》出了一期特刊,每個領域約請兩位學者對談,我和江先生受邀成為法學領域的嘉賓。在“互評”環節,先生說:“現在我已接近完成使命,行將退出歷史舞臺,希望年輕人接過接力棒,承擔起歷史的重任。”先生這話既是自謙,也是對我們年輕一代的勉勵。當記者問到我倆的幸福指數時,先生的回答是9分,我的回答是8分。他說:“缺的一分,是人生不可能有滿分。”事后我想,為何先生的經歷跌宕起伏,卻反而比我感到幸福呢?
江先生從不以權威自居,跟他交流不會感到壓力。有一次我們討論克里米亞問題,他認為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是對的,說那本來就是蘇聯送給烏克蘭的。我反問他,那您今天送給我的禮物,明天您想要回就可以要回嗎?這不符合民法原則吧。他呵呵一笑,就不做聲了。
先生確實是一個充滿故事的人。前不久見到他,我跟他核實,社會上傳說他和屠呦呦是親戚,可有此事?他說是的,兩家現在還有往來,屠呦呦也到他家去過。按先生的說法,兩家還是很親的,江先生和屠呦呦的關系大概相當于表兄妹。江先生祖籍寧波,為何出生在大連呢?就是因為當時屠家在大連,屠呦呦父親把江先生父親也介紹到大連工作,于是江先生一家就搬到大連去了。
就在這次的飯桌上,主食久等不上,江先生似乎有點著急。我很少看到先生著急,心想都這么晚了,他又這么大年紀了,難道還有什么重要事情?過了一會,主食還沒上,他終于忍不住了,跟大家說抱歉,自己要先走一步。我送他到門外,問他為何急著走,他說想趕回去看一場球賽。
這就是江平,一個可親、可敬又可愛的人,一個純凈、善良又率真的人,一個嚴于解剖自己,善于學習,見賢思齊的人,一個“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人。待他百歲時,我期待能有更寧靜的心情和更系統的時間來好好寫寫我眼中的江平先生,再細細品味那些本文沒來得及訴說的故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刑法室主任、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