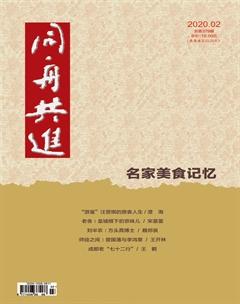“柴爿餛飩”里的老上海記憶
余云
怎么會想起“柴爿餛飩”來的呢?最近餛飩吃多了。
上海家的公寓小區夾在時髦的新天地和煙火氣十足的老城廂之間,人在獅城多年,買了這房子卻沒好好住過,近兩年停留時間稍長,一來二去領略了老城廂的好處:這里一直是最接地氣的市井美食寶地。
就拿上海人情有獨鐘的餛飩來說,大餛飩第一紅牌“耳光餛飩”,小餛飩最佳“夢花街餛飩”,風味別致的黃家闕路“魚肉餛飩”,夏季需耐心排隊的光緒七年(1881)開業的老店大富貴的“冷拌餛飩”,都在步行距離之內。一家家地堂吃、外帶,不亦樂乎中隱然有種失落,傍晚拎著幾盒薺菜肉餡生餛飩走回家時,忽然明白,自己想念的其實是早已不復存在的“柴爿餛飩”。
“柴爿餛飩”是上海人對流動餛飩擔的稱呼。餛飩擔流行于江南市井已有百多年歷史。舊時城鎮,中心以外的巷弄小道上很少小吃店、食品店,入夜更是寂靜一片,小販走街串巷的小吃擔子,牽系平民百姓的飲食日常。小吃擔最為普及的是蘇州、上海、無錫、常州等地,作家陸文夫在《老蘇州:水巷尋夢》一文中描述:“這種擔子很特別,叫作駱駝擔,是因為兩頭高聳,狀如駱駝而得名的。此種駱駝擔實在是一間設備完善,可以挑著走的小廚房……人在兩座駝峰之間有節奏地行走,那熊熊的火光也在小巷兩邊的白墻上歡躍地跳動……”《浮生六記》《閑情記趣》中,蕓娘雇的餛飩擔,就是這樣的駱駝擔。
餛飩擔不光上海才有,唯獨上海人稱“柴爿餛飩”。“柴爿”這個詞可能來自蘇州話,蘇州人稱“薄片”為“爿”,“柴爿”就是薄木片,也即“柴火”。流動攤販用木柴燒火并打著竹梆叫賣,最早可追溯到清末的老城廂,上世紀20至40年代的上海灘,餛飩擔十分常見。
張愛玲寫:“賣餛飩的一聲不出,只敲梆子,餛飩是宵夜,晚上才有……”和其他小販不同,餛飩擔主并不叫賣,而以敲竹梆代替吆喝,一根竹管做成的竹梆裝在餛飩擔前,“篤篤篤,篤篤篤……”竹梆聲自遠而近,黃昏或夜晚,吃客聞聲而來,擔子街頭一支,現煮現吃,水氣香氣彌漫。尤其在清寒秋冬之夜,饑腸轆轆的夜歸人路過,要一碗餛飩,舀一點辣油,在擔子前搖曳的燈光里熱騰騰的一碗下肚,疲憊的身心都舒展開來。

“柴爿餛飩”這種最瑣細的平民小食,到了作家、藝術家的眼里姿色各異。“冬夜,亭子間窗口,嬌滴滴的女子垂下吊籃,內置一碗,給情郎買柴爿餛飩,那吊籃的長繩,然是連起來的絲襪……”在《流言》中,張愛玲寫得香艷。在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里就有這樣的片段:蘇麗珍每天夜里換上一件美麗的旗袍,只為到街頭面攤去買一份餛飩。手上提著保溫桶,裊裊走在狹窄的樓梯上,和周慕云擦肩而過,欲語還休。夜燈迷蒙,餛飩成了隱秘愛情的見證。王家衛拍香港故事,復制的是上海舊時記憶。
退隱江湖的高手穿著打了補丁的布衣賣餛飩,還是香港武俠小說家古龍小說里的場景。擔子一頭炭爐正旺,上架滾水鐵鍋,另一頭油鹽醬醋裝在瓶瓶罐罐里,柜子里幾摞粗碗、幾瓶便宜燒酒。夜深,在小巷角落里卸下桌凳,點起風燈或蠟燭,默默等著來客光顧。來客非等閑之輩,即便販夫走卒也各自揣著驚心動魄的故事。
汪曾祺有篇小說,寫他的家鄉人物秦老吉,靠挑擔子賣餛飩養大三個女兒。他的擔子比別人講究,“一頭是一個木柜,上面有七八個扁扁的抽屜;一頭是安放在木柜里的燒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銅淺鍋。銅鍋分兩格,一格是骨頭湯,一格是下餛飩的清水……這副擔子是楠木的,雕著花,細巧玲瓏,很好看。這好像是《東京夢華錄》時期的東西,李嵩筆下畫出來的玩意兒”。他的餛飩也特別,“除了豬肉餡的,還有雞肉餡的、螃蟹餡的,最講究的是薺菜冬筍肉末餡的……作料也特別齊全,除了醬油、醋,還有花椒油、辣椒油、蝦皮、紫菜、蔥末、蒜泥、韭花、芹菜和本地人一般不吃的芫荽”。三個女兒同一天出嫁,同一天回門,秦老吉招待女兒女婿用的也是自家的餛飩。
一直以為林清玄的散文是些“雞湯”,讀到一篇《木魚餛飩》卻簡潔別致。在臺北臨沂街,推車賣餛飩的老人敲的不是竹梆子,每天凌晨準時傳進靜街窗口的,是梵音一樣清越的木魚聲……
大餛飩重餡,小餛飩重湯。和高郵秦老吉的各種花色餛飩,臨沂街餛飩老漢自豪的飽滿肉餡不同,上海早年的“柴爿餛飩”是清一色小餛飩:皮子薄如縐紗,又名“縐紗餛飩”,里面裹的粉紅肉餡很小一撮卻有點睛之效,湯里飄著豬油、蔥花、紫菜、榨菜、蝦皮、蛋皮絲。上海人愛這種熨帖肚腸、溫暖心房的樸實食物,“柴爿餛飩”是上海的深夜食堂。
后來時代變了,街頭柴火漸漸熄滅,直到1980年代才又重燃,不過攤販換成了到上海討生活的安徽人,有時會在攤子旁擱上一塊“柴爿餛飩”牌子,引來爺叔阿姨,蕩馬路的年輕情侶,加班晚歸的白領,功課做晚了的學生。
好景不長,“柴爿煙火”終于再次消失,真正成了歷史名詞。但食物是人們甄別和記憶一座城市的最好方式,每個在上海長大、有一定年紀的人,心里都存著一碗“柴爿餛飩”。
好友說,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一個冰凍寒夜里,她一只手捂在男友的大衣口袋里,一只手用調羹,在街頭攤子上吃過一碗格外美味的小餛飩。至今歷歷鮮明的是:昏黃的路燈光圈像一個罩子籠住了他們,光圈之外天地清徹,寂然無聲,世界只剩下他和她,一對低頭吃小餛飩的男女。
(作者系香港三策智庫特約研究員、旅加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