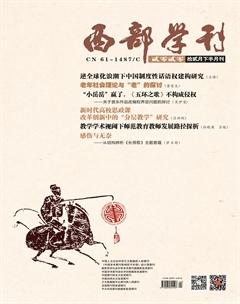試析涉黑涉惡環境資源犯罪案中的檢察監督失靈
摘要:對環境資源涉黑犯罪案件的查辦,涉及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之間的“兩法銜接”。現實中,這一銜接經常發生“不暢”,而檢察監督的失靈可謂是造成這種銜接不暢的重要原因。在當前制度下,環境資源類涉黑案件的司法移送檢察監督程序并沒有失靈;然而該類案件的刑事立案檢察監督卻始終羸弱,這正是該類涉黑案件“兩法銜接”問題在檢察監督層面上的癥結所在。基于此,我們必須探尋一種強化該類案件刑事立案檢察監督的路徑。從現有的檢察監督方式來看,提前介入手段既可以實現對刑事立案監督的補強,又充分契合偵查權的運行規律,可以作為這種強化路徑的現實選擇。
關鍵詞:環境資源犯罪;掃黑除惡;檢察監督
中圖分類號:D916.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0)24-0083-03
一、問題的提出
環境資源涉黑犯罪案件的追訴的過程,往往涉及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之間的銜接,即“兩法銜接”。在實踐中,該類案件“兩法銜接不暢”的情形經常發生,導致案件背后的涉黑因素不能被及時發現和懲治。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進入攻堅期的當下,我們有必要厘清環境資源犯罪案件“兩法銜接”不暢的原因、提出相應解決辦法,切斷黑惡勢力伸入環境資源領域的毒手。
兩法銜接不暢的原因固然是多元的,比如法律體系和信息共享平臺有待完善[1]、行政復議機關的監督職能有待加強[2]等,但筆者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于環境資源類犯罪案件中部分程序的檢察監督失靈,即部分銜接程序的檢察監督存在監督疲軟或監督不具實效的問題。
首先,破壞環境資源行為一般都是由行政執法機關首先介入處理,這就導致了環境資源犯罪的“行政從屬性”:危害環境資源的行為是否會被追究刑事責任,甚至是否存在涉黑涉惡因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行政機關的初判。在缺乏司法機關的監督和指導時,這種行政從屬性,就成為了環境刑事手段被架空的導火線。[3]其次,公安機關在收到環保行政機關移送的案件后,可以自由裁量該案件的性質。在缺乏法律監督的環境下,刑事案件被錯誤定性為一般違法的可能性必然存在,“以罰代刑”的銜接問題隨之產生。
誠然,“兩法銜接”問題的本質是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斷裂,若要從根本上解決此問題,必須要健全社會法制環境,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法治。然而,無須諱言,完全實現社會主義法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當前制度環境下解決“兩法銜接”問題,從檢察監督入手是切實可行的方案之一。
二、探尋“檢察監督失靈”的癥結所在
既然“檢察監督失靈”是導致“兩法銜接不暢”的重要原因。那么,這種“失靈”的原因究竟出在哪里?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梳理現行有效規范性文件中關于“兩法銜接”檢察監督的規定,從制度設計上尋求答案。這些規范性法律文件共有6份①,下面筆者根據這些文件,分別從司法移送監督和刑事立案監督兩方面進行分析。
(一)司法移送檢察監督
目前有效的規范性文件中,2001年“行政機關移送規定”僅對司法移送檢察監督作出了原則性規定: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應當接受檢察機關的監督。“檢察院辦理移送規定”在此基礎上規定:行政執法機關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檢察機關可以提出檢察意見。這種檢察意見只是建議性的,并沒有強制力。[4]2004年“工作聯系意見”進一步規定了監督的具體手段:檢察機關可以向行政執法機關查詢案件情況、經協商同意還可以派員查閱有關案卷材料。若行政執法機關還不配合,檢察機關可以直接請求公安機關立案,當然,也必須“經公安機關審查認為應當立案”才可以立案。可以看出,至少在2004年前后,檢察機關對司法移送的監督是非常被動的。
但是,這種情況從2006年起開始好轉。2006年“行政執法移送意見”中規定:檢察機關查詢案件情況、查閱案卷材料,行政執法機關“應當”配合。檢察機關認為應當移送的,行政執法機關“應當”移送。2017年“銜接工作辦法”進一步限定:環保部門“應當”自收到檢察意見后“3日內”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以上的這些規定,都賦予了檢察機關在司法移送過程中真正意義上的監督權。
所以,從制度上來講,我們今天已經不能說檢察機關的司法移送監督只有形式而無實質了。在今天的制度下,司法移送檢察監督程序并沒有失靈。
(二)刑事立案監督
與司法移送監督類似,在2006年之前,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立案的監督沒有具有強制力的手段。如“檢察院辦理移送規定”規定了檢察機關可以通知公安機關立案、提出檢察意見,但沒有規定這樣的通知、檢察意見具有什么效力。“工作聯系意見”規定了檢察機關可以直接通知公安機關立案,但同時規定了立案決定權在公安機關。然而,與司法移送檢察監督從2006年之后變得具有實質約束力不同,刑事立案檢察監督除了在2006年的“行政執法移送意見”中稍顯強勢外,在其他的規范性文件中,依然顯得十分羸弱。如2011年“轉發銜接工作意見”沿用了2004年“工作聯系意見”的規定,當檢察機關越過行政執法機關通知公安機關立案時,由公安機關決定是否立案。2017年的“銜接工作辦法”也只作出了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立案活動“進行法律監督”“可以啟動立案監督程序”這樣的原則性規定。
而即使在這一份稍顯強勢的“行政執法移送意見”中,檢察監督依然是處于被動的地位。根據該移送意見第八條規定,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后者“應當”在15日以內立案。但是這一檢察監督并不能由檢察院主動發起,而是必須先由執法機關提出立案監督建議。對比這一文件第三條中所規定的司法移送檢察監督既可以經“控告、舉報”,也可以“主動發現”的發起方式,我們明顯可以發現刑事立案檢察監督要“弱勢”很多。
當然,從制度的層面講,刑事立案檢察監督一般不能采取強硬的手段是合理的。就司法移送銜接程序而言,執法機關的執法權是以行政處罰權為核心的[5],對某行為是否涉嫌犯罪的判斷,并不是執法機關的主要權力內容。而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以檢察監督的方式將廣義上的司法權觸角延伸到行政執法階段,這是合法且合理的。而對于刑事立案銜接程序而言,公安機關本就是法定的立案、偵查機關[6],針對涉嫌環境資源犯罪的行為是否立案的判斷,正是公安機關的專長所在。檢察機關在進行立案監督時,必須尊重公安機關的專業性和判斷權,不能僭越權力強令公安機關立案。
從目前的規定看來,只有當執法機關提出立案監督建議的情況下,檢察機關的立案通知對于公安機關才具有強制力。②筆者認為,作出這一規定的原因在于,當行政執法機關堅決認為某一破壞環境資源的行為涉嫌犯罪甚至涉黑涉惡,以至于通過以向公安機關提請復議、向檢察機關申請立案監督的方式去爭取刑事立案時,這一破壞環境資源的行為涉嫌犯罪、涉黑涉惡的可能性是極大的。在這種情況下賦予檢察機關強令公安機關立案的權力,通過公安機關的刑事偵查來確認該破壞環境資源行為的性質,具有合理性。
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在現實中行政執法機關提請復議、申請立案監督的情形是否會經常出現?筆者對此持否定觀點:對某行為是否涉嫌犯罪和涉黑涉惡的判斷,是公安機關的專長,相較于環保部門,公安機關才是做這方面判斷的權威。在“權威效應”之下,環保部門往往會傾向于認為公安機關的判斷才是正確的。因此,執法機關一般不會向檢察機關申請立案監督。所以,現行制度唯一賦予刑事立案檢察監督以強制力的條款,也因欠缺觸發條件而只能停留在紙面上。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兩法銜接”的刑事立案監督程序中,檢察監督始終是柔性的、建議性的。這種過于羸弱的監督方式,使得公安機關實際上獲得了“立或不立”的唯一決定權;進言之,檢察機關無法以監督保障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而涉嫌環境資源犯罪的案件如果不能通過刑事立案進入訴訟程序,行為人就會因此逃脫法律的制裁,這在實踐中就表現為“以罰代刑”,這正是“兩法銜接不暢”的重要表征。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刑事立案檢察監督的羸弱性,正是“檢察監督失靈”的癥結所在,也就是檢察監督層面“兩法銜接不暢”的重要原因。
三、以提前介入機制強化刑事立案檢察監督
通過前文的分析,檢察監督在服務于環境資源犯罪案件的“兩法銜接”過程中,遇到了很尷尬的局面:一方面,刑事立案檢察監督一般不能采取強硬的手段,否則就會有權力僭越的危險;另一方面,過于羸弱的刑事立案檢察監督又無法達到權力制約的目的。那么,是否可以使用其他手段來強化檢察監督,同時保證這種強化手段不至于越權呢?筆者認為,可以嘗試以提前介入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
(一)提前介入是強化檢察監督的可行之策
當下,檢察提前介入的目的已經從“檢警合力打擊犯罪”轉變為“檢警權力體制相互制衡”,[7]更多的是偏向于強化偵查權監督。所以,提前介入的性質應當被界定為,是檢察機關立足于“監督者”這一憲法地位下,對監督手段的一種創新。既然如此,提前介入作為一種檢察監督手段,自然可以適用于涉嫌環境資源案件的刑事立案。那么,這一手段在強化立案監督問題上,有什么優勢?
筆者發現,近年來已經有一些地方在探索以檢察機關提前介入機制來完善刑事立案檢察監督,如四川省某縣檢察機關開展的“刑事立案同步監督機制改革”。在這項改革中,該縣檢察機關通過在公安機關設立“刑事立案同步監督檢察室”、制定“刑事立案巡查制度”等方式實現對公安機關立案狀況的動態監督。在監督過程中發現問題的,檢察人員通過調閱卷宗、詢問辦案人員和當事人等手段提前介入案件進行調查核實,但明令禁止檢察人員直接從事調查取證活動。同時,立案監督全程留痕、按照規定組卷歸檔。[8]
這些提前介入的手段,一是解決了“立案監督信息的來源少和渠道不暢”[9]問題,使立案檢察監督由被動變主動、由滯后變實時。二是用活了相關法律文件賦予檢察機關的具體監督手段③,通過“直接介入案件”的方式使檢察監督落實在實踐中,彌補了檢察立案監督的過分柔性。三是通過規范化組卷歸檔操作,將立案監督由“辦事”轉變為“辦案”,倒逼檢察機關充分行使監督權。這說明了,提前介入手段確實可以強化檢察監督。
(二)提前介入充分尊重偵查權的運行規律
前文已述,提前介入手段僅僅是一種檢察監督的方式。檢察機關對刑事立案提前介入時,只能靈活運用現行法律法規賦予檢察機關的具體監督手段,不能“越權監督”,更是嚴禁檢察人員直接從事調查取證活動。這說明,以提前介入方式實施的立案監督,本質上仍是“救濟式的監督”,而不是“跟班作業式的都管起來的監督”[10]。這種監督模式,符合憲法對檢察機關的定位,并沒有以檢察權去侵犯偵查權。
同時,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還有利于引導公安機關取證,為后續訴訟程序打好基礎。[11]尤其是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今天,庭審實質化的趨勢使得法院對刑事證據的審查日益嚴格。[12]而環境資源案件的特殊性卻恰恰在于原始證據容易滅失,一旦偵查階段未保存樣本,很難通過補充偵查來彌補。在此背景下,檢察機關在提前介入時,可以充分發揮專長,依照審理所需的證據標準引導公安機關取證,避免原始證據滅失。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檢察機關提前介入這一手段,可以在強化檢察監督的同時,契合偵查權運行規律,保證檢察監督權不至于權力僭越。
結語
在環境資源犯罪案件的“兩法銜接”中,檢察監督既是重要的一環,也是薄弱的一環。強化檢察監督,特別是刑事立案環節的檢察監督,對于環境資源案件涉黑涉惡因素的精準識別、精準打擊有著重大意義。強化檢察監督的方式多種多樣,本文所提及的“提前介入”手段也只是其中的一種。就這種手段本身而言,也還存在著“頂層設計有待完善、實踐探索有待豐富、具體程序有待明確”等種種問題。這些問題,仍有待我們繼續探索。
注 釋:
①這6份規范性文件是:(1)2001年《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文中簡稱“行政機關移送規定”);(2)2001年《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文中簡稱“檢察院辦理移送規定”);(3)2004年《關于加強行政執法機關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工作聯系的意見》(文中簡稱“工作聯系意見”);(4)2006年《關于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文中簡稱“行政執法移送意見”);(5)2011年《轉發國務院法制辦等部門〈關于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的意見〉的通知》(文中簡稱“轉發銜接工作意見”);(6)2017年《環境保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辦法》(文中簡稱“銜接工作辦法”)。
②這一規定見2006年“行政執法移送意見”第八條。
③如“轉發銜接工作意見”第十四條賦予檢察機關的查閱權:檢察機關在調查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舉報時,有查閱、復印案件材料的權力。
參考文獻:
[1]劉少伯,李靜.淺析環境資源領域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J].法制與社會,2018(34).
[2]唐鳳華.淺議兩法銜接應注意的問題[N].江蘇法制報,2015-12-31.
[3]趙星.環境犯罪的行政從屬性之批判[J].法學評論,2012(5).
[4]程遠.論完善檢察機關的行政監督職權——以治理以罰代刑問題為重點[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12.
[5]生態環境部行政體制與人事司.生態環境保護綜合執法的職責調整[EB/OL].
http://m.people.cn/n4/2019/0314/c4048-12449926.html.
[6]李文捷.環境犯罪偵查中的法律問題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7.
[7]但偉,姜濤.偵查監督制度研究——兼論檢察引導偵查的基本理論問題[J].中國法學,2003(2).
[8]萬毅.刑事立案同步監督機制的構建——以S省N縣檢察院的改革實踐為樣本[J].人民檢察,2017(24).
[9]陳瑩瑩.刑事檢察監督的程序化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11.
[10]朱孝清.偵查監督的工作格局[J].人民檢察,2013(14).
[11]吳楊澤.論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機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7(2).
[12]袁楓.提前介入機制的實踐革新研究[J].廣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6(2).
作者簡介:石亞文(1990—),男,漢族,湖北老河口人,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漢江分院檢察官助理,研究方向為刑法、刑事訴訟法。
(責任編輯: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