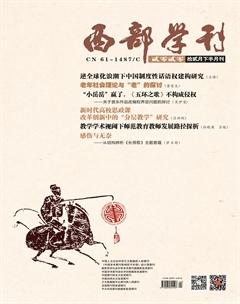網上仲裁協議的形式效力研究
摘要:網上仲裁協議是指雙方當事人在糾紛發生前或發生后,通過電子郵件或數據電文交換等形式所達成的請求仲裁的協議,或在紙質或電子合同中約定的請求仲裁的仲裁條款。應肯定以這種形式達成的網上仲裁協議具有我國《仲裁法》所規定的書面形式效力,承認網上仲裁協議的有效性就是尊重爭議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現。可以參照“功能等同法”解釋我國《仲裁法》第16條規定的“以其他書面形式”。《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第七條第二款規定只要仲裁協議中的數字化信息具備能夠調取以備日后查用的功能,即滿足書面形式之要求。而且網上仲裁協議符合《電子簽名法》第四條、第五條所規定的“書面形式”要求,因此能適用一般法之規定,以明確網上仲裁協議中電子簽名的有效性。建議依據網上仲裁協議有效的要件進而完善我國現行法律之規定。
關鍵詞:網上仲裁協議;書面要求;簽署要求
中圖分類號:D925.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0)24-0107-03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大量的電子商務糾紛頻頻發生,傳統商事仲裁機制難以適應電子商務快速發展的需要,因此網上仲裁這一新的在線糾紛解決機制應運而生。相較于傳統商事仲裁方式,網上仲裁效率高、成本低,專業性強,給人們糾紛解決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法律問題,例如網上仲裁協議的效力、網上仲裁地的“虛化”以及網上仲裁裁決的執行問題等。仲裁協議是仲裁程序的基石,是啟動網上仲裁程序的前提。若網上仲裁協議不符合現行法律規定,當事人可以基于仲裁協議無效,提出仲裁管轄權的異議。本文擬從網上仲裁協議的“書面要求”和“簽署要求”兩方面對其有效性作粗淺探討。
二、網上仲裁協議概述
(一)網上仲裁協議的定義
網上仲裁協議是一種特殊的合同,旨在證明雙方當事人同意將爭議事項提交網上仲裁的真實意思表示。雖然政府在《關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見》中提倡積極發展網上仲裁之要求,但是作為新技術的產物,網上仲裁制度尚未發展到成熟階段,現行《仲裁法》并未規定網上仲裁制度,并且對于網上仲裁協議的界定也莫衷一是。有學者認為,網上仲裁協議是通過互聯網以電子郵件或電子數據交換等形式所達成的請求仲裁的協議或是協議中所附的仲裁條款[1]。也有學者認為,網上仲裁協議包括但不限于將爭議提交網上仲裁,還可以將爭議提交線下仲裁[2]。甚至還有地方性規范文件中規定,電子仲裁協議還包括當事人達成的紙質仲裁協議①。
筆者認為,網上仲裁仍具有“傳統仲裁”的形式,應當具備傳統仲裁協議的基本要素,但又具有一定的創新。首先網上仲裁協議的適用范圍包括但不限于在網上虛擬空間所進行的活動,還包括在現實物理空間所進行的活動。其次,雙方當事人所達成的仲裁協議包括但不限于網上仲裁協議或仲裁條款,還包括其意愿將爭議提交網上仲裁的傳統書面仲裁協議或仲裁條款。最后,雙方當事人既可以將網上爭議提交網上仲裁,也可以將爭議事項提交傳統仲裁以解決糾紛。綜上,筆者認為,網上仲裁協議是指,雙方當事人在糾紛發生前或發生后,通過電子郵件或數據電文交換等形式所達成的請求仲裁的協議,或在紙質或電子合同中約定的請求仲裁的仲裁條款。
(二)網上仲裁協議的基本原理
意思自治原則為網上仲裁的可操作性提供了法律基礎。仲裁最本質的特征就是尊重雙方當事人的意愿,并且意思自治原則貫穿仲裁程序的起始。梅因爵士在他的法律進化論思想中認同了基于契約之上的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因為“權利、義務和責任都源于自愿的行為,而且是行為人之意志的結果”[3]。意思自治一般被視為是私法領域的概念,是合同領域中“契約自由”思想的具象,其核心是排除國家公權力對糾紛的管轄權,提供雙方當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從本質上來說,網上仲裁協議就是雙方當事人之間所達成的一項契約,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由決定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以實現其利益。不論是當事人之間所達成的網上仲裁協議,或是紙質或電子合同中約定的仲裁條款都應當遵循意思自治原則,不僅尊重當事人真實意愿的表達,而且有利于糾紛的快速解決,體現了仲裁制度的靈活性與張力。
三、網上仲裁協議的“書面要求”解釋與效力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仲裁法律制度以及我國《仲裁法》都要求仲裁協議應當具備書面形式,但是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電子商務的形式從傳統的書面形式轉化為無紙的數字化形式。因此,以電子郵件或電子數據電文交換等形式達成的網上仲裁協議是否符合我國《仲裁法》對書面的要求,就成為認定該仲裁協議是否有效的前提。
筆者認為,應肯定以這種形式達成的網上仲裁協議具有我國《仲裁法》所規定的書面形式效力。首先,承認網上仲裁協議的有效性是尊重爭議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現。仲裁協議是整個仲裁制度的基石。傳統仲裁協議的重要性體現在對仲裁參與人、仲裁機構以及法院三方的約束上。于當事人,仲裁協議是雙方自愿將可能發生的或已經發生的爭議提交仲裁的“證據”;于仲裁機構,是其獲得仲裁管轄權的唯一依據;于法院,則對其產生了妨訴抗辯之效力。因此,不能因為仲裁協議的載體不同而否定爭議主體的真實意思表示[4]。
其次,傳統以書面方式簽訂的形式不能滿足互聯網環境下電子商務活動的需要。在互聯網的助推下,電子商務突破了時空、地域的局限性,在開放的網絡環境中為消費者提供商品服務。電子商務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數量大、地域分布廣等特點,交易主體通常以電子合同的形式達成合意。作為新技術的產物,網上仲裁制度應契合電子商務糾紛的特點,放寬仲裁協議書面形式的認定,肯定雙方當事人仲裁合意的同時也保障仲裁的快捷性高效性。
最后,承認網上仲裁協議的效力是各國仲裁立法的大勢所趨,但是各國對仲裁協議“書面要求”的理解各不相同。例如1996年英國《仲裁法》第五條對“書面要求”作了擴大解釋,只要有證據證明該形式能夠依附于某一載體即滿足“書面形式”之要求。1998年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031條第一款規定仲裁協議可以存在于電傳、電報或可提供協議記錄的其他電訊手段中[5]。
我國現行法律雖然并沒有明確規定網上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但是在一定程度也肯定了網上仲裁協議的效力,即我國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對《仲裁法》第五條的“其他書面形式”作了擴大解釋,其他書面形式包括以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等形式達成的請求仲裁的協議。固然,采用擴大解釋的方式能賦予網上仲裁協議以明確法律效力,但并未涉及到該問題的本質。例如我國在《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限定了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互聯網時代,新興技術日新月異,一旦出現了新的技術形式,就必須重新對書面形式作新的擴大解釋,否則容易造成立法資源的浪費。
為適應快速崛起的電子商務交易活動,擴大仲裁協議的“書面形式”之外延是必然趨勢,筆者認為可以參照《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第7條第二款的立法技術——“功能等同法”解釋我國《仲裁法》第16條規定的“以其他書面形式”。《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第7條第二款規定只要仲裁協議中的數字化信息具備能夠調取以備日后查用的功能,即滿足書面形式之要求。該條采用了“功能等同法”解釋其他書面形式之規定。所謂的“功能等同法”是指對傳統書面仲裁協議加以分析,從中抽象出功能標準,再將數據電文的效力與紙面形式的功能進行類比,并找出具有相應效果的手段,以確定其效力[6]。采用功能等同法進行解釋的可行性在于:雙方當事人在爭議發生后,必須提交相應的“證據”作為提起訴訟或仲裁的依據,因之,有效的傳統仲裁協議必須具備書面形式。對于網上仲裁協議中的數字化信息是否滿足現行《仲裁法》對書面要求的規定這一問題,其本質在于什么樣的數據電文可以視為法律所要求的書面形式[7]。申言之,什么樣的數據電文可以作為提起請求仲裁的“證據”。相較于對“書面形式”進行擴大解釋,采用“功能等同法”進行解釋,不僅提升網上仲裁協議產生形式的適用空間,還擴大了法律的確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張力。只要網上仲裁協議能夠達到與傳統仲裁協議異曲同工之作用,就應將視為符合現行《仲裁法》對仲裁協議之“書面要求”的規定。
四、網上仲裁協議的“簽署要求”解釋與效力
“書面形式”證明了網上仲裁協議的存在,而簽名則表示交易雙方達成了仲裁合意。一份有效的仲裁協議需要由當事人對協議中的內容進行簽名確認,該協議在沒有特殊規定或約定的情況下,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蓋章時成立。傳統形式的簽署方式不符合電子商務的現實需求,目前各國通行的做法是以電子簽名代替傳統簽名,并且根據功能等同原則,賦予電子簽名與傳統簽名同等的法律效力。我國《電子簽名法》第14條也充分肯定了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雖然我國《仲裁法》并未規定網上仲裁制度,但是網上仲裁協議符合《電子簽名法》第四條、第五條所規定的“書面形式”要求,因此能適用一般法之規定,以明確網上仲裁協議中電子簽名的有效性。
此外,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得電子商務的形式具有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在簽署方式上也有體現。網上仲裁協議的簽署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電子簽名。例如,人們可能通過“點擊”或“勾選”等操作行為達成與網絡平臺之間的仲裁條款。此類仲裁條款一般存在于網絡平臺事先擬定好的電子格式合同中。由于我國現行法律對網上仲裁協議的簽署方式的規定闕如,因此交易相對人的“點擊”或“勾選”等操作行為是否具有與電子簽名同等的法律效力有待商榷。有部分學者從功能等同的角度肯定了此類操作的法律效力。也有部分學者持否定觀點,認為此類操作違背了意思自治原則,交易相對人可能未完成瀏覽用戶協議的內容而直接點擊“我同意”選項,顯然在此種情況下,這種點擊行為并不意味著交易相對人真實意思表示[8]。
如前文所述,網上仲裁條款一般存在于網絡交易平臺經營者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的電子格式合同中,且訂立該合同時并未與合同相對人進行溝通與協商,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同時,有可能影響合同相對人真實意思表示。雖然通過“點擊”或“勾選”等確認形式以達成的網上仲裁條款犧牲了交易相對人部分的意思表示,卻是數字化時代電子商務發展的必然趨勢。此類操作行為是否具有與電子簽名同等的法律效力,質言之,即探討用戶與平臺之間所達成網上仲裁條款是否違背當事人意思表示以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一份有效的網上仲裁協議(或網上仲裁條款)應當滿足三個要件[9]:第一,該網上仲裁條款本身是否具有正當性。網上仲裁協議或是網上仲裁條款的正當性是仲裁程序啟動的前提保證,也是合同成立的要件之一。第二,網絡平臺經營者提供電子合同時是否對涉及到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條款履行明示、告知義務。例如《網絡交易平臺合同格式條款規范指引》第7條以及《電子商務法》第33條均規定應確保交易相對人能便利、完整地閱覽和保存網站內的電子合同格式條款。第三,交易相對人是否有機會能審閱電子格式合同中的實質性條款,且是否能以一定方式對該條款作出其意思表示。
基于現行法律規定以及目前的司法實踐,網上仲裁協議的簽署方式,包括簽訂確認書,使用電子簽名以及通過“點擊”或“勾選”等行為進行操作。肯定網上仲裁協議中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并無爭議,但是關于網上格式仲裁協議或電子格式合同中所附的格式條款的效力,我國既沒有相應的司法實踐,也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因此存有完善的空間。
第一,為了防止電子格式合同中存有不利于交易相對人的實質性條款,網絡平臺經營者應當確保交易相對人有機會瀏覽、閱讀電子格式合同,履行《合同法》規定的“明示”“告知”義務。例如設置閱讀協議的時間、置頂格式合同中的爭議解決方式,或采用“放大字體”“標紅標亮”“加粗畫線”等形式以提示交易相對人。此外,對于電子格式合同中存在的專業術語應當盡到說明義務,或以超鏈接的方式提供相應的法律規定以供交易相對人參考。雖然我國《合同法》第39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均規定了經營者的明示、告知義務,但是并未界定何為合理的方式或顯著的方式提請交易相對人注意。
第二,網絡平臺經營者應當確保交易相對人有能以一定的行為對該實質性條款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由提供電子格式合同的一方主體在設計電子格式合同時,利用網絡技術將合同內容分為必備條款和可選條款,使得交易相對人能夠根據自己的真實意思勾選合同中的條款,讓預先擬定的、未與交易相對人協商的網上仲裁條款轉化為交易相對人所認同的條款,符合有效民事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的同時也保障其意思表示真實。
第三,網絡平臺經營者應當在與交易相對人簽訂主合同或當事人以履行義務的形式使合同成立時,應當將交易相對人通過“點擊”或“勾選”等操作行為形成的網上格式仲裁協議或電子格式合同,以郵件或其他數據電文形式發送至交易相對人,以作為日后產生網絡爭議提請仲裁的“證據”。通過信息技術手段將交易相對人“點擊”或“勾選”等操作確認行為轉化為電子文件的形式,滿足仲裁協議的形式要件之規定,即“能夠調取以備日后查用”,保障了交易相對人的程序性權利,同時也維護了電子商務交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注 釋:
①中國廣州仲裁委員會《網絡仲裁規則》第5條? 第一款? 網絡仲裁協議應當采取書面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當事人在紙質或者電子合同中訂立的仲裁條款。
參考文獻:
[1]李虎.網上仲裁法律問題研究[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4.
[2]何其生.論電子仲裁協議的要件[J].法學評論,2003(4).
[3]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4]何其生.論電子仲裁協議的要件[J].法學評論,2003(4).
[5]武丹楓.網上仲裁協議的效力分析[D].上海:復旦大學, 2010.
[6]呂國民.數據電文的應用所帶來的若干法律問題探析[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
[7]汪振林.電子證據學[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
[8]王偉.電子仲裁協議的形式與效力研究[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
[9]喬仕彤,何其生.電子格式合同中仲裁條款的效力——以中國消費者市場中Microsoft軟件最終用戶許可協議為例[J].武大國際法評論,2007(2).
作者簡介:王夢露(1994—),女,漢族,浙江溫州人,單位為重慶大學法學院,研究方向為訴訟法學。
(責任編輯: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