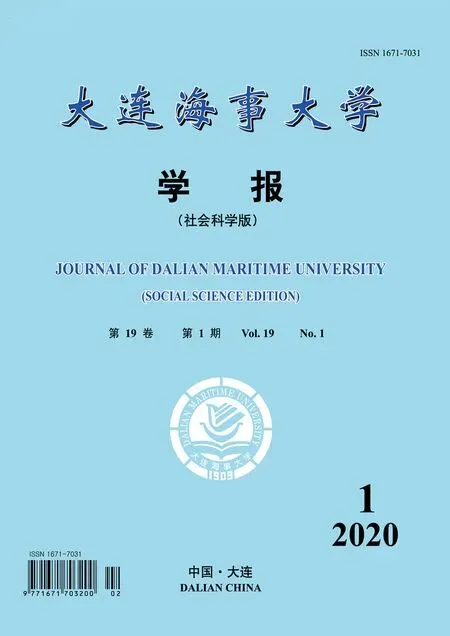《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問題
許 卉
(清華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4)
一、問題的提出
2007年3月,兩艘中國籍船舶“恒冠36”輪與“遼長漁6005”輪在威海水域發生碰撞導致燃料油泄漏,引發油污損害賠償糾紛。(1)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四他字第20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非航行國際航線的我國船舶在我國海域造成油污損害的民事賠償責任適用法律問題的請示的答復》。“恒冠36”輪所有人申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以下簡稱《海商法》)第11章的規定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但異議人認為依據《海商法》第208條、《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條例》(以下簡稱《防污管理條例》)(2)國務院發布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已于2010年3月1日起實行,并于2018年修正,因此國務院于1983年12月29日發布的《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條例》已廢止。第13條的規定,本案應適用2000CLC公約,(3)2000CLC公約是《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議定書》2000年修正案的簡稱,該公約最初的版本是《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國際海事組織對其進行了兩次修正。第一次修正《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的1992年議定書由國際海事組織在1992年11月27日于倫敦簽訂。經國務院批準,我國于1999年1月5日向國際海事組織交存了《〈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1992年議定書》(簡稱1992CLC公約)加入書,成為締約國,并于2000年1月5日在我國生效。第二次修正是國際海事組織于2000年10月召開的法律委員會第82屆會議通過了對經1992年議定書修正的《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的修正案,即《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議定書》2000年修正案,該修正案于2003年11月1日在我國生效。需要說明的是,因“閩燃供2”輪案件發生于1999年,因此本文在該案中使用的簡稱是1969CLC公約;因“恒冠36”輪案件發生于2007年,因此本文在該案中使用的簡稱是2000CLC公約。但是在后文的論證部分,為了便于闡述,本文使用的簡稱是CLC公約。而非我國國內法。該案一波三折,經青島海事法院、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后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最高人民法院答復認為,本案不含有涉外因素,不適用CLC公約,應當適用我國國內法。
1999年3月,兩艘中國籍船舶“閩燃供2”輪與“東海209”輪在廣州港水域發生碰撞導致燃料油泄漏,同樣引發了油污損害賠償糾紛。(4)參見廣州海事法院于2000年2月17日做出的裁定書(法寶引證碼:CLI.C.22278)。“閩燃供2”輪所有人申請依據1969CLC公約設立本次事故油污損害賠償責任限制基金的計算單位,但是異議人認為本案不含有涉外因素,且依據《防污管理條例》第13條,(5)《防污管理條例》第13條規定,“航行國際航線、載運二千噸以上的散裝貨油的船舶,除執行本條例規定外,并適用于我國參加的《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異議人認為該條例適用的船舶是指航行國際航線或載運2000噸以上的散裝貨油的船舶,“閩燃供2”輪是航行國內航線、載運2000噸以下散裝貨油的船舶,“閩燃供2”輪不屬該條例所調整的船舶,因此,本案不能適用《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本案只能適用我國的國內法。廣州海事法院經審理于2000年2月17日裁定本案適用1969CLC公約。
鑒于“閩燃供2”輪案是我國首例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適用的案例,(6)分別以“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海商法”等作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北大法寶、法信網、互聯網等渠道檢索,截至2019年4月23日,“閩燃供2”輪案是能夠檢索到的唯一一個CLC公約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適用的案例。因此有必要對自2000年“閩燃供2”輪案判決以來,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司法實踐、司法解釋、相關法律法規等方面的變化做一個梳理,見表1。

表1 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司法實踐、司法解釋、法律法規中的應用和規定
從表1可以看出,“閩燃供2”輪案雖然打破了國際公約只能適用于涉外案件的思維桎梏,但是該案的裁定沒有成為其他法院在處理類似案情的通行做法,在此后的十余年中,CLC公約再沒能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中適用。最高法院無論是在下發的審判工作通知中,還是對具體案件的處理意見上,都明確表達出CLC公約只能適用于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觀點,直至2011年1月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對該問題予以了回避。2018年3月由國務院發布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以下簡稱《防治海洋環境條例》)(7)《防治海洋環境條例》第50條規定:“船舶污染事故的賠償限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關于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的規定執行。但是,船舶載運的散裝持久性油類物質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海域污染的,賠償限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的規定執行。”第7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對防治船舶及其有關作業活動污染海洋環境有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為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開辟了一條新的解釋路徑。
“恒冠36”輪和“閩燃供2”輪兩起案件中的涉事船舶有著相同的國籍、相似的“經歷”,但是在油污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上卻有著截然相反的“歸宿”,單就該兩起案件而言,可謂是塵埃落定,適用的法律已顯而易見。但是,兩起案件背后有關CLC公約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所引發的爭議和碰撞,以及相關司法解釋和法律規定的發展動態需要進一步深入挖掘和認真探討,從而明確CLC公約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避免再次出現“同案不同判”的情況。
二、CLC公約適用前提的困境:涉外性之爭
(一)涉外性是CLC公約適用前提的爭議因由
國際條約與我國國內法的關系一直以來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之一,究其根源是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條約程序法》均未對國際條約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做出明確的原則性規定,有關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的效力優先關系只是散落在我國不同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之中,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142條、《海商法》第268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260條。但是上述法律條款均是在涉外篇章下的規定,因此有學者提出“法律關系中含有涉外因素是國際條約適用的前提”[1-2]這一觀點。基于“國際條約的適用只能是針對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關系”[3-5]這一前提,作為國際條約之一的CLC公約當然被限定在了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這一范圍之內。雖然也有學者提出“涉外性并非所有國際條約直接適用的前提條件,有些國際條約按照其自身關于適用范圍的規定和締約國的保留情況,對締約國境內非涉外法律關系具有拘束力”[6]15[7],但是隨著2005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的出臺,其第141條“我國加入的《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適用于具有涉外因素的締約國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包括航行于國際航線的我國船舶在我國海域造成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非航行于國際航線的我國船舶在我國海域造成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不適用該公約的規定”,已明確我國最高法的態度是CLC公約不適用于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
(二)CLC公約局限于涉外性與否的重新解讀
1.CLC公約適用范圍的界定
首先,國際公約有兩種類型:一是世界統一型,是指世界各國無論是國內私法關系還是涉外私法關系,均適用相同的法律;二是萬民法型,是指僅調整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8]因此,就國際公約的類型而言,國際公約并非被局限于涉外法律關系中適用。國際公約的適用范圍是由其自身法律條文所規定的,因此有些公約只能適用于涉外法律關系,例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8)《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條第1款規定:“本公約適用于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貨物銷售合同:(a)如果這些國家是締約國;或(b)如果國際私法規則導致適用某一締約國的法律。”但是有些國際公約的適用范圍不局限于涉外法律關系,例如《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9)《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第1條第1款:“本規則條款適用于在公海和連接公海可供海船航行的一切水域中的一切船舶。”
其次,CLC公約第2條第1款規定,“‘船舶’系指為運輸散裝油類貨物而建造或改建的任何類型的海船和海上航行器”,該條款沒有對船舶國籍做出區分;第3條規定,“本公約僅適用于:(a)在下列區域內造成的污染損害:(i)締約國的領土,包括領海;和(ii)締約國按照國際法設立的專屬經濟區;或者,如果締約國未設立此種區域,則為該國按照國際法確立的,在其領海之外并與其領海毗連的,從測量其領海寬度的基線向外延伸不超過200海里的區域;(b)不論在何處采取的用以防止或減少此種損害的預防措施”,該條款沒有對公約的適用范圍做出涉外性要求。從CLC公約自身關于其適用范圍的規定以及我國在加入CLC公約時未做出保留的層面而言,涉外性不構成CLC公約在我國適用的前提條件。
最后,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第141條已明確規定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不適用CLC公約,但是該條表明的僅是最高法于2005年關于該問題在審判工作中所持有的審判觀點,不能據此就否定CLC公約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
2.立法上的解釋路徑
第一,雖然《民法通則》第142條、《海商法》第268條和《民事訴訟法》第260條關于“國際條約優先于國內法適用”的內容均是在涉外篇章下的規定,但是上述法律條款只是強調在涉外法律關系中“國際條約優先適用”的原則,而不是強調國際條約在我國的適用范圍,[6]16不能反向推斷出涉外性是國際條約適用的前提這一結論。因此,以上述條款是在涉外篇章下的規定為由,否定CLC公約在非涉外法律關系中適用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6條、《防治海洋環境條例》第73條以及《海商法》第208條關于“國際條約優先適用”的內容沒有被規定在涉外篇章之下,上述條款內容不受是否以涉外性為適用前提的“爭議”,為CLC公約在非涉外法律關系中的適用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第三,《海商法》為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提供了法律依據。《海商法》第208條規定,“本章規定不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規定的油污損害的賠償請求”。該條款是在“第十一章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篇章下的規定,CLC公約是“我國參加的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依據該條款,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應當適用CLC公約。
第四,《防治海洋環境條例》給出了一條CLC公約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適用的解釋路徑。[9]《防治海洋環境條例》第50條第2款規定,“船舶載運的散裝持久性油類物質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海域污染的,賠償限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的規定執行”。CLC公約是我國加入的含有賠償限額內容的國際公約,因此該條例同樣是從國內立法上明確了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
第五,具有“法際私法”功能的條款指明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應當適用CLC公約。“‘法際私法’是指解決一國民商法中不同法律、法規之間沖突的法律,如國際法與國內法、成文法與習慣法、一般法與特殊法相互沖突時,決定優先適用哪一法律的規范就是‘法際私法’。”[10]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問題上,其沖突在于應當適用CLC公約還是我國國內法,解決該問題的鑰匙正是“法際私法”。在我國國內法中,《民法通則》第142條、《海商法》第268條、《民事訴訟法》第260條、《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6條、《防治海洋環境條例》第73條和《海商法》第208條均具有“法際私法”的功能,其內容均是適用國際公約。著眼于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具有“法際私法”功能的上述條款均指明應當適用CLC公約而非我國國內法。
三、CLC公約適用方式的抉擇:雙軌制之論
(一)CLC公約雙軌制適用方式的成因
CLC公約在我國應當采取雙軌制這一適用方式的成因源于國際公約的制定初衷。各國努力制定國際公約的目的在于解決各國立法不統一給國際經濟貿易交往、國際航運帶來的不便,從而給國際民商事活動提供一套統一的國際行為規則,因此國際公約的初衷是適用于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中。[3]有鑒于此,CLC公約在我國的適用應該施行雙軌制,即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應當適用CLC公約,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應當適用我國國內法的規定。[11]
(二)CLC公約在中國適用方式的重新確立
1.CLC公約雙軌制適用方式的弊端
第一,雙軌制的適用方式不符合CLC公約的制定目的。國際公約的制定目的不僅在于消除各國立法不統一所產生的法律沖突,其目的同樣在于對某一特定領域不合理的法律歧視進行補救,(10)例如《海牙規則》的制定目的不在于消除各國立法不統一而產生的沖突,而是為了解決承運人濫用權利,在提單中大肆增加大量的不合理免責條款這一難題。也在于填補法律的空白。[12]回顧國際海上油污損害賠償法律制度的發展歷程,1969CLC公約的誕生源于1967年的“Torrey Canyon”案件,當時現有的法律制度完全不足以處理該案中船舶污染的后果,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法律制度來解決“Torrey Canyon”案件帶來的問題。根據英國提出的請求,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開始著手處理這一問題,并促成了1969CLC公約的誕生。[13]可見CLC公約的誕生源于填補海上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制度的法律空白,而不是為了消除各國有關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立法不統一所產生的法律沖突。因此CLC公約雙軌制的適用方式并沒有公約制定目的上的依據。
第二,雙軌制的適用方式無益于海洋環境的保護。海洋的局部污染會造成整個海洋生態環境的破壞,因此海洋環境的保護是超越國界的,而“作為規制這一具有整體影響性的污染行為的法律制度也應當是統一的”[14]184。如果以涉外因素作為劃分標準對涉外和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采用雙軌制,適用不同的法律規定和不同的賠償限額,不僅于CLC公約所致力于保護的海洋環境無益,而且與CLC公約的制定目的相背離。
第三,雙軌制的適用方式導致法律威懾力減弱。鑒于CLC公約中規定的賠償限額比我國國內法中規定的賠償限額高,因此如果我國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適用內外有別的法律制度,對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適用CLC公約中規定的較高賠償限額,對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適用我國國內法中規定的較低賠償限額,則難免會使一些主營國內航海運輸的企業在權衡成本和收益之后存在僥幸心理,淡薄海洋保護意識,疏于防范船舶油污事故從而埋下隱患,不僅導致法律的立法本意無法實現,而且會造成法律的威懾作用難以得到發揮。
第四,雙軌制的適用方式不符合締約國的信守義務。我國是國際海事組織(IMO)的成員國,根據《執行IMO強制文書守則》中的內容,(11)Cod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datory IMO Instruments, Resolution A.973(24), Adopted on 1 December 2005(Agenda item 9).“成員國應當在本國進行相應的立法以保證本國的立法和措施符合其加入的國際海事公約的要求,從而保證公約的有效執行”[15]。我國雖然沒有針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這一問題進行專門立法,但是我國在《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6條、《防治海洋環境條例》第50條和《海商法》第208條中已經明確規定適用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與海洋環境保護有關的國際公約——CLC公約,我國應當信守“條約必須遵守”的原則,遵守《執行IMO強制文書守則》以及我國國內法的相關規定。因此,以是否具有涉外因素為劃分標準,對涉外和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采用雙軌制,不僅不符合“條約必須遵守”的國際義務,而且也不符合我國國內法的規定。
2.CLC公約在其他締約國適用方式的立法比較
在加拿大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中,CLC公約優先于國內法適用,無須區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中是否含有涉外因素,只有當CLC公約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中的爭議沒有規定時,才適用相關的國內法對CLC公約中沒有做出規定的爭議內容進行補充規定。加拿大三面環海,不僅是航運經濟大國之一,而且在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法律制度方面也較為完善,其不僅較早加入了CLC公約,而且通過《海事責任法》等相關國內立法彌補了CLC公約規定中的不足和空白。在協調國內法與CLC公約在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法律適用問題上,加拿大不是以法律關系中是否具有涉外因素來決定是適用CLC公約還是其國內法,而是以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在CLC公約中是否有明確規定作為法律適用的確定標準:對于公約內規定的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優先適用CLC公約;對于公約外規定的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則適用國內法。[16]因此,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在加拿大的法律適用問題上,無論是否具有涉外因素,都優先適用CLC公約,只有當CLC公約中沒有規定時,才適用國內法的規定。
在英國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中,鑒于英國將CLC公約轉化為國內法適用,使英國相關國內法在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問題上的主要條款內容與CLC公約的內容基本一致,避免了涉外船舶和非涉外船舶在油污損害賠償糾紛的法律適用方面出現爭議的情況。英國有關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國內立法主要是《1995年商船法》。(12)Merchant Shipping Act 1995.該法第三章“油污責任”的規定與1992CLC公約的規定基本一致,其中第157條第2款關于油污損害賠償限額的規定也與1992CLC公約中規定的賠償限額完全一致。2003年,英國針對《1995年商船法》中規定的油污賠償限額進行了修改,即《1995年商船法(油污賠償限額)2003年規則》(13)The Merchant Shipping (Oil Pollution Compensation Limits) Order 2003.。修改后的油污損害賠償限額與2000CLC公約中規定的賠償限額完全一致。由此可見,英國是將CLC公約轉化為國內法,使有關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這一法律問題在國際公約與國內法層面上的規定保持一致,而無須區分船舶是否具有涉外性。
新加坡同樣是將CLC公約轉化為國內法適用的國家,新加坡在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方面的國內法中的適用范圍、責任限制、賠償限額等規定與CLC公約中規定的內容基本一致。新加坡有關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國內立法是《商船運輸(民事責任和油污賠償)法案》,(14)Merchant Shipping (Civil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Act.該法案最初于1981年12月生效,中間歷經9次修改,目前現行有效的是于2008年修訂之后的法案。該法案于開篇便明確其制定目的是“使CLC公約在本國發生效力,并為與CLC公約相關的事項做出一般性規定”。該法案第二部分“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中規定的適用范圍、責任限制、賠償限額等規定與2000CLC公約中規定的內容基本一致。新加坡同樣是將CLC公約轉化為國內法適用的國家,使得涉外與非涉外船舶在油污損害賠償方面具有相同的法律規定。
此外,澳大利亞的《1981年海洋保護(民事責任)法》、(15)Protection of the Sea (Civil Liability) Act 1981,目前現行有效的是2016年修正之后的版本。該法采納了CLC公約中的部分條款作為該法中的一部分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澳大利亞的國內法中有關油污損害賠償中相關概念的定義、適用范圍、責任限制、賠償限額等規定均與CLC公約中的規定一致。德國的《海上船舶油污損害賠償責任和賠償法》、(16)Gesetz über die Haftung und Entsch?digung für ?lverschmutzungssch?den durch Seeschiffe (?lschadengesetz - ?lSG). 該法吸收了CLC公約中的部分條款規定,例如該法第一部分明確規定有關船舶油污損害的責任和賠償依據CLC公約等國際協定;第六部分“管轄權”中明確提出,有關索賠的爭議適用1992CLC公約中的第3條、第4條和第7條第8款的規定。丹麥的《商船法案》、(17)Merchant Shipping Act (Consolidation),Consolidated Act no. 1505 of 17 December 2018 issued by the Danish Maritime Authority. 該法第十部分伊始就明確提出本部分有關船舶油污損害的責任和賠償的制定依據之一即是1992CLC公約。日本的《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保障法》(18)《船舶油濁損害賠償保障法》(昭和五十年法律第九十五號)。日本于1975年12月(昭和五十年十二月)頒布《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保障法》,將其加入的CLC公約納入國內法體系,目前現行有效的是2018年5月(平成三十年五月)修訂之后的版本。該法中有關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責任限額等內容與CLC公約大多相同,因此船舶本身是否具有涉外性在日本不會導致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適用于不同的法律規定。、韓國的《油污損害保障法》(19)該法中有關船舶油污損害的規定與CLC公約中的規定基本一致,其中第8條規定的油污損害賠償限額也與CLC公約中規定的賠償限額一致。中有關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的適用范圍、責任主體、賠償限額等主要條款與CLC公約中的規定也基本一致。
3.CLC公約在中國適用方式的重構
截至2019年5月,CLC公約的締約國合計138個。(20)參見IMO于2019年2月20日發布的CLC.6/Circ.80文件,其中圭亞那雖然已經加入CLC公約,但是CLC公約將于2020年2月20日對圭亞那發生法律效力。“對于任何國家來講,參加國際公約不是最終目的,其最終目的應當是通過公約在本國的正確實施,通過公約對油污加害方與油污受害方權利義務的平衡,從而促進海洋環境的保護和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17]從上述CLC公約締約國中航運經濟大國有關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國內立法可以看出,上述國家的國內立法均與CLC公約接軌,除加拿大采取國內法與CLC公約相結合的法律適用模式,用其國內法彌補CLC公約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之外,其他國家如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德國、丹麥、日本、韓國都是采取將CLC公約納入其國內法體系的做法,使其有關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國內法與至少是CLC公約中的主要條款保持一致,而非因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法律關系中是否具有涉外因素而適用不同的法律和不同的賠償限額,使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清晰和明確,成功避免了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出現法律適用混亂的情況。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18年海運述評報告顯示,以載重噸計算,我國是世界第三大船舶所有國,占世界總量的9.59%;按吞吐量計算,世界前20名的港口中,中國港口有13個,占比達65%。(21)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8, by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pp.30-66.因此我國是世界航海經濟大國之一。不僅如此,我國海關總署發布的2018年12月進出口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進口原油4.62億t,同比增長10.1%,[18]因此我國也是原油進口大國。進口的原油主要靠船舶航運,進口原油數量的增多,必然會導致海上溢油事故風險的增大。有鑒于此,在我國國內法沒有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問題做出專門立法、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尚存爭議,以及CLC公約締約國中的主要航運大國在本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均是適用與CLC公約主要條款相一致的規定的現狀之下,我國應當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中適用CLC公約,通過規范和統一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解決目前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在我國法律適用方面出現的“同案不同判”的困境。
四、CLC公約適用后果的沖突:利益衡量之辯
(一)否定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適用的緣由
CLC公約中規定的賠償限額較高,超出了我國從事沿海運輸企業的承受能力,不利于我國沿海運輸業的發展。大多數從事我國沿海內河運輸的船舶屬于中小型船舶,且掛靠經營盛行,與從事國際運輸的船舶相比,其經濟實力、安全技術標準和管理規范等方面都相對較低。如果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適用CLC公約,則導致的結果是即使低于5000總噸的中小型船舶,也要適用CLC公約中規定的最低賠償限額——451萬特別提款權,如此高額的賠償限額超出了船舶所有人的負擔能力,很有可能導致船舶所有人的破產,遏制沿海運輸業的發展。因此,CLC公約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適用,將導致適用CLC公約中較高的賠償責任限額,不利于我國沿海運輸業的發展。[14]183
(二)CLC公約賠償限額的重新審視
1.中國國內法和CLC公約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限額規定比較
目前我國國內法和我國加入的國際公約中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限額做出具體規定的是交通部《關于不滿300總噸船舶及沿海運輸、沿海作業船舶海事賠償限額的規定》、《海商法》和CLC公約。依據這三部法律,不同噸位的船舶所承擔的賠償限額見表2。

表2 適用交通部規定、《海商法》和CLC公約賠償限額比較 萬SDR
從表2中的數據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1969CLC公約中的賠償限額相對較低,并且按船舶的實際噸位確定賠償限額,在船舶噸位為500噸以下時,1969CLC公約的賠償限額低于我國交通部《關于不滿300總噸船舶及沿海運輸、沿海作業船舶海事賠償限額的規定》中的賠償限額,在船舶噸位為50 000噸以下時,1969CLC公約的賠償限額低于我國《海商法》中的賠償限額。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在前述“閩燃供2”輪案中,申請人向法院申請以1969CLC公約作為確定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限額的法律依據的原因。
(2)1992CLC公約以及2000CLC公約均對1969CLC公約中最初設定的賠償限額進行了大幅修改,并且均以船舶噸位在5000噸作為賠償限額的起算值,換言之,即使船舶噸位小于5000噸,也要按船舶噸位為5000噸來確定賠償限額。修改后的1992CLC公約和2000CLC公約中規定的賠償限額均明顯高于我國國內法對賠償限額的規定,這同樣也從另一個側面解釋了在前述“恒冠36”輪案中,申請人向法院申請以我國《海商法》作為確定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限額的法律依據的原因。
(3)與目前現行有效的2000CLC公約相比,我國國內法所規定的油污損害賠償限額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這無疑將會引發兩個潛在風險:第一,當賠償限額低于潛在的油污損害賠償金額時,就會出現法律威懾不足的風險,從而導致船舶所有人缺乏足夠的責任心來采取足夠必要的安全預防措施避免船舶油污事故的發生;第二,從經濟學的角度考慮,如此低的油污損害賠償限額將會導致無法反映出由于船舶溢油污染所造成的真實社會成本。[19]
通過比較我國國內法和CLC公約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限額的規定可以看出,誕生之初的1969CLC公約中規定的賠償限額較低,低于我國國內法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閩燃供2”輪案適用了1969CLC公約。但是此后1992CLC公約和2000CLC公約均對賠償限額做出了大幅修改,修改之后的賠償限額已遠高于我國國內法的規定,在此種情況下,CLC公約再沒有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適用。但是,法律適用是一回事,懲罰力度是另外一回事,以懲罰力度過重為由阻止法律的適用無疑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
我國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制度,對于涉外和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均應當致力于對損害進行充分賠償,但是,我國立法現狀無法滿足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的賠償需求,油污損害一直處于較低的賠償水平,得不到充分的賠償。[20]與我國對船舶油污損害的立法現狀不同,CLC公約對船舶油污損害的賠償是充分賠償。CLC公約前言部分就已經明確公約的目的是“意識到由于遍及世界的海上載運散裝油類而出現的污染危險,確信有必要對由于船舶逸出或排放油類造成污染而遭受損害的人員給予充分的賠償,本著通過統一的國際規則和程序以便確定在上述情況下的責任問題并提供充分賠償的愿望,議定下列條款”。其中CLC公約英文原文用的是“adequate compensation”,“adequate”這個詞在《韋伯詞典》中有兩個釋義:(1)sufficient for a specific need or requirement;(2)lawfully and reasonably sufficient。在《元照英美法詞典》中,“adequate compensation”被翻譯為“充分補償”。可見CLC公約的立法宗旨是對船舶油污損害給予“充分賠償”而非“適當賠償”。因此CLC公約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有其合理性。
2.CLC公約在非涉外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已有中國保險制度的保障
首先,在保險義務方面,CLC公約和我國國內法均對船舶所有人的船舶油污強制保險義務做出了明確法律規定。CLC公約第7條規定,“在締約國登記的載運2千噸以上散裝貨油的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必須進行保險或取得其財務保證”。我國交通運輸部下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實施辦法》)(22)《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實施辦法》最初的文件是交通運輸部令2010年第3號,交通運輸部于2013年進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文件是交通運輸部令2013年第11號。第8條、第9條同樣規定了船舶所有人的強制保險義務,其中第9條的強制保險義務規定甚至比CLC公約第7條的規定更為嚴格。此外《海洋環境保護法》第66條、《防治海洋環境條例》第51條均規定了船舶所有人的船舶油污強制保險義務。可見我國國內法已經對船舶所有人的油污強制保險義務做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
其次,在保險額度方面,我國國內法已經對CLC公約中規定的賠償限額做出了相對應的最低保險額度的法律規定。交通運輸部下發的《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實施辦法》第5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海域內航行的載運散裝持久性油類物質的船舶,投保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或者取得其他財務保證,應當不低于以下額度:(一)5000總噸以下的船舶為451萬特別提款權;(二)5000總噸以上的船舶,除前項所規定的數額外,每增加一噸,增加631特別提款權,但是,此總額度在任何情況下不超過8977萬特別提款權。”該條所規定的船舶油污損害保險的最低限額451萬特別提款權和最高限額8977萬特別提款權與現行有效的2000CLC公約中所規定的最低和最高賠償限額是一致的。可見我國國內法已經在保險額度方面做出了與CLC公約所規定的賠償限額相對應的法律規定,在國內法層面上保障了船舶所有人賠償風險的分散。
船舶油污保險制度的作用在于,借助保險公司的經濟實力,一方面解決應急情況下清污啟動資金的問題,保障海洋環境得到及時、有效的清理和修復;另一方面保障船舶污染損害的賠償,起到分散船舶所有人賠償風險的作用。[21]鑒于我國國內法已經在保險義務和保險額度方面均做出了與CLC公約相接軌的法律規定,因此CLC公約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保險制度作為保障,船舶所有人依據CLC公約中規定的賠償限額對非涉外油污損害進行賠償的風險已經能夠得到足夠的分散。
3.適用CLC公約規定的賠償限額有利于改善中國沿海運輸業現狀
第一,美國有關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立法實踐給我國沿海運輸業現狀的改變帶來一定的啟示。美國有關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國內立法是《1990年油污法》(OPA),該法所規定的賠償制度比1969CLC公約中的規定更為嚴格。(23)美國《1990年油污法》第1004款規定:“油輪的責任限額為每總噸1200美元。超過3000總噸的船舶,最低責任限額為1000萬美元;不足3000總噸的船舶,最低責任限額為200萬美元。”為了便于比較,可以把單位“美元”換算成單位“SDR”進行比較:依據美國《1990年油污法》,3000總噸船舶在生效之初的1989年的賠償限額約186萬SDR,而同樣是3000總噸的船舶,依據當時現行有效的1969CLC公約的賠償限額是40萬SDR,可見美國《1990年油污法》中規定的賠償限額遠高于1969CLC公約中規定的賠償限額。美國的這一國內立法引起了石油航運業的憤怒,石油航運業警告美國該部法律的出臺將會影響到對美國的石油進口供應。但事實上,OPA出臺之后,大多數石油航運業并沒有拒絕向美國繼續運輸石油,美國的石油進口數量也沒有減少。[22]美國能源部委托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OPA實施以來的顯著變化是在石油航運貿易中,“安全第一”成為首要準則,石油航運公司通過自有船舶或者通過與租用船舶的獨立船東建立緊密聯系以及對船舶進行徹底的安全檢查來控制風險,一些船舶所有人甚至在推銷船舶時,以“船舶經過徹底的安全操作系統改良”作為賣點。[23]自OPA實施以來,除極少數例外情況外,船舶溢油事故的數量和規模都呈下降趨勢。(24)See Briefing memo for Chicago QER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p.22.由此可見,OPA在降低美國水域船舶溢油事故和提高船舶所有人航運安全意識等方面所起到的法律規范作用無疑是顯著的。
第二,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將促使我國沿海運輸業的經濟結構和管理模式向更優的方向發展,這與我國所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所倡導的綠色發展理念相符合。一方面,我國沿海運輸市場中存在著很多小型、破舊的船舶,這些船舶不僅導致海上溢油事故頻發,同時以低價競爭的方式,在市場中擠壓那些具有先進技術、質量更優的船舶。鑒于CLC公約規定的賠償限額比我國國內法中規定的賠償限額更高,因此在非涉外船舶溢油事故中,適用CLC公約將導致船舶所有人面臨承擔更多賠償金額的風險,這在沿海運輸市場中無疑將成為新的競爭因素,從而加速老舊船舶的淘汰,促進企業購買安全性能和質量更佳的船舶,進而加速我國船舶制造業的研發和發展。[12]這一發展模式與我國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所推進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相契合。另一方面,CLC公約中所規定的較高賠償限額將在船舶運輸企業中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迫使船舶質量差、管理水平低、海上溢油事故頻發的小型船舶退出國內沿海運輸業務競爭,凈化國內沿海運輸市場,促進船舶運輸企業向高標準、高規范的發展方向看齊,促進船舶所有人、經營人以及船員對船舶安全進行更加嚴格的把控,從而保障航海安全,減少我國水域溢油事故的發生。這一管理模式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相吻合。因此CLC公約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適用所產生的導向——優化船舶運輸業的經濟結構,加速船舶制造業的發展以及更加嚴格的航運安全控制,不僅會促進我國沿海運輸業更好地發展,而且符合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要求。
五、結 論
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問題上存在著適用范圍、適用方式和適用后果三個層面的爭議。通過對公約適用范圍的辨析、國內法律條文的解讀和我國經濟發展理念的分析等方面做出的回應,認為CLC公約在我國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有其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一,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符合公約的適用范圍。CLC公約的誕生源于填補海上油污損害賠償制度的法律空白,我國在加入CLC公約時未做出任何保留,CLC公約第3條已明確其自身的適用范圍不受涉外因素的限制。
第二,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符合國內法的規定。“法際私法”的功能在于解決法律適用沖突,具有“法際私法”功能的《海商法》第208條、《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6條和《防治海洋環境條例》第50條等條款內容,均是應當適用CLC公約,為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提供了法律依據和解釋路徑。
第三,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有完善的保險制度保障。《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實施辦法》第8條和第9條、《海洋環境保護法》第66條和《防治海洋環境條例》第51條均規定了船舶所有人的油污強制保險義務,其中《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實施辦法》第5條規定的相應保險最低額度與CLC公約中規定的最低賠償限額一致,可以有效分散船舶所有人的賠償風險。
第四,CLC公約在非涉外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符合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要求。我國是航運大國,推動我國沿海運輸業發展的關鍵在于提升自身的競爭力,而非通過規避有著較高賠償限額的CLC公約來加以維護。通過CLC公約在非涉外油污損害賠償中的適用,將會為沿海運輸業增加新的競爭因素,促進國內沿海運輸業的經濟結構改革和船舶運輸企業的管理模式更新,符合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發展理念的時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