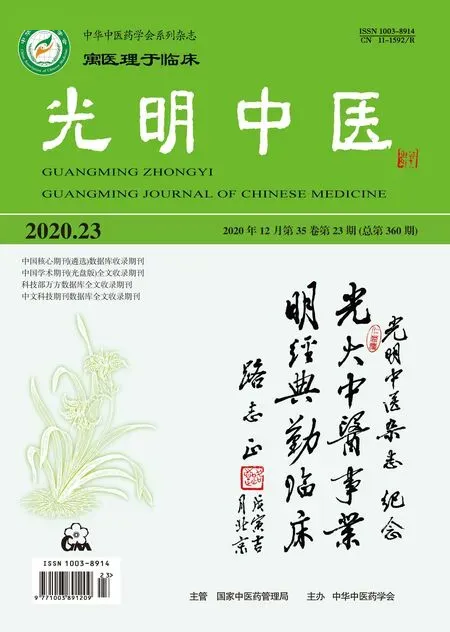彭建中教授治腎病之疏風勝濕法
耿賢華 彭 越 彭建中
吾師彭建中,主任醫師,教授,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醫學人文系原副主任,腎病會診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已故著名中醫學家任應秋先生的關門弟子,已故著名中醫學家、三代御醫之后趙紹琴教授的學術繼承人,趙紹琴名家研究室負責人,彭建中名醫傳承工作室指導老師。從事中醫臨床50多年,學驗俱豐,擅長以中醫藥治療慢性腎炎、腎病綜合征、慢性腎功能衰竭、尿毒癥等各種慢性腎病,療效顯著。彭教授繼承了趙教授的學術觀點,認為慢性腎病是由郁熱傷血或濕熱傷血所致,制定了以涼血化瘀為主,以疏風勝濕、疏調三焦、通腑排毒、分消水濕、益氣培元為輔,配合飲食調攝、運動鍛煉的綜合治療方法。疏風勝濕法是常用的治療方法,今將疏風勝濕法淺析如下。
1 疏風勝濕法的確立
彭教授認為慢性腎病為現代醫學腎臟系統的多種疾病[1],包括原發性腎臟疾病和繼發性腎臟疾病,前者如慢性腎炎、腎病綜合征等;后者如糖尿病腎病、高血壓腎病等。初起多表現為乏力、神疲、腰酸、夜尿增多、不同程度的水腫,至嚴重時出現嘔吐、大小便不通,后果十分嚴重。慢性腎病后期階段治療棘手,自古民間就有“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的諺語,其嚴重以及難治程度可見一斑。慢性腎病屬于中醫“水腫”“關格”等范疇,早在《黃帝內經》就有“陰陽俱盛,不得相榮,故曰關格”的相關記載,指出其為陰陽失衡不能互根互用的病理本質。《傷寒論》描述其為“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的臨床表現。歷代醫家通過司外揣內的認知方式,多認為屬于脾腎兩虛,濁邪壅塞三焦,濕毒為患,涉及肺脾腎等臟器。彭教授認為慢性腎病的病機為熱郁血分、絡脈瘀阻[2],或濕熱傷血、絡脈瘀阻[3],確立了以涼血化瘀為主的治療大法,也同樣十分重視濕濁之患的消除,且僅以涼血化瘀法難祛留滯血分之郁,必以疏散透達之品輔之以使郁通絡暢,故確立了以疏風勝濕法排除體內濕濁之邪,協助涼血化瘀法以建功。
《素問·經脈別論》曰:“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臟腑氣健代謝有序,外邪侵襲傷及臟腑,或起居失宜臟腑不健,致氣機紊亂,濕濁乃生。《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跗腫。”葉桂又說:“濕勝則陽微也。”蓋因濕為陰邪最易傷陽,尤傷脾腎之陽,具重濁黏膩、阻滯氣機、濕性趨下等特點,易入下焦,延及肝腎,則下焦不利,氣機失司,水液失常,濕濁乃生,故凡病及下焦,則濕濁乃釀,濕阻則陽郁,郁久化火傷絡以致絡脈瘀阻;濕濁又有黏膩不易清除之性,且易于寒化、熱化而成寒濕或濕熱之證,濕熱郁久而愈熱,濕熱耗陰傷血致絡脈瘀阻;寒濕聚于下焦,經脈澀滯,肝腎二臟氣血不暢,久則郁而生熱化火,亦傷腎絡而致絡脈瘀阻。故濕濁之邪與下焦絡脈瘀阻關系至為密切,祛除濕濁之邪是當務之急。濕濁之邪盤踞下焦,何以除之?通天徹地唯風可到!風能勝濕,又可開宣肺氣,升發肝氣,故祛下焦濕濁當以疏風勝濕法。疏風勝濕法是通過“疏”而啟動,《黃帝內經》曰:“疏其氣血,令其調達,而至和平”,通過疏風以暢氣機、祛濕濁、解郁滯,以使郁滯散解、氣血流暢,來治療濕濁阻塞、氣血郁滯之疾,正如王孟英所說:“人身氣血貴通而不貴塞”。由此觀之,疏風勝濕法既能祛濕又能透熱外出,在祛濕的同時疏通郁熱外出之路,這也是“透熱轉氣法”的一種體現。
2 疏風勝濕法的選藥
疏風勝濕法用于慢性腎病的治療,是基于慢性腎病濕濁的病機。彭教授認為慢性腎病的病機為郁熱或濕熱導致絡脈瘀阻,濕濁為之創造了條件并能使之加重,涼血化瘀通絡是治療絡脈瘀阻之主法,祛除下焦濕濁亦同等重要。濕濁之治有芳化、淡滲、燥濕等法,故立疏風勝濕、分消水濕、疏調三焦以治之,以此配合涼血化瘀法助絡脈瘀阻之消除。疏風勝濕法與涼血化瘀法結合應用,須時時不忘涼血化瘀之基,故選藥既要根據病情病機,更要兼顧涼血化瘀法,在涼血化瘀的基礎上宣氣機、升清陽、祛濕濁、散郁滯、暢氣血。選藥以輕清靈動、升發清陽為原則;以藥性平和、微溫為佳;藥量宜小,冀其緩緩透散。下面取幾種具疏風勝濕功效的藥物分析之。
荊芥味辛,性微溫,入肺、肝經,有輕浮疏散之功,能勝濕止痛,且能解痙以緩絡脈拘急;升肝中清陽,一助化濕,一利降濁;宣在表之風,散聚于肌膚之濕濁毒結以止癢疹;有消瘡之效,對濕熱化火、火刑絡腐之腎病尤宜;炒炭有止血之能,對腎病出血尤宜,《本草綱目》云其可治吐血、衄血、下血、血痢等。《本草經疏》云:“下瘀血入血分,辛以散之,溫以行之之功也。”
防風味辛、甘,性微溫,入膀胱、肝、脾經。具祛風解表、勝濕止痙之功。其性緩和,溫而不燥,發而不峻,為風中之潤劑,治風通用之圣品,善行全身。《本草匯言》云:“防風辛溫輕散,潤澤不燥,能發邪從毛竅出,故外科癰瘡腫毒,瘡痿風癩諸癥亦必須也”[4]。慢性腎病熱傷血絡,腎絡瘡腐,與荊芥相須用之,可輔升清陽、散濕濁、暢氣血,以助涼血化瘀之劑清血分郁熱,開腎絡之郁滯。
白芷味辛,性溫,入肺、胃、大腸經。可祛風解表、燥濕排膿、消腫止痛,入氣分、亦入血分,其性升散,《本草經疏》云:“辛香散結而入血止痛,故長肌膚。”可知其生肌之效。本有祛風勝濕之功,又可長肌生絡,與腎病絡脈瘀阻病機相合,能促進腎絡之修復,用之適宜。《本草求真》曰:“能溫散解托,而使腠理之風悉去,留結之癰腫潛消,誠祛風上達,散濕火要劑也。”其消癰散濕火之功正合慢性腎病之質,既能去下焦濕濁又可消腎絡之癰,以助瘀化絡通。
獨活味辛、苦,性溫,入肝、腎、膀胱經,祛風濕,解表,止痛。性較緩和,發散力弱,善治人體下半部之疾,對于慢性腎病可溫散下焦寒濕,疏通血氣,使脈絡和暢。《本草正義》云:“氣味雄烈,芳香四溢,故能宣通百脈,調和經絡,通筋骨而利機關,凡寒濕邪之痹于肌肉,著于關節者,非利用此氣雄味烈之味,不能直達于經脈骨節之間”。濕濁之邪伏于下焦,宣疏之常藥難以及之,需得此氣味具厚之品引之,旨在引龍出海,透邪外出,以此用之與涼血化瘀類相伍,又有相反相成之妙。
紫蘇葉味辛,性溫,入肺、脾之經,發表散寒,理氣和營。入肺宣發肺氣,開水之上源,暢通三焦,水濕下行,以利水道,有“提壺揭蓋”之功;又能行氣理脾,章虛谷說:“三焦升降之氣,由脾鼓動,中焦和則上下順”,紫蘇葉即可宣肺又能理中焦脾胃氣機,中焦健運則水濕自化,對腎病之濕濁阻滯甚是相合。
疏風勝濕類藥物還有很多,如羌活、柴胡、升麻、葛根、白蒺藜、蔓荊子等,均有疏風勝濕之功,又各有所長,臨證時需據病情之不同,依法組方,選而用之。
3 疏風勝濕法的運用
彭教授認為慢性腎病的病機是郁熱或濕熱導致的絡脈瘀阻,郁熱或濕熱是致病元兇,濕濁與之合污,濕濁不去,元兇難除。疏風勝濕類藥物具祛濕濁、透邪外出之功,能同克兩方面因素,故疏風勝濕類藥物是用于慢性腎病全程治療中。應據病情合理選用,嚴格注意用量,疏風勝濕類藥物性多辛散,量大或藥味過多有助熱之弊,尤其尿中有紅細胞甚或血尿者更要謹慎,應味少、量小以緩緩透熱外出,不可過用以防增熱動血。
水腫是慢性腎病主要癥狀之一,輕者多見顏面虛浮或兩下肢水腫,重者則表現為全身水腫,甚或胸水、腹水,其中以腎病綜合癥腫勢最甚。郁熱或濕熱之邪,傷及血分致腎絡瘀阻,故腰痛酸;氣化無力,水液排出受阻,小便不暢,濕濁聚集,水濕泛濫,水腫乃作;水濕不行,肺脾腎受損,氣機不暢,則乏力困倦;濕濁內阻,肝胃升降失和可見惡心、嘔吐、腹瀉或便秘;濕濁上蒸則苔黃厚膩;濕邪上犯心肺可出現胸水、心包積液等;濕濁積聚日久化毒則血尿酸、肌酐、尿素氮等升高;濕濁壅滯三焦,三焦氣化失司,元氣損傷,腎氣愈加難復,如此進入惡性循環。腎絡之瘀阻不通,濕濁愈甚,濕濁不去,瘀阻之絡脈難暢,三焦氣化不行,二邪膠結,須多法并行而解之。
乏力、神疲也是慢性腎病的常見癥狀,其主要原因是由濕濁阻滯氣機或熱郁致經絡不通、氣血不暢,氣血不能營通肢節則乏力,氣血不能上榮于腦則神疲,亦有氣虛所致,結合脈證可辨。亦有濕濁、火郁致邪毒壅盛,阻礙氣血生化而致嚴重貧血乏力者,須結合其他大法治之。臨證常見面色淡黃或萎黃虛浮,舌體胖大多有齒痕,亦濕濁所致,濕郁有熱則舌紅且胖,火郁者舌邊尖紅,苔多垢厚,脈多按沉方得。
以上諸癥皆以濕濁為重,必須在針對絡脈瘀阻的病機上重祛濕邪。風能勝濕,風藥輕清,上宣肺氣,外開腠理,通調水道,以達祛濕之效;風性宣散,透達毛竅,疏通郁熱之出路,散熱外出;風能入絡解痙,緩解筋脈、血絡之拘急,使絡脈通暢;一舉多效,皆中慢性腎病之病機,結合涼血化瘀法及其他祛濕之法,可有效解決絡瘀濕濁膠著之勢,有利于慢性腎病恢復。
4 驗案舉例
楊某某,女,38歲,慢性腎炎。一診:2019年3月7日,面浮、兩小腿水腫10 d,伴腰酸、神疲乏力。2年前有“腎炎”病史,因元宵節外出受涼隨咽痛發熱咳嗽,經輸液5 d方愈。10 d前又發現面浮緊腿腫,又有腰酸,感覺沒精神沒力氣,懷疑腎炎復發,隨即來診。刻見:面浮白,目腫無神,腎區叩痛,脛前、腳面腫甚,按之凹陷久久不能恢復,左側略重,體溫:36.8 ℃,血壓150/90 mmHg,尿常規:BLD++,PRO++,舌淡紅略胖邊尖瘀點,苔白厚,脈弱重按有力。診斷:水腫。西醫診斷:慢性腎炎。證屬濕熱傷血,絡脈瘀阻。治法:涼血化瘀,疏風勝濕。處方:荊芥炭10 g,荊芥6 g,白芷6 g,獨活6 g,防風6 g,生地榆10 g,赤芍10 g,丹參10 g,炒槐花10 g,藿香6 g,佩蘭6,金銀花10 g,連翹10 g,大黃6 g,紫花地丁10 g,竹葉6 g,水紅花子9 g,茯苓皮30 g,冬瓜皮30 g,車前子10 g,雞內金 10 g,焦三仙各10 g。水煎溫服,每日1劑,7劑。囑:低鹽飲食,忌食辛辣、寒涼、高蛋白食物,注意休息。
2019年3月14日二診:自覺已有力氣,精神可,腰部稍累,望之面浮顯減,目已不腫,兩腳踝略腫,按之輕度凹陷。舌淡紅略胖邊尖瘀點,苔白略厚,脈弱。前進涼血化瘀、疏風盛濕、分消水濕之劑,濕祛熱減,絡脈已暢,故精力恢復、面浮肢腫漸消,效不更方,繼進原方14劑。
2019年3月28日三診:面浮肢腫消退,自覺身體輕快,尿常規無異常,舌淡紅略胖邊尖瘀點,苔薄白,脈較前有力。處方:荊芥6 g,白芷6 g,獨活6 g,防風 6 g,生地榆10 g,赤芍10 g,丹參10 g,炒槐花10 g,金銀花10 g,連翹10 g,大黃6 g,紫花地丁10 g,枳殼 10 g,大腹皮子各10 g,水紅花子9 g,冬瓜皮30 g,車前子10 g,土茯苓30 g,雞內金10 g,焦三仙各10 g。
按:本例患者2年前有腎炎病史,仲春時節又因外感誘發,屬伏邪為患,柳寶詒說:“邪伏少陰,隨氣而動,流行于諸經,或乘經氣虛而發,或挾新感而發。”邪伏少陰,遇外感而動。經云:“腎者水藏,主津液”“腎者胃之關也……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5]。外邪動內患,濕熱傷腎,氣化不足,水液代謝障礙,水腫乃作;濕熱漫延,三焦不暢,阻滯氣機,則困倦乏力;濕熱動血,腎絡損傷,紅細胞、白蛋白漏出,尿中可見;腰為腎府,腎絡瘀阻,不通則痛;水濕泛濫,脈伏其下,故弱但重按有力。其治以涼血化瘀,疏風勝濕之品,先予7劑,顯效之后又連投14劑,癥消邪退,調整方藥,續清余邪。
5 小結
慢性腎病是由熱郁血分或濕熱傷血導致絡脈瘀阻所致,故消除絡脈瘀阻是治療本病的根本,熱郁和濕熱是關鍵致病因素,而濕濁又是與之膠結的另一致病因素。風藥能勝濕,疏散之性能透邪外出、能入絡解痙,配合涼血化瘀藥物使用,對體內濕濁、濕熱、郁熱能有效清除,并能疏暢氣血,調和經絡臟腑,對慢性腎病的恢復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疏風勝濕法在慢性腎病中的應用,是“開鬼門,潔靜府”“透熱轉氣”“引經入絡”等原則的充分體現與發展。在臨證中結合涼血化瘀、疏調三焦等其他治法,治療慢性腎病能收到令人滿意的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