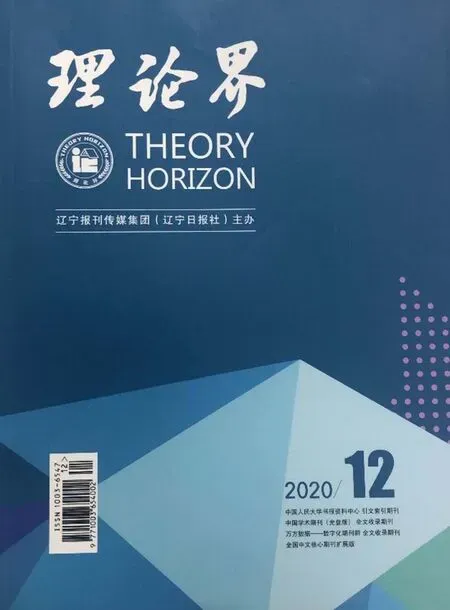主流話語與朱權的戲曲批評的史家立場
劉梅蘭
明初,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發生巨大變遷,政治話語強勢介入文學場,功利主義思想成為“文學思想的主要潮流”,“文學從原來的自適閑適轉向實用教化”,〔1〕文學的倫理教化功用被普遍強化。如宋濂論詩主張學習古人,以期成為“世法”而有“補于政治”,〔2〕即所謂“先王道德之澤,禮樂之教,漸于心志而見于四體,發于言語而形于文章,不自知其臻于盛美耳”,〔3〕極力強化傳統詩學表現先王道德之澤及其禮樂教化功能。
文壇主流話語也直接引導了包括劇作、曲論在內的戲曲生產與消費。朱權作為皇子頗受乃父朱元璋看重,而他作為帶甲擁兵、驍勇善戰的藩王,又曾被明成祖朱棣脅迫利誘靖難起兵,朱棣登基后自以為有功而實則處境難堪、頗受打壓。朱權所著的《太和正音譜》初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改定于永樂六年(1408)以后,正是在政治規引下文壇重視倫理教化主流話語在戲曲場的直接反響,而自覺不自覺回應和維持著朝廷“制樂以節樂”主流話語導向。但朱權并沒有因此喪失自主性而淪為政治附庸,他站在戲曲史家的批評立場,對戲曲本質屬性作了專注探索,特別是音律論與北曲譜、戲曲風格論、雜劇題材論等,這與其中保存的戲曲史料等內容,均體現了朱權戲曲批評的自我意識,微妙反映了他前后不同的社會處境及戲曲批評心態。
一、主流話語與朱權戲曲批評的禮樂內涵
朱權(1378—1448),字臞仙,號大明奇士、涵虛子、丹邱教授,明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受封大寧(熱河市東部,今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擁兵塞外,“帶甲八萬,革車千乘,所屬朵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4〕朱棣起兵靖難時,曾計謀脅迫朱權出兵,許以事成后“中分天下”。建文四年(1402)朱棣登基為帝,朱權請封蘇州、杭州,均未如愿。永樂元年(1603),朱權被改封江西南昌,又遭遇“人告”“巫蠱誹謗事”,后雖經朝廷核查無實據,但朱權自此對世事頗為失望,開始遠離朝政,韜光養晦,著書釋道,寄情戲曲,晚年隱逸學道。卒謚獻,后世又稱寧獻王。
朱權學識淵博,多才多藝,著述頗豐,主要有《通鑒博論》《漢唐秘史》《文譜》《詩譜》《茶譜》《神奇秘譜》等,其中雜劇作品和戲曲理論著述最為人稱道。朱權共作雜劇十二種,今僅存《沖漠子獨步大羅天》《文君私奔相如》二種,殊為可惜。《瑤天笙鶴》《淮南王白日飛升》《周武帝辨三教》《齊桓公九合諸侯》《肅清瀚海平胡傳》《北豐大王勘妒婦》《楊娭復落娼》《豫章三害》《煙花鬼判》《客窗夜話》只存名目未見傳本。曲學論著三種:《太和正音譜》《務頭集韻》《瓊林雅韻》,今只存《太和正音譜》。《太和正音譜》又名《北雅》,題“丹邱教授涵虛子撰”,正是這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戲曲專著,奠定了朱權在戲曲批評史上的地位。
朱權對其父明太祖營構的文化政策領悟精深,其戲曲批評自覺不自覺地回應和維持著明朝廷“制樂以節樂”的主流話語導向,高度認同戲曲的禮樂內涵和感化人心教化作用,藉此鼓吹“洪武盛世”的“禮樂之盛,聲教之美”。如《太和正音譜·自序》云:
猗歟盛哉,天下之治也久矣。禮樂之盛,聲教之美。薄海內外,莫不成被仁風于帝澤也,于今三十有余載矣。近而侯甸郡邑,遠而山林荒服,老幼聵盲,謳歌鼓舞,皆樂我皇明之治。夫禮樂雖出于人心,非人心之和,無以顯禮樂之和;禮樂之和,自非太平之盛,無以致人心之和也。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是以諸賢形諸樂府,流行于世,膾炙人口,鏗金戛玉,鏘然播乎四裔,使鴃舌雕題之氓,垂發左祍之俗,聞者靡不忻悅。雖言有所異,其心則同,聲音之感于人心大矣。〔5〕
這里“樂府”指散曲和雜劇。序言以儒家禮樂為立足點,闡釋《太和正音譜》取名旨意源自儒家《禮記·樂記》,試圖把雜劇納入樂府范疇,以其呈現“禮樂之盛,聲教之美”。朱權立足禮樂論曲與文壇主流話語保持了高度一致,卻也未曾喪失自我立場。畢竟朱權是發自內心地禮贊乃父治下的禮樂盛世,代表了明王朝復歸華夏正統歷史大環境下世人的自信和豪邁心態。
朱權論曲禮樂內涵,學界所論各有側重,現摘其要者如下:
第一種觀點重在探討朱權論曲的禮樂意識和禮樂精神之體現。如李舜華《禮樂與明前中期演劇》以禮樂視閾解讀朱權的戲曲理論,將朱權及其曲論置于明前期禮樂制作的社會大環境中,從禮樂到演劇,從樂學到曲學,樂論與曲論互相發明,探討朱權論曲體現的禮樂精神及其內涵。指出朱權曲學高揚聲教之美、禮樂之和,集中發展了元代以來“曲與禮樂之盛、聲教之美的聯系”,是“以戲曲歌詠太平的禮樂意識”的體現;朱權關于“樂在章不在聲的議論”,雜劇乃太平盛世之產物,亦是“明初禮樂制作的內在精神”的體現;〔6〕這種思維方式,由元代的“周德清、虞集、鄧子晉等人在理論上發起,經明初樂制改革付之于實踐”,再經過朱權的理論總結而“已深入人心”,由此影響了永樂、宣德年間以朱有燉為代表的宮廷北雜劇的“日益繁熾”,及其之后的演劇發展;朱有燉等人的雜劇創作,也是“朱權曲學的直接體現,絕不僅僅是韜晦之作”,〔6〕深刻闡釋了此一時期曲論發生的文化內涵與社會動因。
第二種觀點重在闡釋《太和正音譜》作為工具書,為戲曲作者提供了作曲范式。如姚品文《朱權研究》指出,朱權撰寫《太和正音譜》的宗旨和性質在自序中表述已經非常清楚,其“基本目的”并非頌揚“皇明之治”,亦非闡釋樂府產生與太平盛世之間的直接關系,朱權選取“元之老儒”和“當代群英”所作樂府“依聲定律”“按名分譜”,目的是為作北曲的“好事者”和“學者”提供一個“楷式”,“作者的初衷,是為了提供一部工具書”。〔7〕
第三種觀點認為朱權以禮樂論曲,旨在提高戲曲的社會地位。出版于2010年的姚品文的《太和正音譜箋評》對朱權戲曲理論的禮樂內涵有了新的解讀,指出這是朱權為了“改變人們觀念中對樂府性質的認識”,提高人們“對樂府社會意義的評價”,把“‘樂府’和‘禮樂’重新聯系起來”,“為了張揚樂府文學而拉起了‘禮樂’的神圣旗幟”。因此,朱權在自序中討論禮樂的言論“確有美化之嫌”,他宣揚太平盛世“也未免粉飾”,但他的動機以及由此達成的效果,卻“無非為‘拔高’樂府,為《太和正音譜》之編撰尋求支持”,因此,“我們不得不對這位貴族文人反傳統的良苦用心和勇氣刮目相看”。〔5〕她2013 年新出的著述《王者與學者——寧王朱權的一生》指出,朱權“在序言中將新樂府與禮樂等同”論說,“多少有些牽強,但從原理上來說也未為悖謬”,指出這是朱權為“提高‘樂府’社會地位”所作的努力。〔8〕徐子方也認為《太和正音譜》作者憑借藩王之尊,將“不登大雅之堂的戲曲與傳統上官方音樂機構樂府畫上等號”,自居曲學“行家”,在將“雜劇由民間提升到了精英文化的檔次方面顯示了前所未有的力度”。〔9〕
第四種觀點側重于朱權的教化觀及其作為皇族文人階級傾向的表現。如黃仕忠《朱權的人生道路和戲劇理論》指出,朱權認為“蓋雜劇者,太平之勝事,非太平則無以出”,《太和正音譜·序》中說道:“禮樂之和,自非太平之盛,無以致人心之和”,“強調戲劇藝術粉飾現實的功用”,表現出的是“皇族文人鮮明的階級傾向”。〔10〕俞為民亦持相似觀點,他認為朱權作為皇族戲曲家,視戲曲為太平盛世之產物,“明顯地帶有明初教化派曲論家的痕跡”,具有“狹隘的功利主義色彩”。俞為民對朱權的戲曲理論既批評也肯定,他認為朱權把“封建正統文人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戲曲藝術提高到了與詩文一樣,具有粉飾太平、和悅民心的功能,這對于以詩文為正統的文學觀念是一種革新”。〔11〕也有學者對此持不同觀點,如朱萬曙認為朱權以“盛世心和”戲曲觀取代教化觀,體現了一種“戲曲觀念的鼎新”。〔12〕而萬偉成指出,朱權立足傳統禮樂“治理朝政,端正社會風氣”的理論基礎,“強調音樂與人心的雙向效應”,目的在于“提高雜劇的地位,使它為明代文化建設乃至‘皇明之治’服務”,《太和正音譜》提出以“太平”為宗旨的“教化說”,其中的“中和樂章,內容多是歌舞升平,粉飾太平,屬于典型的雅樂歌辭,說明他把當時視為俗樂的北曲運用到禮典上來,實踐了他的理論主張”,〔13〕多少有點調和的意味,卻不無道理。
筆者以為,《太和正音譜》作為中國古典戲曲理論誕生的重要標志,“采摭群英詞章,依聲定律,按名分譜”,〔5〕為北曲雜劇立下了規范,在中國古典戲曲理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者確有將之作為工具書,提高戲曲地位等用心。但以戲曲呈現“禮樂之盛,聲教之美”卻是朱權編纂該書不可忽視的重要目的所在。從整個社會大環境看,明代漢族大一統政權的重新建立,明前期初步形成的勵精圖治社會政治格局等,社會各階層普遍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群體自信,乃至自負心理。文學場不能不受此影響,歌詠大明王朝開國之初的太平祥和盛世氣象,自然成了明前期文學的普遍審美趨向。由元入明的楊維楨、高啟、宋濂、劉基等人,以及明前期的臺閣文人楊士奇、楊榮、楊溥等都對明代前期的盛世歡欣鼓舞,倍感自豪、自信,寫詩歌頌皇恩浩蕩、圣主英明,歡呼國朝升平昌盛、河清海晏。明前期戲曲與政治緊密相連,戲曲作為政治的運作媒介,帝王與皇室貴族,包括文人士大夫等精英階層在戲曲場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明初對戲曲價值的高度重視必然導致對戲曲獨立性的強調,由此深化了對戲曲屬性的認識,從而極有可能刺激戲曲批評、理論總結的出現,一定程度上規范和導引著戲曲生產和消費,對戲曲自主性規則理解的深化,相應地提高了戲曲的社會地位。朱權所著的《太和正音譜》論曲的禮樂內涵,自覺或不自覺地回應了當時文學場的主流思潮,是主流話語在戲曲場的呈現。《太和正音譜·自序》對戲曲禮樂內涵的闡釋,呈現了戲曲的社會性需求及帝王統治的價值,而明前期帝王對戲曲價值的重視又刺激放大了這種需求。
從文化場與政治場的互動復雜關系看,某一王朝重建思想體系時,文化場自主性規則就被削弱,通過文化宣傳、說服、爭取的任務就加重,也就更強調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效用,文學、藝術等組成的文化場的小場域生產就越發冷寂蕭條。隨著政權的逐步鞏固,社會越穩定,文化生產就越豐富,文化場的自主性規則就可能逐步得到強化。以此考察《太和正音譜》,正好可以印證朱權在“群英所編雜劇”中對雜劇生產社會環境的解釋,其言曰:
“蓋雜劇者,太平之勝事,非太平則無以出。”〔5〕
朱權認為,明朝建立了大一統的帝國統治,社會承平、氛圍祥和,為戲曲表現太平提供了最好的材料和題材,因而歌頌、表現盛世當為戲曲首要任務。這說明朱權對戲曲社會功效的重視和認同,既取決于明王朝的政治策略及其在戲曲場的話語霸權及其皇族身份,也取決于彼時戲曲的發展態勢。《太和正音譜》將戲曲的娛樂性與太平盛世相聯系,把戲曲的生產消費與粉飾太平直接結合,主張雜劇美化盛世,點綴升平,并通過品評雜劇作家作品,將此理念融入雜劇體制、分類、流派、音律、創作、演唱等諸方面,以凸顯戲曲的教化功能,反映了朱權作為皇室成員、藩王貴族的身份認同和階層意識,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傳統詩教觀念的革新,客觀上起到了提高雜劇社會地位的作用。
朱權對雜劇十二科的分類,也可視為對明王朝戲曲策略的一種回應和維護。十二科中“披袍秉笏”(君臣雜劇)“忠臣烈士”“孝義廉節”“叱奸罵讒”“逐臣孤子”等宣揚忠臣孝子、忠義廉節等綱常教化者五類,再加上“鈸刀趕棒”表現英雄俠義,隱逸樂道、安做順民的“神仙道化”“隱居樂道”兩類,教化題材占比最重,與明王朝詔令提倡和褒獎的“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等聲教題材高度一致,完全符合明王朝戲曲高臺教化要求。
二、主流話語與朱權戲曲批評的史家立場
文學場從未真正擺脫權力場的影響,文學場從來都與政治、經濟、倫理等場保持著密切聯系。明前期政治話語霸權強勢介入戲曲場,對戲曲生產與消費態勢影響可謂深遠,但朱權的戲曲批評并沒有完全喪失自主性,淪為政治場的附庸。朱權以戲曲史家的批評立場,對戲曲本質屬性作了專注探索,特別是音律論與北曲譜、戲曲風格論、雜劇題材論等內容,其中保存的戲曲史料更體現了朱權戲曲批評的自主性和自我意識。我們可以將之視為朱權以著述呈現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既然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那么從事詩詞曲賦等文學創作、批評,直接參與戲曲生產與消費,既能避禍,修養身心,又能在閑情逸致、雅趣享樂中施展才華,確認自我生命的存在價值,不至于在失去政治抱負和理想的時候,再失去自我存在價值。當然,這些現象的背后,無疑又潛藏了朱權作為皇室貴族的優越感和自信心。
《太和正音譜》對三家之唱、雜劇十二科、十五體與二百零三格勢等曲品式批評,微妙反映了朱權在洪武朝和永樂朝的不同境遇、心態和處世方式。明太祖《三教論》闡釋了三教為政權服務的重要性,朱權亦比較看重三教之于戲曲的功用。《太和正音譜·詞林須知》將元曲中三教所唱內容作了分類,并結合“雜劇十二科”“十五體”品第其高下:
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隱居樂道、三曰披袍秉芬、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義廉節、六曰叱奸罵讒、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鈸刀趕棒、九曰風花雪月、十曰悲歡離合、十一曰煙花粉黛、十二曰神頭鬼面。〔5〕
朱權將神仙道化、隱居樂道位列第一、第二,論者大都認為這與他個人的人生經歷和中年之后崇道密切相關,如黃仕忠《朱權的人生道路和戲劇理論》、萬偉成《朱權的戲劇學體系及其評價》等所論,顯然與朱權自署“洪武三十一年”(1398)所作《太和正音譜》序相矛盾。關于《太和正音譜》的成書時間,學界依據影抄《太和正音譜》洪武刻本, 確定完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但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有學者對《太和正音譜》成書時間提出質疑。如洛地認為《太和正音譜》 應作于“永樂年間(1403—) 或永樂七年(1409) 前后或以后”,〔14〕周維培認為《太和正音譜》是永樂元年(1403)朱權改封南昌后的手筆,絕無產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以前的可能,應在永樂六年(1408)以后,并指出《太和正音譜》有兩種:朱權封藩大寧時的初刻本,改封南昌后的增補本,初刻本成書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主要內容是北曲調名總目和北曲格律簡譜,永樂六年(1408)以后補入曲論、曲目等有關內容,是為增補本。〔15〕夏寫時也認為《太和正音譜》有洪武本與成于永樂末年的增訂本之分,并且產生深遠影響者為增訂本。〔16〕黃仕忠則指出所謂《太和正音譜》“洪武刻本根本不可能存在”,該書的“曲譜部分可信編定于洪武三十一年”,而卷首的“曲論部分的撰成,應是在朱權的晚年”,并列舉四條材料闡釋朱權思想和曲論觀點有早期與晚年的差別,證明《太和正音譜》曲論部分成于晚年,闡明朱權之所以特別推舉馬致遠等人的神仙道化劇,應該與他本人的人生經歷緊密相關。〔10〕姚品文也通過考訂認為《太和正音譜》成書時間大約在永樂前期。學界對《太和正音譜》不可能成書于洪武三十一年的考證,為研究朱權的曲學思想及其演變提供了有力佐證。
筆者以為,在朱權人生歷程的不同階段,對儒釋道三教的崇奉程度各不相同,但儒家始終是其主導思想,禮樂教化當是《太和正音譜》編纂主旨所在。《太和正音譜》對北雜劇曲譜對音韻格律的論述和規范等,也顯示了朱權對北曲“正音”與“雅韻”地位的認同,視禮樂為太平治世的結果,自覺維續和聲援明代前期統治者構建的戲曲場規則,強調“聲教”感化人心的重要性。《太和正音譜》之所以把神仙道化和隱居樂道放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也是本著實事求是的歷史態度,作者站在戲曲批評史家的立場而非思想家視閾關照全書。具體而言,當與《太和正音譜》主要批評品第元代和明前期雜劇作品有關,也與明前期文士所處社會地位和隱逸心態有關,當然也不能排除朱權個人的趣尚。理由如下:
一者,元代文人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他們或反復求取功名而不得,或僥幸取得功名但歷經官場挫折,只能退而以旁觀者的心態立身處世,失缺了政治參與熱情,生活態度閑散,一再放任個性去飲酒聽曲、唱和賦詩,是一種面對社會現狀無奈之下的隱逸樂道。〔1〕“心之所感,情之所發”,“有感于中而行于言”(周砥《荊南唱和詩序》),元代文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他們的存在方式、生命狀況和心理狀態,必然會滲透并通過他們的戲曲活動表現出來。二者,元末明初的社會場造就了道家修仙飛升,儒家隱居樂道類雜劇產生的溫床,所謂“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曲家對現實的失望,以及抑郁不得志而紛紛隱逸,創作了大量神仙道化劇。元末雜劇重心南移,因而江南文人對世事的冷漠絕望與對隱逸樂道的熱衷在戲曲中的表現尤其明顯。三者,元明易代,文士由元入明,朱元璋采用科舉、征召等多種方式設法使文士為己所用,文士地位和生存狀況明顯改善。明王朝復建漢族大一統政權,也確實讓他們歡欣鼓舞,但明太祖任用文士的輕率隨意態度,又使文士常常被莫名責罰,抱負才華難以施展,社會地位得不到保障,甚至性命不保。元末明初文士已然形成的隱逸“慣習”也不會立刻改變,他們依然留存了回避政治的“慣習”,表現在戲曲創作上,就是神仙道化和隱逸樂道劇批量生產。四者,朱權論曲主張“和”,表現“人心之和”的神仙道化、隱逸劇自然受其青睞,與他推崇“治世之音安以樂”的戲曲思想保持了高度一致。
朱權借鑒詩學批評方法,把“體”“格勢”引入曲學批評,在上卷簡要闡釋新定樂府體一十五家的風格,并將“丹丘體”置于各體之首。在朱權的很多自號中,“丹丘”排在最前,且將之闡釋為“豪放不羈”。我們至少可以從中管窺到三點:首先,朱權對道教題材的推崇,實質基于對“中和之美”的欣賞。其次,表現了朱權皇室成員、藩王意識下的安樂平和心態。朱權所謂“豪放不羈”,并非指雄闊豪邁之氣魄,亦非放誕不羈及俠氣,而是姚品文所言的“一種極度的曠達和通脫的心態”,“不羈”也“不是語言的全無忌憚,而是精神的真正解脫”,〔17〕這種曠達通脫反映在戲曲批評上,便是對“禮樂之和”之作的推崇。再次,“豪放不羈”,也是劇作風格、氣象、情感表達的體現。
洪武朝和永樂朝都頒布了搬演雜劇戲文禁限詔令,不許樂人“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賢神像”律令,朱權將這些禁演的雜劇題材列入“十二科”中,說明朱權主要依據雜劇作品現狀對其進行分類,同時也表明《太和正音譜》改定之時朝廷的戲曲禁限政策有所松動。我們藉此可推論《太和正音譜》有洪武本和永樂增訂本之分,曲譜部分編撰于洪武三十一年,曲論部分應編訂于永樂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