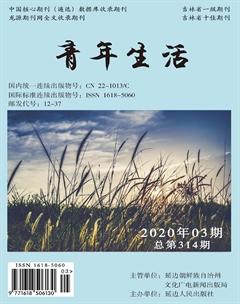試論元代延祐儒治的意義
白云敏
摘要: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在其統治的延佑年間(1314年—1320年)實行恢復科舉考試、編撰法典、翻譯和出版書籍等一系列使蒙古政權儒化的措施。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
關鍵詞:延祐 儒治 元仁宗
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從十幾歲開始學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輸的儒家倫理和政治觀念對他后來的政治態度有很大的影響。仁宗在懷州任宗王及后來身為海山的皇太子時期先后在身邊任用了許多漢儒,如趙孟頫、張養浩、姚燧等;因此,仁宗不僅能夠讀、寫漢文和鑒賞中國繪畫和書法,還非常熟悉儒家學說和中國歷史。仁宗對儒學及其政治價值是有深刻認識的。和所有蒙古貴族一樣,他也迷信佛教和薩滿教。他“通達儒術,秒悟釋典。”常曰:“明見心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常與群臣語,我勸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他十分關懷國學,屢次下詔勉勵學校。他指示省臣說:“國子學,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訂國子生額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定式。”在儒家政治學說的強烈影響下,仁宗即位之初就將海山時期的大部分政策廢止。在大批儒士的引導和支持下,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后便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推動了元朝進一步漢化和儒化改革。
一、恢復科舉考試
科舉考試是中原王朝甄選統治精英的主要途徑,關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斷圍繞恢復考試問題展開爭論,但是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以后,形勢發生了變化。改善官員水平的迫切需求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化的迫切要求,使得恢復科舉考試的呼聲再次高漲起來。皇慶二年(1313年)頒詔恢復科舉考試。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令天下郡縣舉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試于廷,賜及第出身有差。他表示:“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至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從至元以來屢議屢格得科舉制度正式開始舉行。考試科目重經學而輕文學,指定朱熹集注的《四書》為所有參試者的標準用書,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釋的《五經》為漢人參試者增試科目的標準用書。這一變化有助于確定理學的國家正統學說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歷史意義,并被后來的明、清兩代基本沿襲下來。
延祐開科意義重大,以程朱理學文科考內容是歷代所無,一改前代詩詞文賦為科考內容的歷史,科舉內容的重大變化,必然影響著文風的走向。形成了重根底,不尚空言的文風,文風據理,考據精確,矯正了南宋末年科舉文風的流弊。這與仁宗皇帝頒布的科舉詔書有極大的關系,仁宗科舉詔中說:“浮華過實,朕所不取。”雖然科舉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元代儒士入仕的問題,取仕的規模也遠遠不能與唐宋明清相比,但延祐科舉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推動了元朝文風的大變革,此時文治達到元代的高潮。所以延祐科舉自然成為元代前后期文風的分界線。鄧紹基主編的《元代文學史》把延祐作為元代詩文發展的分界線,并認為延祐科舉以后的成就超過了此前,并提出了依據:“元詩發展以仁宗延祐年間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延祐以前宗唐得古詩風興起到旺盛,延祐以后宗唐得古潮流繼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后期成就超過前期。”
二、編撰法典
編撰法典是仁宗改革元代制度而且產生預期效果得另外一個領域。可能是因為在多元文化社會確定統一的法典有難以克服的困難,也可能是因為蒙古統治者認為統一的法典會限制他們的權力所以才采取了反對的態度,元朝從未制定一個通行全國的標準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漢人官員的極大焦慮。
愛育黎拔力八達很快采取措施對這樣的形勢加以補救。在1311年即位當月,他命令中書省臣匯集從忽必烈朝初年以來的律令條規。這一匯編工作于1316年完成。但是對匯編的復審過程要比預期的時間長的多。直到碩德八剌即位后兩年的1323年,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頒行。這個新法典收錄了建國以來的法律條文2400條,分為斷例、條格、詔制、別類四大類。
《大元通制》雖然不是一部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現代法制史學者的觀點,此書“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標志,因為他有充實的內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的法典結構。”《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他的編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但是,作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沒有照搬中國以前的法典。它在許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習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大元通制》和也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編輯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兩個里程碑,也是作為征服王朝元朝日益成熟的反映。
三、書籍翻譯和出版
愛育黎拔力八達對漢文化的喜愛,他和他的臣僚(特別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對儒家政治學說和漢人歷史經驗的渴求,可以從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翻譯或者出版的著作的數量和性質上反映出來。翻譯成蒙古文的漢人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尚書》;宋人真德秀撰寫德《大學衍義》;與唐太宗有關的兩部書吳兢撰寫的《貞觀政要》和太宗本人為他繼承者撰寫的《帝范》;司馬光撰寫的偉大史書《資治通鑒》。在愛育黎拔力八達贊助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孝經》,劉向撰寫的《烈女傳》,唐代陸淳研究《春秋》的論著以及元代官修農書《農桑輯要》。
雖然以上所列都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同意下出版的漢人著作,反映的是他作為天子有倡導大眾道德和增加物質福利的責任,翻譯著作的選擇,則顯示了他的實用主義的目標。在下令翻譯《貞觀政要》時,他指出此書有益于國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能誦習該書的譯本。蒙古君主顯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夠學習儒家的政治學說和漢人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唐太宗的教誡,能把國家管理的更好。
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在其統治得九年時間里重用儒士,實施多項漢化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蒙古統治者與漢族官僚士大夫之間得矛盾,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對提升蒙古人與色目人得文化素養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促進了各民族之間文化得交流與民族融合。仁宗得各項政策對他得繼任者碩德八剌產生了重大影響,碩德八剌繼續貫徹仁宗得各項漢化政策。愛育黎拔力八達朝以極大期盼和果斷行動開端,被一些史學家稱為“延祐儒治”。它雖然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實際上沒有成功的遏制蒙古和色目精英得既得利益,因此沒能從根本上改造蒙元政權得“整體結構”。
參考文獻
[1]《元史》卷175,第4089頁。
[2] 狄百瑞:《理學與心學》,第57—66頁。
[3] 李文勝:《論元代延祐科舉的意義》,第75頁。
[4] 鄧紹基:《元代文學史》,第370頁。
[5] 陳恒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第24—26頁。
[6] 陳恒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第29頁。
[7] 孫克寬:《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