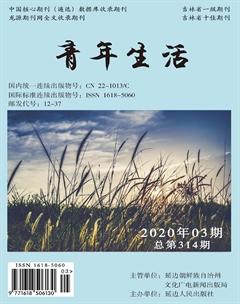鄉村的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如何協調推進
楊季明
摘要:“經濟決定政治,經濟發展決定政治發展”這一命題幾乎成為我國學術界普遍公理。但應用到我國鄉村層面上,我認為鄉村經濟發展并不能帶來政治發展,國家政權應是推動鄉村政治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不是鄉村經濟發展。本文淺析現階段鄉村政治發展與鄉村經濟發展的關系和內涵,并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對策。
關鍵詞:鄉村政治發展;鄉村經濟發展;協調推進
鄉村經濟建設和鄉村政治建設是當代我國鄉村發展面臨的兩項重要任務。現代化建設目標當然包括實現鄉村經濟和政治的現代化,但在這過程中,鄉村經濟發展和鄉村政治發展的關系,存在很多問題。分析當前我國鄉村治理的發展趨勢和面臨的困境。一是當前我國鄉村治理呈現新的發展趨勢:主體由“一元”向“多元”轉變、目標由管制向提供公共服務轉變、過程由權威服從向民主協商轉變;二是鄉村治理面臨的新困境:鄉村治理缺乏整體性研究、當前鄉村治理主體單一化、制度體制機制運行不統一、鄉村社會治理能力弱化;最后,從整體思路和具體路徑兩個方面得出推進我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路徑選擇。一是推進我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整體思路:“五位一體”綜合建設、“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基本制度體制機制有機統一;二是推進我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具體路徑:重構鄉村治理主體間良性互動關系、建構和完善鄉村社會治理多重機制、加快和全面提升鄉村社會的治理能力。以期適應時代發展潮流,解決當前鄉村治理面臨的新困境,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整體思路和具體措施,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貢獻微薄之力。伴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速,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那個曾經“與世無爭、隱形無聞”的鄉村社會,在市場化與城鎮化的洗禮之下,已經成為了經濟迅速發展、百姓安居樂業、鄉村文化繁榮的代名詞。
一、鄉村經濟發展與鄉村政治發展的內涵。
鄉村經濟發展是指鄉村社會經濟各方面由低級到高級,由欠發達到發達的變化過程,它反映了整個鄉村的經濟風貌,其首要目標是實現鄉村經濟現代化,根本宗旨是達到全村村民的共同富裕。具體來說,鄉村經濟發展包括以下方面的衡量指標:一是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和收入分配的狀況;二是村民健康指數和人口素質狀況;三是鄉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要素投入的比例狀況;四是生態經濟角度下的鄉村生態環境保護狀況。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指導下,鄉村經濟發展在我國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鄉村政治發展是鄉村政權組織為實現鄉村社區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和政治現代化所進行的政治活動過程,它可以涵蓋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基層政權組織機構、制度的完善以及政策的調適;其二是政權組織活動過程中的公眾參與程度。鄉村政治發展的目標就是要實現社會政治一體化,從而促進政治體系完成對基層社會的整合,鄉村政權組織滲透到基層社會,具有統攝鄉村社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方方面面的能力,使鄉村基層社會納入到國家現代化的統一進程中。
二、對鄉村經濟發展和鄉村政治發展關系再認識。
(一)現階段推動鄉村政治發展的動力是國家政權,而不是鄉村經濟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原理“經濟決定政治”可以說是真理,現階段鄉村政治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國家政權力量而不是經濟發展。參照于王滬寧教授的歷史——社會——文化的分析模式反證鄉村經濟發展不一定是鄉村政治發展的前提。在歷史上,皇權不下縣的做法沿襲了整個封建社會,鄉村毫無政治傳統,但鄉村經濟卻是向前發展的,這表明鄉村經濟發展并不一定帶來鄉村政治發展,且歷代鄉村政治變化都是政權自上而下改革的結果;現實社會中,貧困落后是我國鄉村的寫照,村民的一切行為都是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即使是新富階層積極從政,也是為自身經濟利益著想,村民經濟認同超過了政治認同,在經濟慣性影響下,鄉村政治發展會走向畸形;在文化上,鄉村政治文化的缺失是不爭的事實,且鄉村主流政治文化依然是官民分化、官本位思想特濃,且由于我國政治體制不健全,鄉村經濟發展只會加劇村民將政治作為獲得經濟利益的手段,或將政治作為高高在上的身份象征。因此,鄉村經濟發展不一定帶來鄉村政治發展。現階段,國家政權應是推動鄉村政治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國家政權要為鄉村政治發展提供制度條件,只有完善了制度,理清了政權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的關系,鄉村政治穩定發展才有可能;其次,國家政權應推動鄉村政治運行機制的法治化,規范村民形式政治權利及政治組織運用政治權力的手段,才能培育村民的政治認同,從而推動鄉村政治發展。
(二)“高工業化、高集體化、高個體化”的三高經濟模式是推動鄉村政治發展的理想模式。蘇南模式重集體、輕個體,溫州模式重個體、輕集體,這兩種模式都有其固有的弊端。“三高模式”綜合了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既重集體也重個體,摒棄了蘇南模式中的個體對集體的嚴重依賴和溫州模式中集體經濟缺失所形成的“空殼村”的現象。高集體化、高個體化倡導集體和個體的地位平等,主張集體和個體在平等的地位上以合作的方式達到對彼此的認同。集體經濟強大有助于村級政治組織獲得豐厚的財政來源,使其能夠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為個體發展創造條件,贏得個體的政治擁護;個體經濟強大可以擺脫對集體的過度依賴,增強了個體的獨立自主性,并且在平等的地位上同集體談判,獲得充分的尊重,能激發個體的政治興趣。在處理高集體與高個體的關系上,由于集體不能直接對個體進行命令控制,集體在推行某一政策時必須爭取個體的合作,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形成集體與個體的良性互動,從而推進鄉村政治的民主化進程。
(三)鄉村政治發展應優先于鄉村經濟發展,并需為后者帶來積極正效應,這也是村民雙重角色融合的條件在村民的雙重角色的關系中,“經濟人”角色是本質的,“政治人”角色是外在的,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礎之上的,并須為前者服務。村民作為“理性經濟人”,其一切行為都是基于自利的動機,如果想要促使村民積極參與政治互動,擁護政治權威,鄉村政治發展首先要為村民帶來利益,即要有所作為。主張鄉村政治發展優先于鄉村經濟發展,就是旨在鄉村政治能夠為鄉村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能夠給鄉村經濟發展帶來積極的正效應。如果依靠鄉村經濟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自行崛起,然后再推動鄉村政治發展,這是不可行的,原因是鄉村政治在鄉村經濟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功勞,理性的村民不會認同無益的政治參與。
因此,鄉村政治要想獲得村民認同必須積極作為。
具體做法上,首先,要構建鄉村政權與村民自制的信任機制,使鄉村基層組織的權力運用由法定走向合理,樹立權為民所用的正確權力意識觀;其次,將村民利益作為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引導村民致富,滿足村民“經濟人”角色的要求,從而推動村民產生政治認同;再次,鄉村政治要排除家族、宗派勢力的干擾,保持公平與公正,也是吸引村民政治參與的一大亮點。總之,只有鄉村政治主觀上樹立為民服務的觀念,行動上落實為民謀利,才能有效地將村民的雙重角色有機結合。
由此可見,想要實現鄉村政治發展和鄉村經濟發展協調推進,必須貫徹落實國家的方針政策,為了實現鄉村振興,首先,加強基層自治,強化民主建設。基層民主建設雖較為完善,鄉村社會自治的互動性良好,村民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不斷凸顯,但是仍需要進一步強化鄉村自治的制度設計,以推動鄉村政治的社會主義現代轉型。其次,按照政治體制改革的路線圖,落實戶籍、醫保制度改革,打破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公,突破權利壁壘限制,真正跳出“城市中心主義”的固化思維,強化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改革,制定傾向于農村的公共醫療與財政政策,使村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提升村民們的政治認同感和政治效能感。強化基層黨組織建設,基層黨組織是黨在基層特別是鄉村社會的戰斗堡壘,是鄉村政治社會化的中堅力量,也是黨在基層的代言人,其肩負著維持鄉村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的重任,也是各項政策制度在鄉村社會落腳與生根的重要保障。最后,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要充分運用現代治理理論,用鄉村精英和“新鄉賢”有效地把鄉村政治發展與鄉村經濟發展結合起來。自邁入新世紀以來,黨和政府對農村又好又快的發展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鄉村治理主體日益多元化,鄉村中有威望、有能力的新鄉賢開始著手鄉村治理之事,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群眾的贊許,成為不少農村地區村級治理的領頭羊,并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之一。鄉村精英和新鄉賢在秉承傳統鄉賢文化的基礎上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在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價值引導作用,不僅使鄉村振興戰略得以實施得可靠保障,還維護農村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進一步促進了鄉村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有機結合。
參考文獻:
[1]中國城鎮化戰略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建構[J]. 黃建洪.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02)
[2]基于“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政府本分”的轉換——從李克強關于政府作用的話語與實踐說開來[J]. 羅忠桓. ?西藏發展論壇. 2016(01)
[3]中國鄉村治理的回顧與展望[J]. 袁金輝. ?云南行政學院學報. 2016(01)
[4]我國鄉村治理模式的變遷、困境與內生權威嵌入的新鄉賢治理[J]. 付翠蓮. ?地方治理研究. 2016(01)
[5]社會結構變遷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J]. 姜裕富. ?重慶社會科學. 2015(04)
[6]城鎮化發展的“中國道路”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基于公共供求的視角[J]. 黃建洪. ?江漢論壇.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