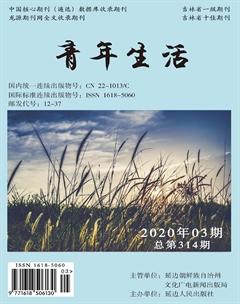淺析張愛玲小說的語言特征
李斯怡
摘要:張愛玲的小說具有非常高的造詣,尤其表現在語言方面。由于張愛玲本人具有非常高的文學素養,使得她的小說受到了大量讀者的歡迎。她的小說中綜合運用了多種語言表現手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本文結合小說語言的具體實例,分析了小說作品中在語言上具有的種種特征,如小說語言中具有的古典性、反諷性、色彩性等等。
關鍵詞:張愛玲;小說;語言特征
一、小說語言具有豐富的古典性
張愛玲具有非常高的古典文學素養,這是受到了家庭的影響。張愛玲對古典文學作品例如《紅樓夢》等非常感興趣,由于在古典文學方面具有濃厚的造詣,這對張愛玲后來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雖然張愛玲受到了正規的西式教育,是現代文壇上的大家,但是她的作品尤其是小說中,都能看到古典文學的影子。例如在她的中篇小說《金鎖記》中,就有很多類似于《紅樓夢》的語言描寫片段。如作品中的一段對話是這樣寫的:
“小雙道:告訴你,你可別告訴你們小姐去!咱們二奶奶家里是開麻油店的。鳳簫喲了一聲道:開麻油店!打哪兒想起的?像你們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的小姐,我們那一位雖比不上大奶奶,也還不是低三下四的人”,這一段話人物的語氣和語言強調與《紅樓夢》中的人物語言極其相似,語言活潑俏皮,人物形象十分鮮明。《金鎖記》中對曹七巧的描寫和《紅樓夢》中的王熙鳳有著相似之處,出場濃墨重彩,對于其服裝、外貌描寫的很細致,將曹七巧的刻薄潑辣的性格展現的淋漓盡致。
二、小說語言具有濃厚的反諷性
張愛玲小說在反諷的使用上還是比較多的。為了收到語言的表達效果,尤其是強調的意味,所以特別在語言上做了反諷的處理。張愛玲小說語言在反諷方面運用了很多的方式。具體來說,主要在場景的搭建以及詞語的運用上運用反諷這一語言藝術。
在場景的搭建上進行反諷。這種反諷方式主要指的是通過構建一定的場景,在內容以及含義本身進行反諷。特別是將作品中的人物以及情節置身于現實生活、現實場景中,運用一種和現實生活、現實場景截然相反的背離,表現出諷刺的意味。例如在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中,用“傾城”來成全小說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的“戀愛”,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男女主人公的“戀愛”也缺少純粹性,但是用一個城市的“淪陷”來表現這種并不純粹的“戀愛”,本身就具有非常大的諷刺意味,收到了小說語言所應該表達的效果。
三、小說語言具有冷暖色彩性
張愛玲的小說具有較濃厚的色彩性,她的小說的總體色彩基調的“蒼涼”的,這種蒼涼尤其在語言色彩的運用上更能體現出來,用語言的色彩來襯托并推展小說的情節。張愛玲小說中很多語言中運用了相對暖色調的詞以及冷色調的詞,用冷色調的詞直接表達了小說主題特別是小說人物的蒼涼之感;用暖色調的詞從相反的角度來反襯出深層的蒼涼之感,雖然是暖色調的,但是表現出生活中頹廢、無助等等。例如在其作品《沉香屑·第一爐香》中有這樣的描寫: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鵑花,正在開著,花朵兒粉紅里略帶些黃,是鮮亮的蝦子紅。墻里的春天,不過是虛應個景兒,誰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墻里的春延燒到墻外去,滿山轟轟烈烈開著野杜鵑,那灼灼的紅色,一路摧枯拉朽燒下山坡子去了。杜鵑花外面,就是那濃藍的海,海里泊著白色的大船。該語言描寫是對周圍環境的色彩描寫,張愛玲前后用了“粉紅”“黃”“蝦子紅”等色彩詞,將梁太太家的庭院勾勒得一覽無余,其后又用“淺藍”“白色”作對比,實際上是寫出了絢麗惹眼的杜鵑花與平凡無奇的葛薇龍的格格不入。杜鵑花似紙醉金迷的酒吧樂舞,她則是清遠悠揚的鋼琴小夜曲,而世人卻沉醉于燈酒霓虹,無暇顧他。
四、小說語言具有律動的音樂性
1、疊字—聲韻和諧
在張愛玲小說中,疊音隨手拿來,處處可見,形式多樣,頻率又高,而且這樣的疊音“未必就是副詞、形容詞,卻是用做副詞、形容詞的居多”。例如:《半生緣》中“平時常常站在窗前看著他來的,今天她卻不愿意這樣做,只在房間里坐坐,靠靠,看看報紙,又看看指甲。”“坐坐”、“看看”“靠靠”、都是動詞的疊音形式,在此時的作用就是表示其短暫的特性,這樣幾個看似簡單的字就顯示出曼禎當時不愿意的那種左右不是,百無聊賴的復雜,語言表達簡單,但是綻放出靈動活潑的文字生命感,語言的和諧,讓人感到舒服也讓人覺得很真切。
2、反復—整齊回環
反復,在文學作品中的有著展現語音的節奏的作用,構成有意味的形勢。在文學環境中,往往體現出一種環環相扣的回環之美,也是音樂性語言形成的特殊手段。如:《金鎖記》中“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 我有什么地方不好……”曹七巧大膽地向季澤求愛,季澤卻拒絕了她,重復出現“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的句式,這種看起來很哆嗦的單調的語言,往往是實際生活境況演變而來的,會發現這就是每一個相似境遇的人(七巧)對溫柔的渴望與欲求,她的那種困惑以及哀求般的痛楚,被這些反復的文字加重,讓讀者深感其中,讓人感到她的凄美之感,很具有震撼力。
五、小說語言具有豐富修辭性
在成功的文學作品中修辭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寫作方式,其在某種程度上對于文章主體的質量有著直接的影響。然而,通常來說,修辭在作品中往往不會占據主體的地位,這是由于比喻與意向過多使用會影響到小說情節的發展。但是,在張愛玲的小說當中,比喻與意向并不是影響小說情節開展的因素,而是造就了小說作品的成功。在《紅玫瑰與白玫瑰》當中,張愛玲對王嬌蕊的神態進行了細致的描寫,“她穿著一件曳地長袍。是最鮮辣的潮濕的綠色,沾著什么就染綠了。”讀者讀到這里只需要細細的一想就可以在腦海中浮現出這種綠色醒目到讓人難以接受的程度,這種綠色占到什么就能夠把什么的染成綠色,甚至連透明的空氣都可以留下綠色的影子目。張愛玲采用這一比喻手法也巧妙的暗示了王嬌蕊與振保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王嬌蕊甚至可以穿透振保呼吸的空氣。整體來說,張愛玲小說中這種精妙的比喻與意向幾乎全部都來自于人物身邊的景物與事物等,并且夾雜在男女之間的日常故事當中。
結語:
張愛玲的小說語言具有獨特的風格。在閱讀并鑒賞張愛玲的小說中,要認真分析小說中語言的風格以及特點,從中感受到張愛玲小說中語言的獨特魅力。
參考文獻:
[1]曾守群. 蕭紅與張愛玲作品中的創作比較研究[J]. 武漢冶金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16(02)
[2]姜良琴. 蕭紅與張愛玲女性主題小說的比較與分析[J]. 語文建設. 2015(11)
[3]韋家海.試論張愛玲小說創作心路變化根源[J].安徽文學(下半月).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