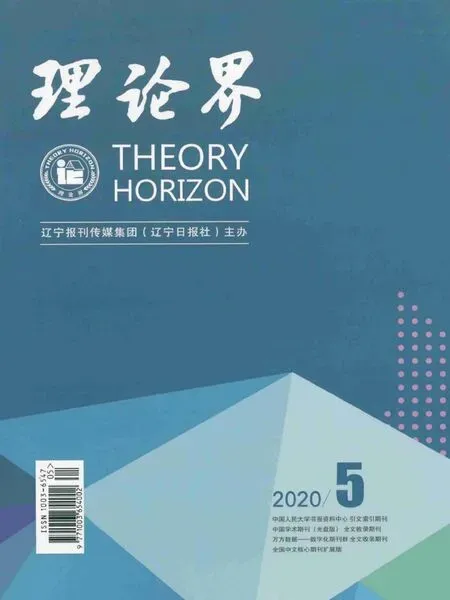生存論視野下論儒家與存在主義救贖觀的差異
何剛剛
學界近年來興起了儒學與現象學比較的風潮,但對于繼承了現象學方法的存在主義與儒家的比較很少。劉東先生在其著作《天邊有一塊烏云:儒學與存在主義》中提出,儒家與存在主義的關系最為密切,“不論是兩者對神靈采取的“缺省”處理方式,以及將關切點轉向現世人間的“有限理性主義”,兩者都存在著極大的相似性與可比性。因此,劉東認為唯有薩特哲學或加繆文學的那個時代,反而才最為類似先秦儒者面臨的思想困境。隨著儒學與現象學比較的深入,儒學與存在主義之間的比較必定會成為一個新的熱潮。因此,本文嘗試從生存論角度去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分析它們救贖觀之間的不同,為兩者之間的進一步比較研究建立基礎。
一、儒家與存在主義生存論三維度的差別
生存論即圍繞人的生存而展開的研究。人何以生存既與他如何存在有關,也與他如何看待生存聯系在一起。說到底,生存論的核心是生存方式的問題。“人的生存之所以不同于動物的生存主要是在于人按照對象的需要具有自我創生性。生存論還包括對人的生命體驗、生存領悟和生活信念這些要素的揭示,進而使得人生存得到全面的展開。因此,生存論就是人的生命在周遭世界中的表現和的體驗活動。”〔1〕因此,下文主要通過生命意志的展開,時間體驗的不同,以及自我與他人的關系等三個方面來分析儒家與存在主義生存論的不同以及兩者救贖方式的差異。
1.生命意志的指向不同
所謂生命意志指的是文化潛意識中的一種東西,它以生生不息的欲望對于人類具體的生存活動進行影響。每個文明中都有各自內在的一種生命沖動。關于東西方的生命意志問題,梁漱溟先生曾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有文化三路向說。其實這種劃分并不見得精確,但是他認為西方文明是一種進取性的文明。這是比較恰當的。存在主義繼承了西方意欲向前的浮士德精神。這種精神表現為對于某種宿命性力量的反抗。這種宿命性的力量可以是理性,也可以是上帝抑或其他存在。這種生命意志表現為不斷地向前進取。如存在主義認為“正因為荒謬,所以才肯定。爭取把不可能變為可能,乃是一場瘋狂的斗爭”。可見,這種進取實際上也暗含著斗爭性。
而儒家的生命意志始終在追求天人合一。它欲以一個定點,逐漸過渡至更為廣闊的境域來尋其宇宙之大全。錢穆先生曾說:“中國文化以自我為中心推到世界外圍,用有限去追求無限,故而中國文化在于對于無限的宇宙之大自然而融為一體者的追求。”〔2〕所以中國文化雖然強調諸如“心”與“性”這些內在的概念,但其實這些概念永遠離不開天與道。所以《中庸》說:“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3〕可見,天人合一才是其追求的意欲之所在。而存在主義中不論是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還是尼采所提出的超人意志,實際上都是繼承了不斷向前的浮士德精神。
2.對于時間的領悟不同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認為儒家的時間觀與西方的時間觀的差別是標度性的時間與體驗性的時間之間的差別,又將西方的時間觀分為循環式的時間觀與線性的時間觀。〔4〕但是這種劃分其實是有問題的。儒家與西方的時間觀不在于線性與非線性的差別,而在于儒家對于時間的表達始終要與其他萬物聯系在一起。它的表達方式,也基本運用具象化的語詞。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樣就將時間轉化成為了生存世界的一部分。有學者認為,儒家是以物觀時空。利用微粒性的“氣”來觀測時空。〔5〕可見,這種時間觀始終與具體的生活世界相聯系。
而西方,在希臘時期確實是一種循環式的時間觀。在《蒂邁歐篇》中柏拉圖指出,時間是“永恒”的運動摹本,并依照數的法則運轉,為了說明時間的計量,他揭示了一種宇宙原初的“世界大年”,亦即以所有行星從同一地點出發最后同時回歸到原初位置的歷時為一個“世界大年”。在柏拉圖看來,創造主創造了諸個星辰,并用星辰的循環運動來確定計量時間的數,“世界大年”就是最大的時間單位。〔6〕海德格爾在胡塞爾的基礎之上提出時間性的“綻出”。海德格爾視“將來”“過去”和“當前”為流俗的時間領悟。他反對將時間看作一種無始無終的現在序列,并由此引出了“此在式空間性的時間性”的概念。薩特的時間觀也重視將來,并受到海德格爾“到時”概念的明顯影響,但他承認“過去”的確定性,他論述的兩個角度:存在與虛無、自在與自為,這些都是海德格爾所沒有的。薩特認為,不論是柏格森和胡塞爾認為過去是存在著的主張,都把現在和過去的橋梁切斷了。〔7〕薩特將時間有看成了一個有組織的結構,薩特的時間觀為他關于自由選擇的生存論哲學奠定了重要基礎。因此,可以說以薩特為代表的整個存在主義哲學家都在某種意義上是在維護穩定的時間序列結構。
3.自我與他人的關系
在自我與他人的關系這一問題上儒家和存在主義是有著鮮明不同的。儒家強調自我與他人的和諧,而存在主義強調自我與他人沖突。儒家常講的“仁義禮智”,固然是所謂的“非外鑠與我”,但其實都需要和他人在共存之中實現。可以說,儒家文化中的“我”其實并不能脫離他人,“我必在人之中成一我,我若離了人,便不再見有我,舜與周公之最高德性之完成在其孝,舜與周公之最高品格在成為一孝子,但若沒有父母,即不見孝子的身份,更何有孝的德性之表現與孝的品格之完成呢?”〔8〕儒家的道德規范都必須在與他人的共存之中才能實現。
而存在主義認為個體與他人的關系永遠是若即若離的。因為一方面實現自我的救贖需要與他人形成特定的指向關系,而另外一方面群體對于個體的救贖始終會造成一些阻礙。如海德格爾認為此在,共在作為此在的生存論建構和本質結構,此在與他人總是“共同存在”于世界之中,而在日常生活中,此在和他人都是以“常人”這種方式共存于世。這個常人就是無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在中又總已經聽任這個無此人擺布了。這實際上是一種此在的沉淪。薩特探討自我與他人關系時說:“他人的存在向我揭示了我所是的存在,但是我又不能將這種存在回歸于己有,所以這種存在引起了兩種對立的存在,一方面他人的對象性是我存在的毀滅,另一方面他人又是自在存在的基礎。”〔9〕薩特認為,他人與自我的沖突并不是一種對抗式的,而是一種共在關系之中的沖突。
二、存在主義與儒家不同的生存體驗
生存論影響了對外部世界的體驗,這種體驗又影響了對于外部的世界的領會與感知不同。存在主義所感知到的是一種荒謬,而儒家所感知到的是一種荒涼,存在主義的情感側重于孤獨,而儒家是一種孤寂,存在主義所要解決的是主客之間的恐懼感,而儒家所要解決的是個體對于未知的憂懼意識。
1.荒謬與荒涼的生存境遇
不同的生命意志影響著不同的生存境遇。由于存在主義的生命意志繼承了浮士德精神,它是一種勇往直前的欲望。而儒家的生命意志追求的是一種天人合一。這就造成了面對世界兩種不同的原初體驗的差異。儒家追求的天地萬物一體,使得它始終將自我與天地萬物聯系在一起,看到人生的界限之所在,認識到個體的卑微與渺小,由此產生出一種荒涼感。如孔子在晚年面對著一種失意、落寞,而在流動不息的河流中感受到人生無常的荒涼,不禁感嘆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而朱熹在晚年也流露出同樣的荒涼感,這尤其表現在他晚年仕途失意之后所寫的詩之中,如“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盡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10〕這種失意之后的荒涼感在儒家知識分子的詩歌中屢見不鮮。
而存在主義的生命意志,產生的是一種荒謬感。荒謬感是指人與生活世界的脫離,主體與世界產生了一種不協調的沖突感。“荒謬”一詞來自于拉丁文,意思是“不合乎曲調,無意義的”。“absurds”(荒謬)其前綴“ab”作用是加強語氣,后綴“surds”意思是“聾”或“被蒙住”。“荒謬”一詞在西方哲學史中具有深遠的歷史背景。基督教哲學家德爾圖良就曾說過“因為荒謬,所以相信”。在德爾圖良那里是指信仰與理性精神沖突之后產生的感覺。
西方單一線性的生命意志意味著世界有一個點性的開端和歸宿,而發生在這時間之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獨一無二的。它無疑默許了一種崇高感的存在。這種崇高感可以對應上帝,也可以對應于理性。然而,如果這種線性的觀念受到沖擊之后,那么耶穌赴死本身也成為一件極為平常的事,所有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還要發生。所以尼采曾說:“你現在和過去的生活也就是你以后的生活,并且再過無數遍,其間將沒有任何新東西,而只有每一種痛苦與快樂,每一思想和每一聲嘆息包括這個蜘蛛與樹間的月影,也將一再重復。”這是尼采在用消解一元性的方法來批判基督教。然而,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保證了崇高性、唯一性的同時,也使得所有的人都處于一種“被剝離”的狀態,人可以成為“局外人”去直面終極的問題。由于所有人本身都是獨一無二的,所有的生活在線性的時間里也都是神圣的。但是當人在循環之中如果追問到“意義”之時,就會對自己所在的世界以及所做的事情產生質疑,荒謬感也就由此產生。
2.孤獨與孤寂的個體體驗
在生存體驗上,存在主義感受到的是孤獨,而儒家感受到的是孤寂。平面化的時間觀之下,處在時空之上的每一個定點的位置實際上是永久不變的,過去、現在、未來是三個互不相容的位置,每一件事情必須坐落在其中一個時間節點上,而且只能是一個,具有極強的排他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時間的位置總是相對的,現在的事情,在過去就是未來,在未來就是過去。〔11〕如存在主義代表人物薩特的時間觀是一種結構化的觀念。薩特的時間觀總結為:忘掉過去,關注現在,面對未來。在這種時間觀之下,個體永遠宛若時間上的一個定點,雖然與其他的點看似處在聯系的狀態,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孤零零的原子。
而對于儒家而言,時間始終需要和自然萬物結合起來表達。《孟子》中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這種時間是與農業生產聯系在一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天道與萬物的永恒性與個體的有限性之間產生了強烈的對比,個體渺小的失落感就會油然而生。在中國古代的詩歌中這種孤寂與落寞表現得很多。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描繪了一幅空曠,孤寂的圖景。而王陽明在被貶貴州之后,看見那死去在上任途中的異鄉人,在無比孤寂的心情下寫出了流傳千古的《瘞旅文》。“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游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12〕
3.恐懼與憂懼的生存困境
存在主義與儒家在個體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上有很大不同,存在主義產生的是一種恐懼,而儒家產生的是一種憂懼。恐懼在于它有一個特定的客體,給人的壓迫感更大,憂懼雖然有一個客體,但是這種客體并不形成對抗性的關系,而且最終會轉換成為主體的一部分。
在圣經中處理人神關系時,用到的詞是“恐懼”。基督教文化深刻地體現了在恐懼情感下,人對于上帝的絕對服從。如上帝為了考驗約伯的信仰,不斷地賜給他苦難,而約伯在這種苦難中依然對于上帝充滿了無限的崇拜與服從。而克爾凱戈爾在《恐懼與顫栗》中更是把這種服從中的恐懼感刻畫得生動至極。“亞伯拉罕帶著以撒騎著毛驢沉默著走了三天,第四日清晨當到達摩利亞山附近時,亞伯拉罕依舊一言不發。”在這種沉悶的氣氛中蘊藏著巨大的恐懼感。亞伯拉罕自然對于上帝是無限的忠誠,但是上帝所命令的事將與倫理發生悖論。因此,即便最終亞伯拉罕完成了上帝對于他的考驗,但當他獻祭完畢回家之后,“變得老態龍鐘,他不能忘記那件事帶給他的恐懼感,亞伯拉罕眼前一片黑暗,他再也看不到歡樂與愉快了”。〔13〕這種恐懼感是存在主義所面臨的一個生存困境。
而儒家的時間觀造就的是一種憂懼感。儒家的時間觀使得它能看到當下生存狀態的另外一面,能從喜悅的一面,感受到無限的悲涼。宛若一個轉動不息的陀螺,能夠在喜悅的一面感受到憂懼。這種憂懼并沒有特別客觀的對象,它指向的是一種模糊的未知狀態。如在《詩經·豳風·七月》中說“春日載陽,有鳴倉庚”的歡樂時,也更多地流露出“無衣無褐,何以卒歲”〔14〕的憂懼。這是對于未知的一種憂慮。因此,《周易》不斷強調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等。而《孟子》中說:“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15〕這也表現了對于未來的憂懼。《周易》中最后一卦是未濟卦,這是借“未能濟渡”說明事情未能成功,固然在“未濟”中有向“既濟”轉換的希望,但是在這種希望中對于未來又充滿著無限的憂懼意識。
三、兩種救贖觀的差別
存在主義與儒家生存論的差別,影響了他們對于感性世界的認知。而對生存境遇感知的差異,又影響了他們的救贖觀。總的來看,這種差異體現在救贖的方式、救贖的主體以及救贖的終極價值等三方面。
1.救贖的方式:反抗與消融
存在主義的時間觀之下每一個時間節點都需要與其他的時間點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之下,每一個時間點都受到束縛,擺脫掉這種確定性就必須借助反抗性的救贖方式。如加繆筆下的默爾索,他認為基督教的確定性本身是需要質疑和反抗的,所以他認為雖然自己兩手空空,但是他也絕不會接受神父為他預設的確定性,他一無所有,對于未來沒有把握,但是他至少能夠把握現在。〔16〕這種對彼岸世界的摧毀實際上是對確定性的反抗。而儒家的救贖方式則是在擴充中消融苦難。這種救贖方式具有極強的伸縮性。它以一個基本的孝悌觀念為出發點,而后將其普遍化。如《論語》中所說的“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西銘》中所說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都是如此。它使得宇宙萬物成為一個大我,在這個大我之中,一切矛盾與悖論都會被消解。因此,儒家的救贖方式不在于反抗,而在于放置在一個更大的維度中去消解矛盾。
2.救贖的動力來源:激情與仁愛
存在主義的個體體驗側重于孤獨,而儒家側重于孤寂。兩者要擺脫這種狀態,都需要用愛來救贖。然而,儒家的愛可以由孝悌的“差等之愛”進而過渡到“一體之仁”。而存在主義的愛更側重于激情。因此,德爾圖良和克爾凱戈爾堅決聲稱,“因為荒謬才可信,正因為不可能才肯定,爭取把不可能變為可能,乃是一場瘋狂的斗爭,都是一場瘋狂的斗爭,是以眼淚、呻吟和詛咒為代價的斗爭”。這種激情將愛賦予特定的指向來實現救贖。然而問題在于,這種激情有時候會吞噬掉愛本身,使得反抗超過了應有的限度。因此,薩特強調自由背后是責任,而加繆也說反抗應該遵守一個限度。他說:“反抗在歷史上也是一個無規律的擺鐘,在不確定的弧形上不停擺動,不斷追尋自己最完美、最深刻的節奏。但是這種不規則不是絕對的,它始終圍繞一個中軸,有自己的調整與限度。”〔17〕薩特和加繆都認識到了依靠激情所支撐起來的愛具有的危險性,因此,用限度來規范它。而儒家的愛并非只對于一個特定的對象,而是帶有一定的伸縮性。
3.救贖的終極價值:自由與中和
存在主義面臨的是個體的命運受到注定之后的荒謬感,終極目的在于實現自由。薩特在《禁閉》中把我與他人的關系說成“他人即是地獄!”由于每個人都有絕對自由,都把自己當作主體性存在。“每個人如一口陷阱,時刻準備埋藏他人主體性存在。”〔18〕因此,個人的自由永遠受到他人的限制,因此,可以說自由才是存在主義所追求的最核心的價值。薩特的哲學核心就是在追求自由。薩特曾說“人是自由的”,“事實上,我們被判處了自由這樣一種徒刑”。而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最終的目的也是為了實現自由。由此可見,存在主義的終極價值就是自由。而儒家的終極價值在于追求中和。因為儒家的憂懼感是在個人的有限與天道的無限,個人的渺小與自然的遼闊的對比中產生的。因此,它對矛盾的解決并不訴諸對抗性的方式,而是內化于主客不分的和諧狀態。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中庸》中也認為“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因此,可以說存在主義追求的終極目的在于個人的自由,而儒家追求一種個體與整體之間的和諧,儒家最終的目的并不在于個人,也不在于他者,而側重于個人與他者之間的一種關系的協調,這種關系使得主客之間喪失了對抗的可能性。因此,儒家的救贖側重于關系,而不是主客,側重于關系的中和,而不是主客的對抗。
四、結語
從生存論角度而言,儒家與存在主義從生命意志到對于時間的領悟,以及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三個方面都存在不同。存在主義的生命意志表現為不斷向前的浮士德精神,而儒家的生命意志追求天人合一。存在主義是結構化序列的時間觀,而儒家是多維的時間觀。存在主義的他人與自我的關系充滿了沖突,而儒家強調自我與他人的和諧。從這三個角度來看它們的生存境遇,存在主義流露出的是一種荒謬感,個體體驗是一種孤獨,對于生存表現為一種有對象化的恐懼感,而儒家則是情感上的荒涼,個體體驗上的孤寂感,而對于生存表現為一種無對象化的憂懼意識。這就決定了在救贖層面而言,存在主義的方式是反抗客體,救贖的動力是激情,企圖達到的目的是自由,而儒家的救贖方式是消融主客,救贖的動力來源是愛,追求的終極目的是中和。因此,儒家與存在主義在對于生存的處境問題上存著許多相似性的觀點,對于存在主義與儒家救贖方式的對比研究,能促進兩種理論之間的融合與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