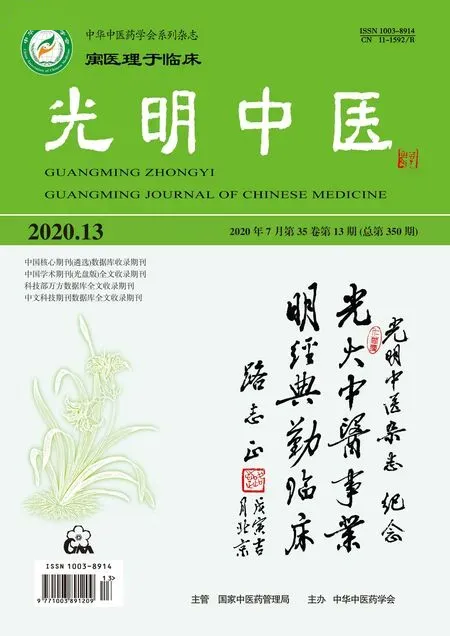廖世煌教授“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的應用*
吳宇金 廖世煌
“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出自清代醫家葉天士所著的《溫熱論》,針對濕熱病提出了“通陽利小便”的治療原則。濕熱病以濕邪彌漫,阻滯氣機,陽氣因而不能布達,故治療在于宣展氣機,淡滲利尿,使濕邪從小便而去,濕去氣通,陽氣自然布達。
廖世煌教授是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基礎學科金匱要略博士及碩士研究生導師,主任中醫師。廖世煌教授從事教學、臨床與科研工作近50年,除深入鉆研《金匱要略》外,還對《溫病學》等經典也有頗多建樹。廖老師認為廣東地處南嶺以南,氣候炎熱多濕而多瘴霧,四時季節不分明,濕熱之氣常盛,故長期生活在這種氣候環境下,其人多見陰虛或濕熱體質,脾胃濕熱證常見,強調在遣方用藥時要因地制宜,而“通陽利小便”法則能指引治療嶺南地區常見的脾胃濕熱證。筆者有幸跟師學習,觀察廖教授運用“通陽利小便”法治療脾胃濕熱證每多獲良效。本文茲將廖世煌教授運用“通陽利小便”法的經驗介紹如下。
1 理解“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
廖教授認為學習務必從源到流,學好經典,對于臨床辨證施治及深一步研讀后世醫書能夠奠定堅實的基礎,學好中醫基礎是提高臨床療效的重要條件。
1.1 條文解讀“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出自清代醫家葉天士所著的《溫熱論》第九條“且吾吳濕邪害人最廣……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血,而在津與汗,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然較之雜證,則有不同也”。該條文闡述濕熱為病與體質的關系及其治療的有關問題。首先提出居住環境與發病的關系,吳越地區易感受濕邪發病;濕熱為患與體質有關,“面色白者”,是素體陽氣不足,若感受濕熱之邪,治療宜清熱祛濕兼顧陽氣;“面色蒼者”,是素體陰虛火旺,若感受濕熱之邪,治療宜清熱化濕兼顧津液,切忌溫補;濕盛體質的人外感濕熱邪氣,易內外合邪發為濕熱病,濕熱病以脾胃為病變重心,隨體質不同,證候類型有“胃濕”與“脾濕”的區別;最后提出了治療原則:溫熱病“救陰”,濕熱病“通陽”,而“救陰不在血,而在津與汗,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是進一步闡述“救陰”與“通陽”兩大法則的具體運用。歸納起來,葉天士“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含義是說,濕為陰邪,容易閉郁氣機,陽氣因而不能布達,故治療在于宣展氣機,淡滲利尿,使濕邪盡從小便而去,濕去氣通,陽氣自然布達[1]。
1.2 通陽不在溫“通”者行也,“陽”者氣也,通陽即屬行氣,氣行則陽通。濕為陰邪,易阻遏氣機,損傷陽氣,陽氣因而不能布達,濕邪熏蒸三焦,上下彌漫,清陽之氣受阻,升降樞機不利,濕濁內蔽,內外交困,上可阻礙肺氣、蒙心,中可困脾,下注傷腎,致使全身陽氣不得暢通。廖教授認為濕邪閉阻陽氣乃屬必然,故通陽為濕溫之主要治法。而“通陽”的方法,也適用于諸多的陽之不通。陽氣有溫煦、推動、固護、防御、氣化等作用,當機體因濕熱、寒濕、寒凝、痰瘀、飲停等阻遏陽氣時,均可表現為郁滯、阻遏陽氣閉郁不通之病證,此時均可用通陽法[2]。廖教授強調要分清“通陽”與“溫陽”的概念。溫陽是用溫熱性質的方藥祛除寒邪和溫復陽氣的一種治法,是為陽氣衰微,陰寒內盛而設,主要用于中焦虛寒、亡陽欲脫、寒凝經脈等證。《傷寒論》中形成了一整套溫陽祛寒的方藥,如小建中湯、附子湯、四逆湯、干姜附子湯、真武湯,桂枝附子湯等。廖教授認為多數人在臨床中重視溫陽,但對濕邪郁陽,人們往往會忽視,他強調在雜病中陽氣不通之病機屬濕邪阻滯,或瘀血阻滯、痰瘀互結等,阻礙氣機運行,其癥酷似陽虛之惡寒,或某局部惡寒者,當用化濕、活血行氣、活血化痰等法,使其陽氣以通行。
1.3 利小便利小便法《黃帝內經》謂為“潔凈府”。《傷寒論》氣化失司者,用化膀胱寒水之氣的“五苓散”及水熱互結下焦、傷津之“豬苓湯”,后世清下焦濕熱之“八正散”等方,皆為利小便而設。濕熱病中濕阻氣機,陽氣不通,治療原則為分消濕熱,而以祛濕為要,淡滲利尿,使濕邪從小便而去,濕去氣通陽氣布達。廖教授臨床常用茯苓、薏苡仁、萆薢、蘆根等淡滲利尿,強調如果過用、早用苦寒清泄,不僅濕邪不能祛除,反致氣機閉塞,陽郁不通,濕熱為寒涼壅遏于內,邪無出路,而成壞證。廖教授認為葉氏所云“利小便”之法,是為了強調祛濕可以通陽,并非指單用淡滲利尿之品通利小便,而是代指宣上、暢中、滲下分消走泄之法。因濕熱病的病機是濕邪阻滯三焦,上下氣機不通,所以治療應分消走泄之法,宣上、暢中、滲下并施,使肺氣宣暢,脾升胃降,水道通調,邪有出路,三焦彌漫之濕得以祛除,氣機暢達而陽氣自通。
2 “通陽利小便”在脾胃濕熱證的應用
廖教授指出葉氏“通陽利小便”是針對外感熱病中的濕溫病而設,但也同樣可以用之于內傷雜病之脾胃濕熱證。溫病濕熱與脾胃濕熱證兩者都是以脾胃為中心,其發病機理可以互相影響,但溫病濕熱以外感為主,而脾胃濕熱證以臟腑功能失調為主[3]。“脾胃濕熱”是中醫脾胃理論的重要內容,是指濕熱內蘊,中焦氣機升降失常,脾濕胃熱互相郁蒸所致的一種病證[4]。脾胃濕熱證的形成,與人體素質有密切的關系,“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脾胃虛弱是罹患濕熱的前提,外感濕熱病邪為濕熱證發病的誘因之一。廖教授認為嶺南地區氣候炎熱、潮濕,濕熱之氣常盛;加上現代生活的環境、飲食結構、體質因素發生變化,飲食偏于厚味,心理壓力大等原因,故臨床脾胃濕熱證較為多見。脾胃濕熱證的病機為:濕熱困阻中焦,脾胃升降失司,上逆下流橫泛[5]。病變部位以中焦脾胃為中心,可上逆影響肺臟,下流傷及腸道,橫逆波及皮膚。以脘腹痞脹,納呆嘔惡,肢體困重,便溏不爽,渴不多飲,舌紅苔黃膩,脈滑數等為常見癥的證候。濕熱蘊結中焦脾胃,升降失調,濕熱上逆郁肺氣,出現咳喘;濕熱下流腸道,可見便溏、下痢;濕熱橫逆肌膚,身目發黃、濕疹瘙癢、黃水;濕熱上蒸,口腔糜爛;濕熱困阻中焦,濁氣上泛,清陽窒阻,可出現暈厥、耳聾、目痛。廖教授指出治療脾胃濕熱證的關鍵是調理脾胃,通達氣機,分解濕熱,葉氏“通陽利小便”法給脾胃濕熱證以治療的啟迪。脾胃濕熱證的治療,注重分解濕熱之邪,恢復中焦脾胃氣機之升降功能,抓住濕這一關鍵進行辨證治療。或淡滲通利,或清熱化濕,或芳香化濕,或苦溫燥濕,或多法聯合應用,注重通利三焦之氣,給濕邪以出路,濕去邪無所依則孤熱易清,徒清熱則易傷陽氣,且易濕熱復聚。此即葉氏“熱自濕中而出,當以濕為本治”“熱從濕中而起,濕不去則熱不除也”[6]。予宣上、運中、滲泄三法同用,以分解濕熱之邪,宣通氣機,恢復脾胃升降功能。這是“通陽利小便”法在脾胃濕熱證中的應用。
3 醫案舉例
尹某,女,66歲,2017年11月就診。干燥綜合征病史,口干,鼻干,唇爛脫皮,疲倦肢冷,胃納好,大便日1次,便溏,眼屎多,活動后氣不順。觀其癥:疲倦,大便質爛,舌體胖,有齒痕,苔白膩,脈滑為脾虛有濕;胃納好,口干口渴,眼屎多,舌紅為胃熱,濕熱之象;口干、鼻干、唇爛脫皮、肢冷均為脾胃濕熱,濕熱困阻中焦,運化不暢,影響津液輸布,津液不能上承濡潤,故口干、鼻干、唇爛脫皮,陽氣受阻,不能溫養故肢冷,證屬脾胃濕熱。廖教授擬益氣健脾,淡滲利濕之法,方用參苓白術散加減以調理脾胃,通達氣機;予茯苓、薏苡仁、萆薢、蘆根淡滲利濕,分解濕熱。擬下方:黨參30 g,太子參30 g,砂仁(后下)10 g,白術10 g,懷山藥30 g,扁豆20 g,茯苓30 g,薏苡仁30 g,川萆薢20 g,蘆根15 g,天花粉20 g,枸杞子15 g,麥冬10 g,五味子10 g。一周后復診癥狀有好轉,其后原方加減服3個月,口干、鼻干、唇爛、肢冷癥狀均有明顯改善。
4 小結
廖教授教誨我們要夯實基礎,熟讀經典,進而領會精髓,臨床療效才會提高。通過學習中醫經典名句“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在對原著作全面認識的基礎上,理解其不但用于濕溫病,還可以廣泛指導其在內傷雜病的運用。臨證中須勤讀、熟讀古籍,學以致用,臨床運用方面才能有新的領悟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