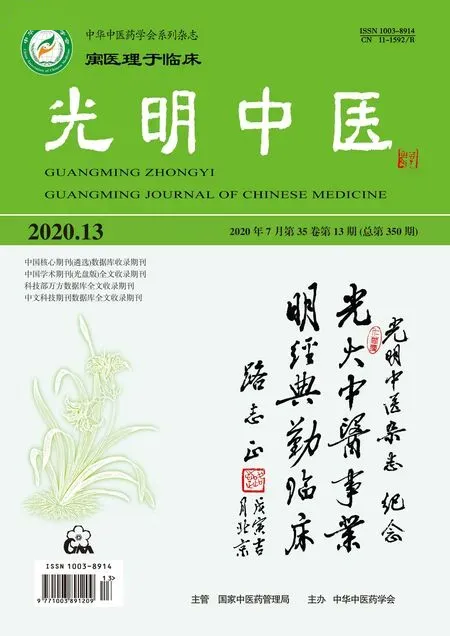宋承杰對脾胃病的辨證施治
宋艷敏
宋承杰,名老中醫,副主任中醫師,出生于中醫世家,從事中醫臨床研究50 年,主攻脾胃肝膽病,經驗頗豐,臨床收效甚佳。本篇主要介紹宋老對于脾胃病的一些獨到的見解,中醫對于脾胃功能的論述,《素問》云:“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靈樞·營衛生會》說:“人受氣于谷,谷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人體以五臟六腑為中心,脾胃就構成轉輸精華及氣機的樞紐。醫史上對“脾胃學說”的專著,其代表人物是金元時代的李東垣,其所著《脾胃論》中反復強調脾胃對人體生命活動的重要性,并力倡補脾胃,提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論點,從而被稱為“補土派”。在整個消化過程中,脾主運化包括運化水谷和運化水液,并將這些精微物質逐漸地轉化為人體的氣血津液,故脾胃為“氣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若脾失健運,則機體的消化吸收機能隨之失常,而會出現腹脹、厭食、便溏,以致倦怠、消瘦和氣血生化不足等病變[1]。分別類似于西醫里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急慢性胃炎、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萎縮性胃炎及缺鐵性貧血等。《素問·至真要大論》說:“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脾失健運,不能運化水濕,能引起水腫。
脾主升清,正如李東垣強調的脾氣升發則元氣充沛,人體始有生生之機,由于脾氣的升發才能使機體內臟不致下垂,若脾氣不能升清,則水谷不能運化,氣血生化乏源,可出現神疲乏力,頭目眩暈、腹脹、泄瀉等癥,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清氣在下,則生飧泄”,脾氣(中氣)下陷,可見久瀉脫肛[2],甚或內臟下垂,分別類似于現代西醫學中的急慢性腸炎、腸易激綜合征及胃下垂、眼瞼下垂、子宮脫垂、脫肛等。脾的升清,是和胃的降濁相對而言的,脾胃之間是升降相因,燥濕相濟,陰陽相合,相反相成,若胃失通降,不僅可以影響食欲,而且因濁氣在上而發生口臭、脘腹脹滿或疼痛,及大便秘結等癥狀,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濁氣在上,則生脹”,若胃氣不僅失于通降,進而形成胃氣上逆,則可出現噯氣腐酸、惡心、嘔吐、呃逆等癥[3]。類似于西醫中的反流性食道炎、幽門痙攣等。
以上諸如此類消化系疾病看起來病種多而繁雜,但宋老將這一系列消化系疾病利用中醫之妙根據中醫辨證施治和整體觀念的特點,歸納總結,認為脾胃功能失調是這些疾病的其中一個致病病機,就是說醫者看到這類疾病,也許會將思維西化,認為病位不同,而診治起來無從下手,但只要認真分析,若病因病機相似,皆可異病同治[4]。
《素問·上古天真論》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這里告訴我們人類在自已的日常生活中[5],一定要科學合理的安排自己的生活、飲食、起居和工作,不可任意妄行。然而,隨著社會生活節奏加快,一部分人群重事業而輕養生,一來,飲食無節制,饑飽失常,寒溫不調,損傷脾胃,《素問·痹論》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還會導致“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為痔”(《素問·生氣通天論》)。《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九痛敘論》云:“飲食勞逸,使臟氣不平,痞隔于中,食飲遁疰,變亂腸胃,發為疼痛,屬不內外因[6]。”《靈樞·師傳》云:“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指出攝取飲食物時,應“寒溫中適”。若有因脾陽素虛,或恣食生冷,致中陽不振,升降之能呆滯出現腹痛、泄瀉、便秘等病癥,如急慢性胃炎、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等疾病,況《景岳全書·心腹痛》曰:“因寒者常居八九,因熱者十惟一二”;二來,中國人受傳統文化影響,吃飯為舌頭而吃,重在吃味道,致五味過極,辛辣無度,肥甘厚膩,飲酒如漿,致使脾胃陽氣受損,濕不得去,久之聚而生痰,發為怪病;三來,來自生活、工作及家庭的壓力增大,肝郁氣滯也極易橫逆犯胃,即“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九痛敘論》云:“若五臟內動,參以七情,則其氣痞結,聚于中脘,氣與血搏,發為疼痛,屬內所因”[7]。肝郁化火,灼傷胃陰,絡脈失養,如食道炎、萎縮性胃炎,況且現代人戶外運動減少,脾胃不壯,陽氣虧虛,運化不佳,升降失調。宋老認為脾胃本為后天之本,為氣血生化之源,卻因以上多種不良生活習慣使得氣滯濕阻、運化失職,久之脾胃虛弱,陽氣不復,胃陰失養,從而形成諸病病因,并認為脾胃陽虛、胃陰不足、肝郁氣滯為脾胃病最常見的證型。各列舉一案例如下。
1 脾胃陽虛型病例
患者,王某,男,31歲。2012年6月15日初診。
主癥:脘腹攣縮痛已有5年,喜食熱飲,口中異味,畏寒,四肢不溫,脘痛發作有似痙攣樣,泛清水,時有燒心,泛酸,便溏,舌淡苔白滑,邊有齒痕,脈沉弦。患者自訴:嗜煙酒,常夜間暴飲暴食,西醫診斷:十二指腸球部潰瘍,幽門螺桿菌(++)。治宜溫陽健脾止痛,藥用:炒白芍20 g,甘草10 g,延胡索10 g,烏梅15 g,黃連10 g,吳茱萸3 g,制附子10 g,干姜8 g,砂仁(后下)10 g,姜半夏10 g,九香蟲10 g,海螵蛸10 g,焦白術15 g,炒山藥30 g。每劑加生姜3片、大棗3枚作引,共7劑,水煎服。醫囑:飲食規律,忌食生冷油膩,清淡飲食,晚餐不宜過飽,戒煙限酒,起居有常。
患者脘痛有似痙攣樣,泛清水,畏寒,四肢不溫,便溏,舌淡苔白滑,邊有齒痕皆屬脾胃虛寒之象,用附子、干姜溫陽以助命門之火溫煦脾土,芍藥甘草湯緩急止痛,延胡索、九香蟲行氣止痛;白術、山藥鍵運脾胃;濕盛則會舌苔白滑,有齒痕用姜半夏、砂仁健脾燥濕;時有泛酸,燒心,口中異味是由于肝胃郁熱所致,用左金丸疏肝瀉火,用海螵蛸抑酸,患者嗜煙酒,夜間常暴飲暴食,幽門螺桿菌(++),也是導致脾胃積熱的原因,故用黃連、烏梅殺除幽門螺桿菌。此病陽虛為本,郁熱為標,標本同治[8]。
復診:偶有脘痛,口中異味消失,泛酸、燒心癥狀皆有所緩解,偶有便溏,舌淡苔白滑,齒痕減少,脈略沉。原方加減再服10劑,結合患者本人的飲食配合,病情基本痊愈。半月后回訪:復查幽門螺桿菌已轉陰性。
2 胃陰不足型病例
患者,陳某,女,45歲。2014年9月9日初診。
據述:胃病已經16年之久,西醫診斷:萎縮性胃炎。經多方治療不愈,聞名來診,患者形體消瘦,兩脅攻撐脹痛,煩躁易怒,胃痛隱隱,有灼熱感,嘈雜脹滿,納呆,食后脹甚,神疲乏力,無噯氣泛酸,無嘔血便血史,大便溏薄,一日3~5次,舌紅苔膩,脈濡細而數。證屬胃陰不足,養陰益胃為主。藥用:綠萼梅10 g,生山藥30 g,蓮子肉10 g,石斛15 g,生谷芽、生麥芽各30 g,炒白芍20 g,甘草6 g,藿梗10 g,佛手10 g。10劑,水煎服。并囑其忌食生冷油膩,煎炸炙煿及辛辣動火等刺激性食物,適宜清淡飲食,尤忌過度思慮憂郁,注意調養情志。
患者脾胃素虛,納化失常,久病正虛,故神疲乏力,陰虛津少,胃絡失養,則絡脈拘急,故隱隱作痛。用芍藥甘草湯緩急止痛,胃痛有灼熱感,形體消瘦,舌紅,脈細數為陰虛內熱之象,用石斛養陰益胃,脘悶嘈雜,大便溏薄,苔膩為濕濁內蘊之征,用山藥、蓮子肉健脾止瀉,兩脅撐脹,煩躁易怒,為木盛克土,肝用過亢所致,綠萼梅疏肝和胃,用谷麥芽、藿梗、佛手行氣醒脾治療納呆。
復診:10劑藥后,胃部灼熱感已失,隱痛減輕,納谷欠佳,大便一日一行,時有口干,精神見振,舌質暗滯,脈弦細數。病癥較前明顯減輕,據上方加麥冬12 g,玉竹10 g,烏梅10 g以滋養胃陰治療口干。原方加減再服20劑,諸癥未作,食欲增加,大便成形,形體見豐,一年后回訪,一直工作,再未復發。
3 肝郁氣滯型病例
患者,馬某,女性,48歲。2016年11月初診,自訴近兩年諸事不順,患有梅核氣兩年,服用中藥略有好轉,現患者胃中脹悶不適,胸脅脹痛,牽連背部,易怒,喜太息,偶有惡心,納差,大便秘結,三日一行,疲乏,舌苔膩,舌邊紅,脈弦。腹部B超顯示:肝膽胰脾雙腎無異常。治宜疏肝理氣,健脾和胃,方用自擬疏肝湯:玫瑰花10 g,厚樸10 g,紫蘇葉10 g,隔山消10 g,娑羅子10 g,香附18 g,枳殼10 g,當歸15 g,炒白芍15 g,柴胡10 g,川楝子15 g,佛手10 g,陳皮10 g,瓜蔞15 g,生麥芽15 g。10劑,水煎服。并給患者以情緒疏導,望其配合。
痞滿病位雖在于胃,但與肝、脾關系密切,脅痛病位在肝膽,與脾胃及腎相關,患者易怒,喜太息,氣郁傷肝,肝氣橫逆,克傷脾土,使氣機阻滯,胃失和降而致病,患者一派肝郁氣滯之象,故借用疏肝理氣之品以治療梅核氣、脘腹脹滿及胸脅脹痛,如:玫瑰花、隔山消、娑羅子、香附、柴胡、川楝子、生麥芽;枳殼、當歸行氣通便以降濁;佛手、陳皮、瓜蔞寬胸理氣醒脾以治療納差、便秘。肝脾調和,則氣血生化有源,疲乏自消。
10劑后,效佳,梅核氣、脘腹脹滿及胸脅脹痛明顯好轉,情緒亦好轉,食欲尚可,大便通暢,一日一行,已無惡心癥狀。再服10劑,癥狀消失,今年再見患者氣色佳,情緒良好,對宋老頗為感恩。
4 結語
李東垣在其所著《脾胃論·脾胃虛實傳變論》中說“元氣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后能滋養元氣。若胃氣之本弱,飲食自倍,則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宋老認為臨床上診治任何疾病都應十分注重“保胃氣”,才能保障五臟氣血充盈,六腑功能調和。近年來惡性疾病的發病率逐年上升,并趨于年輕化,今后要逐步改變傳統習慣,由為舌頭味道而吃轉向為健康而吃,戒煙限酒,調暢情志,適量運動,才能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