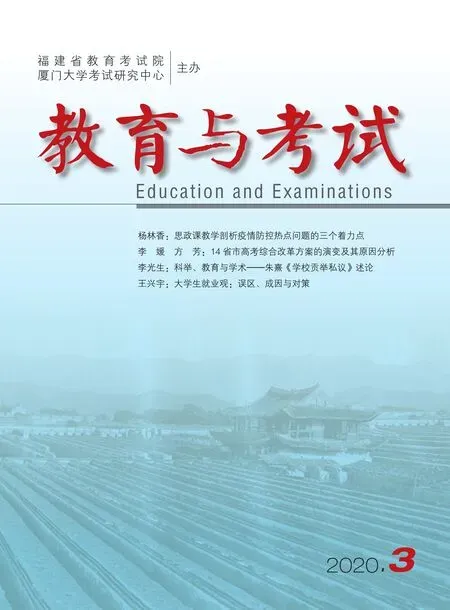科舉、教育與學術*
——朱熹《學校貢舉私議》述論
李光生
前言
《學校貢舉私議》①(以下簡稱《私議》)乃朱熹晚年未及上呈的一份關于科舉教育改革的奏議,束景南先生認為作于慶元元年(1195)。《朱子語類》載:“乙卯年,先生作《科舉私議》一通,付(王)過看。大概欲于三年前曉示,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如大義,每道只六百字,其余兩場亦各不同。后次又預前以某年科場,別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也。過欲借錄,不許。”[1]2698-2699據此,束氏考證道:“王過紹熙五年(1194)末來考亭問學,慶元元年(1195)上半年猶在考亭,故得見朱熹作《學校貢舉私議》。蓋朱熹在朝時,趙汝愚欲行三舍法,而陳傅良、葉適欲行混補,朱熹均反對,遂歸而深思熟慮作《學校貢舉私議》。”[2]《私議》被馬端臨收錄于《文獻通考》[3]之后儼成國人對待科舉態度的定調之作,在中國科舉史和教育史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然而,對于這樣一個堪稱經典的科舉教育文本,雖說歷代教育史尤其是宋代教育史著述多有涉及,但不免浮光掠影,令人遺憾②。迄今為止,學界僅李存山先生《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述評》[4]一文,對《私議》做了較為深入的文本專題研究。李氏不僅剖析了朱熹完整的教育思想,認為其中之“明體達用之學”淵源于范仲淹、胡瑗等宋代新儒學先驅,而且把《私議》與中國近代學制改革相聯系,突顯其歷史地位。見解精辟,尤具開拓之功。如果說李氏文主要著眼于從時間維度的縱向視角對《私議》進行研究,那么,本文主要從橫向視角分析《私議》寫作的真正動因及文化內涵,即朱熹在倡議科舉改革、提出“德行道藝”的教育理想外,還有著針對永嘉學術的明顯意圖,其中也有朱熹對北宋以來學術傳統在科舉場域下獲得支配性發展的質疑。
一
朱熹自幼立下學為“圣人”的宏愿,也把培養“圣人”看作教育的最終目的,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5]3873。然而,在科舉文化已然成熟的宋代社會,大多數士人讀書和受教育目的,往往直指科舉功名而忽視了教育的道德意涵。朱熹《私議》針對當時科舉制提出了尖銳批評:
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涂,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于太學。其說雖若賢于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眾。[5]3633
朱熹認為解額不均和設立太學是科舉制度的兩大弊端,“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尤其是太學,“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雋于場屋者耳。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既無所求于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茍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5]3641。朱熹認為太學作為中央官學,只是“利誘之一涂”的“聲利之場”,善為科舉之文,失去了教人“德行道藝”的本意。
朱熹認為科舉制度的弊端直接導致教育之失,因而倡議科舉教育改革,《私議》接著說道:
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涂。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5]3634
在朱熹看來,“均諸州之解額”可以保證考試的公平公正,“立德行之科”可以兼顧考試的道德意義,“分諸經、子、史、時務”等科能培養學生通經致用之才。
關于立德行科,《私議》云:
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余五十人自依常法。……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于省試后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于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于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余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余人,倍其取人分數,如余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后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于空言矣。[5]3635-3636
朱熹建議從進士科中的地方考生解額中分出四分之一,以此額度來實行德行科的選拔。縣令需要搜尋這樣的人才,每次考試時把固定人數的德行科考生送至州府。如果他們可以通過州府級的考查,知州會將他們送往禮部,然后他們會有與進士科考生類似的安排。一旦到了京城,德行科考生會享受特殊待遇。他們會被送入太學,且不用參加學校里面的月書季考。太學第二年時,考生會去政府的各個部門實習,表現出色者會在第三年獲得政府職位。剩下不能直接授官的學生則可以參加下一次省試。朱熹相信德行一旦成為科舉的關鍵因素后就更容易推廣,故德行科的創立和提倡會影響參與考試的所有人,也勢必會導致教育的全面轉型。為此,朱熹還主張任命有道德之人為學官,《私議》云:
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5]3640-3641
在朱熹看來,久任有德之人為學官,不僅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解額不均和太學虛設的問題,而且能保證德行教育得以較好的落實。
朱熹認識到天下之理不可能通過讀書而“盡通”,所謂“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于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故須在學校所設課程和教學內容上進行改革,“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即在諸科中還要分科,并分年考試。如諸經“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份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5]3637朱熹主張在經書學習上要分配比重。《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在三年一次的科舉中是必考科目,然后以每四次科舉為一個循環,其他各種經書在這個循環中依次出現。經典被分為三類:第一年和第七年的兩次科舉考《易》《書》《詩》;第四年考《周禮》《禮記》《儀禮》;第十年考《春秋》及其注解。諸子、史和時務也以類似的方法在四次科舉中考核。下一輪考試各科會涉及的書目和主題會在殿試之后馬上宣布,這樣考生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內可以專心研讀數量有限的一些書籍。
治經持守家法,還必須改革科舉考試的形式。首先要革除考官命題“附益裁剪”“穿鑿新奇”之弊。考官命題“多為新奇,以求出于舉子之所不意,于所當斷而反連之,于所當連而反斷之”,這致使考生“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闘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結果是“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其次要改革考生經義答題的形式。“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于治經,而難于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5]3640。
在朱熹看來,通過改革科舉制度、改變學校所設科目,促使士人學習儒家經典,不僅能“直論圣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解決科舉考試中道德與才能之間的矛盾,并終能“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于世,而其遺風余韻又將有以及于方來”“進于道德之歸”,而這也是朱熹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
二
事實上,《私議》所倡議的科舉教育改革措施明顯帶有針對永嘉學術的黨派傾向。眾所周知,12世紀中后期的科舉場域是永嘉學者的天下。在科舉教育場域,由永嘉學者陳傅良、葉適等人編纂的幾部策文選本如《待遇集》《進卷》最為流行,考生爭相學習。吏部尚書葉翥在1196年的一份奏章云:“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6]陳傅良、葉適等永嘉學者成為當時聞名遐邇的指導舉業的教師。為了聆聽陳傅良的舉業課程,數百名學生聚集在溫州府南門附近的茶院寺。[7]而永嘉士人在科場的卓越表現帶給他們在中央政府任職的機會,如陳傅良先后擔任多中書舍人、起居郎等職位,葉適擔任過太學正和國子司業等職位。他們常擔任科舉考官之職。日本學者岡元司發現1142年至1199年間二十次省試里面,僅有兩次考官中沒有溫州人,[8]這些都體現了永嘉學術在科舉場域的巨大影響力。《私議》的黨派傾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朱熹強烈反對混補法
《私議》云:“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眾。”[5]3633顯然,朱熹既反對三舍法,也反對混補法,兩者相較,三舍法要優于混補法。尤其是混補法與程試文字相關聯,且由永嘉學者陳傅良、葉適等人倡議。《私議》對此說道:“所以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5]3634所謂“溫、福、處、婺之人”,除“福(州)”多指浙東學者。南宋浙東學派林立,下分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等,其學術思想或有差異,然對待科舉的功利態度上卻并無二致,故科舉場域的“永嘉”往往不限于永嘉地區,而是涵蓋了整個浙東地區。朱熹反對混補法,實則是反對“永嘉”在科舉場域的影響力。
(二)朱熹對科舉中治《春秋》風氣的極端不滿
永嘉學者向來有治《春秋》的傳統,永嘉學派在科舉場域的崛起與永嘉學者專精《春秋》密切相關,如陳傅良和蔡幼學在太學以專治《春秋》知名,陳傅良有《春秋后傳》一書存世。葉味道(1220年進士)來自溫州府,他在1191年到1200年間跟隨朱熹學習。[9]葉氏告訴朱熹他計劃在下次考試時以《春秋》為專經,朱熹說道:“《春秋》為仙鄉陳蔡諸公(按:陳傅良和蔡幼學)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為尤甚,天下大抵皆為公鄉里一變矣!”[1]2761朱熹對永嘉學者因專治《春秋》而占據科舉場域優勢地位且引領一時學風深懷憂慮乃至不滿。《私議》云:
近年以來,習俗茍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仿,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5]3638
朱熹著重突出時下治《春秋》之陋習,固然體現了《春秋》在科舉場域的重要地位,卻也反映出朱熹對永嘉學術的不滿乃至敵視態度。
(三)強調道學注疏及“四書”的經典地位,排斥永嘉學者的注疏
朱熹主張治經必守家法,而要立家法,當以注疏為主。《私議》云:
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5]3638-3639
朱熹所列的這份注疏書目名單,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特別強調道學注疏的重要地位。道學人士的注疏被推崇為指導經書研讀的最優選擇。程頤被朱熹定為道學先賢,其各種注疏被列在所有經書之下,這在各家中是唯一一位。張載、楊時等其他被朱熹列入道學譜系的人物也常出現在這份名單中。第二,這份名單明顯排斥了“永嘉”諸子的注疏。“永嘉”學者特別在《春秋》和《周禮》這兩部經書的教育和注疏上享有盛譽,但朱熹對此不屑一顧。《朱子語類》載:
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按:陳傅良的字)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圣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棄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昨說與吾友,所謂專于博上求之,不反于約,乃謂此耳。是乃于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后學。”[1]2959
永嘉看文字,文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尋節目以為博。[1]2964
顯然,朱熹對“永嘉”諸子在經書尤其是《春秋》注疏教學方面的影響頗為不滿乃至憤怒,因為他認為這些人對經典的解讀方法和他希望自己學生掌握的閱讀方法背道而馳。從這份名單可見,朱熹希望限制學生對“永嘉”諸子的了解,僅列出了薛季宣的一部《尚書》注。
另一方面,為爭取道學在科舉場域的地位,朱熹選擇一套核心科目以及為每一步經書指定相應的注解。如上文所述,在科舉考試的經典科目中,《易》《書》《詩》《周禮》《禮記》《儀禮》《春秋》皆依次循環出現,只有《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在每次科舉中必定會出現。這套《四書》首先由朱熹在1182年結集出版,成了正在定型中的道學經典的核心內容。這套書的第一部《大學》在12世紀中葉就已經成為道學運動的基礎入門作品。朱熹一直認為《大學》一書包含了道學總綱,向學生介紹了修身步驟,即把個人、家國都整合進宇宙道德秩序之內。一旦學生理解了《大學》的中心思想,他們就可以在閱讀清單上別的經典時應用這種思想。對朱熹而言,《四書》為辨別其他一切作品提供了標準。除了選編經典文本和強調其在閱讀時的重要性,朱熹也對經典進行注疏。在《私議》倡議的教學內容中,其為《四書》所作注疏被列為理解核心經典的唯一選擇。
(四)對時文的批評
南宋以來,科舉時文(論體文)漸趨程式化、標準化。四庫館臣云:“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自出。未賞屑屑于頭項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來講求漸密程式漸嚴。試官執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雙關三扇之說興,而場屋之作遂別有軌度。雖有縱橫奇偉之才,亦不得而越。其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式實后來八比之濫觴。亦足以見制舉之文源流所自出焉。”[10]“頭項心腹腰尾之式”指的是12世紀后半葉程式化文章的段落名字。論體文包含六個順序固定的段落,前三個相對較短。作者首先在破題中簡明介紹主要論點。在此之后,用同樣長度或者稍長點的文字列出幾個分論點(“接題”或“承題”)。作者也可以選擇在論體文的序論部分放入一段更詳細的摘要,稱之為“小講”。以上這一段必備的文字包含了“破題”“承題”及“小講”,構成了論體文的導言(“冒子”)。文章主干“講題”之前通常有一個“原題”,確定題目在原引書中的出處,它也代表導言的結束和主體部分的開始。在立論中,對偶成為最主要的修辭手法。這樣的標準也同樣適用于經義考試。考官支持這樣程式化、標準化的模式,因為這有利于提高閱卷效率;大多數考生也都遵循這種模式。占據12世紀中后期科舉場域優勢地位的永嘉學者對此自然也提倡有加。
朱熹注意到這種標準化考試文體結構對教學有負面影響,認為堅持某種特定格式會影響學生對文本的解讀。現有的傳統因此產生了一種特定的閱讀方法。《私議》云:
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5]3640
朱熹認為這種考試形式完全基于修辭考量,因而主張改變考試形式、改變評估標準。《私議》接著說道:
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5]3640
朱熹提議的經義文章形式包括三部分:先指出所引文章之上下文,再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注疏傳統進行討論,最后學生討論自己對該段文字的理解。在朱熹看來,注疏在古典教育中的角色盡管關鍵,但還是次要的,原始文本才最為重要。學生使用注疏的方法反映了注疏的輔助性質,而注疏需要被批判性閱讀。朱熹把對文本的個人理解定義為“直論圣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這種對文本的個人理解,既不是提倡對原文進行批判性解讀,也不是鼓勵提出新穎的觀點。閱讀經書的目的是親身經歷且認同這些作品的意涵。而這些皆與永嘉學者的教學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
尤其是,朱熹對永嘉學者視作文修辭技巧為教學的中心地位甚為不滿。在他看來,永嘉學者著迷于對科舉文章進行修辭分析,這給歷史和經學研究帶來嚴重問題:
問:“今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它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1]2700
朱熹對時文的批評不僅涉及時文結構的標準化問題,更涉及古文尤其是蘇軾的文化遺產在士人文化中的權威地位。這一權威地位的形成在朱熹看來完全拜永嘉學者所賜。在朱熹眼中,永嘉學派的中堅人物陳傅良跟蘇軾是同類人:“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著。如東坡子由見得個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卻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1]2960朱熹認為古文教學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問題,更是對道學的一種思想挑戰。古文在科舉場域中取得極高名氣,一個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呂祖謙的教學活動。呂祖謙通過編纂古文選本及評點,對古文風格的議論范文進行結構和修辭分析,教導學生如何寫作時文,所謂時文“以古文為法”。如其《古文關鍵》收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蘇洵、蘇轍、曾鞏和張耒八家之文,教學生“看”文字,分析整篇文章在語義和風格上的組織方法。《總論看文字法》云: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處。蘇文當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厭人,蓋近世多讀故也。[11]
呂祖謙認為韓、柳、歐、蘇等古文經典作家作品代表了古文范式,指出文章須注重體式、用意和下句(即行文),并從“大概、主張”“文勢、規模”“綱目、關鍵”“警策、句法”四個方面說明“看文字法”。客觀上,呂祖謙的選文及教學活動有助于12世紀晚期和13世紀古文經典的形成。但朱熹對呂氏分析古文時所用的技術性和修辭方法提出了嚴厲批評: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曰:“陸教授謂伯恭有個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個腔子做,文字氣脈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1]3321
呂祖謙寫作各種文體文章所用的“腔子”來自他對古文尤其是韓、柳、歐、蘇作品的研讀。他以注釋和解讀來教導學生如何掌握古文名家作品的組織結構和修辭技法。朱熹認為時文結構的標準化以及12世紀晚期古文的權威地位都是士人重視修辭技巧的主要原因,是對道學及其教育的嚴重威脅。這其中,永嘉學者難辭其咎。
三
宋廷治國以儒家教化為本,表現得最徹底的就是對教育的重視實施及對科舉考試的整頓。宋人清楚地認為,科舉制之能實行,主要靠它的公正性。夏竦的說法頗具代表性:
伏以隋設進士之科,唐代特隆,其歲選登榜帖不過三十,賢俊之器、將相之具在其中,諒不虛語。然主司慎選,弊于回撓。豪右角逐之衢、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直而有愧,私權貴則道枉而無咎。[12]
就夏竦而言,唐代科舉制度在實行時,不免常有私于權貴的現象,但由于它能給寒畯之士提供社會升遷的機會,因而應將它視為可以彌補社會之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一種制度。夏竦的這一信念和宋人關于考試的看法基本一致。宋人相信科舉考試的基本功能是選官,但儒家學說的最高信念是要以德行表現作為選舉的唯一標準。一般說來,宋人大都相信科舉制度必須兼顧選舉的道德意義,但他們中不少人認為如此制度對實現選舉的道德理想無能為力。在南宋,關于考試的道德目標以及教育如何同考試相關聯的看法,通常傾向于認為只有教育才有希望為政府培養德行卓然的行政官員,而科舉制度不可能真正實行以德行取士的理想,大多數人也放棄了那種考試能衡量一個考生道德水平和學術成就的簡單信仰。葉夢得曾說道:“讀書而不應舉而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敘進,茍不違道與義皆不可。”[13]
朱熹提倡孔子的“為己之學”,明確批評科舉取士,對科舉制度的真正本質提出了質疑,并考察了它所存在的問題根源。《私議》為此提出改革,通過“均諸州之解額”的公平公正“以定其志”,同時立德行科以突顯科舉考試的道德意涵,以此達成教育理想。《私議》概括了當時科舉制真正的和重要的基本問題,準確揭示了宋代士大夫在面對所謂“公正”考試問題上所遇到的主要困惑:保證了考試的公正性,就必須付出放棄以德行取士的儒家理想的代價。朱熹心里應該很明白,科舉場域以德行取士只是一種美好而無法實現的愿景。朱熹自己也承認,上文提出的科舉改革措施只是“如曰未暇”的下下之策,真正要達成所愿,“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明道先生熙寧之議”,即程頤《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在朱熹看來,取士的公正性兼德行考察的實現只有在學校教育下才有可能達成。
借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科舉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結構,政府、考官以及各樣讀書人都是主觀上形塑這個科舉場域的參與者。李弘祺先生認為,科舉制是影響中國思想及文化最大的力量,宋代以后中國學術史很難說不是政府、考官與士人在科舉場域爭取主導權的發展史。[14]189-190換言之,科舉是創立、傳播和改變學術思想的重要場域。面對永嘉學術在12世紀中后期在科舉場域咄咄逼人的聲音,朱熹自然希望道學思想在科舉場域能占有一席之地,《私議》極力倡議立德行科、確立《四書》及其注疏的經典地位、強調科舉考試的道德意義,無疑是意欲其道學思想在科舉場域獲得發展的一次努力嘗試。然而,北宋經學在科舉場域的發展史表明,光是在科舉場域里圖謀發展一家學術是相當困難的。正如李弘祺先生所云:“科舉考試在促成學風變革上,可能在王安石變法之后,變得不是那么明顯。而同時,在科場上面相對缺乏影響力的北宋五子的道學思想只能通過其他途徑發展他們的空間。”[14]198《私議》既然稱為“私議”,表明它實際上只是朱熹與朋友之間的私下討論與流傳,在當時士人文化中并不算流行,然而,他將死時,其學術思想已經廣為傳播,這表明當時流傳的科舉時文并不能真的對學術產生完全支配性的作用。因而,學術思想的發展除了科舉場域,應該還有另外一個場域——教育場域,《私議》標題事實上對此已有明確暗示。也就是說,對朱熹而言,無論是對于“德行道藝”“進于道德之歸”教育理想的達成,還是道學思想的發展,學校教育場域可能比科舉場域更值得信賴。
注釋:
①本文所引《學校貢舉私議》俱出自《朱熹集》(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版)。
②較為著名的宋代教育史(包括書院史)著述如袁征《宋代教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版);李兵《書院與科舉關系研究》(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及苗春德、趙國權《南宋教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皆有涉及,然多作征引文獻之用,并未對文本本身的意涵有所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