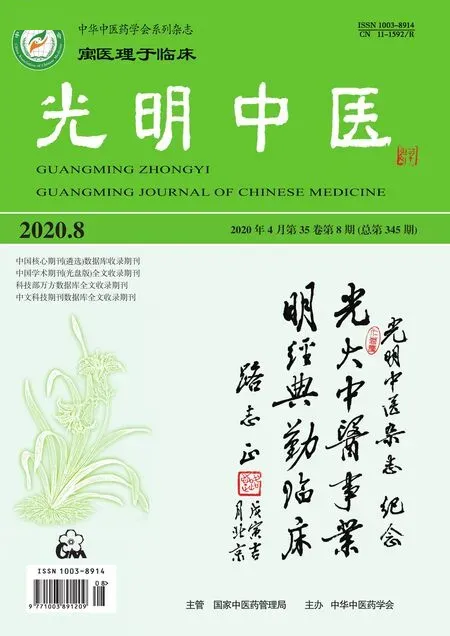從腎論治黃褐斑的思路沿革及驗案舉隅
靳曰軍 張冬云 余 華
面部的黃褐色色素沉著稱為黃褐斑,多對稱分布于面頰部,形如蝴蝶亦稱蝴蝶斑,中醫稱之為“黧黑斑”[1]。其特點是對稱分布,無自覺癥狀,日曬后加重。常發生于孕婦或中年婦女。隨著激光醫學的快速發展,太田痣等其他色素性疾病正被逐漸攻克,但西醫治療黃褐斑仍困難重重,而中醫學治療該病卻有著明顯的療效。良好效果的前提是對整體觀與辨證論治的準確把握,尤其是辨證。在諸多證型中從腎論治黃褐斑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本文通過梳理古籍中從腎論治黃褐斑的辨證思路沿革并歸納分析,總結出該思路的發展規律并應用于臨床,以期為提高中醫治療黃褐斑的臨床療效提供一定幫助。
1 理論基礎
從腎論治黃褐斑源于《黃帝內經》中黑色屬腎的理論。
黃褐斑古人稱之為黧黑斑,黧在《玉篇》中的解釋為“黑也”,《廣韻》解釋為“黑而黃也”,都與黑有關。《黃帝內經》中黑色對應的臟腑是腎,《素問·五藏生成》中論及“色味當五臟……黑當腎、咸”,《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記載“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其在天為寒……在色為黑。”黃褐斑的顏色從淡褐色到黑褐色均有,相對于白皙的面部底色,該病的顏色很多時候被描述成“黑”色。因此,《黃帝內經》中黑色屬腎的理論為后世從腎論治黃褐斑提供了理論依據。
2 沿革過程
2.1 萌芽階段 從腎論治黃褐斑萌芽于唐朝。隋朝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將黃褐斑作為獨立疾病較早地提了出來,當時稱為“面黑皯”,但他認為病因是痰飲或風邪所致的氣血不調,未涉及腎的問題[2]。到了唐朝,藥王孫思邈雖未專病專論,但其《千金翼方》論及“黑色見顴上者,腎有病”[3],首次明確將顴部黑色的疾病責之于腎。在內服藥治療上,《備急千金要方》跟《千金翼方》散在著許多治療面色黧黑的方劑,雖未明確提出是腎虛所致,但以方測證可推大部分方劑溫補腎陽,或陰陽雙補,其中以太一白丸和干地黃丸最為后世所推崇。太一白丸出自《千金翼方》,“主八痞,兩脅積聚……面目黧黑”,其中附子、烏頭、肉桂的大溫之品就占總共五味藥中的三味。干地黃丸出自《備急千金要方》,“治五勞七傷六極……顏色黧黯……進食資顏色長陽”[4],原著中此方僅列功效與藥物組成,未賦予方名,取排列在首的干地黃為名是后世所加,組成中天雄、肉桂、蛇床子、杜仲、肉蓯蓉等溫腎陽之品印證了原文中“滋顏色長陽”的用意。
2.2 形成階段 從腎論治黃褐斑的思路形成于北宋,以腎陽虛為主。北宋時《圣濟總錄》首次明確提出了“腎藏虛冷”“腎勞虛寒”或“腎臟虛損,陽氣痿弱”等腎陽虛可以導致面色黧黑的觀點,又有“女人子臟久冷,頭鬢疏薄,面生皯黑曾”的記載,子臟屬腎,也支持腎陽虛可導致黃褐斑。書中記載了許多補腎陽治療面色黧黑的方劑,如葫蘆巴丸“治腎藏虛冷……面色黧黑”,菟絲子丸“治腎臟虛損,陽氣痿弱……面色黧黑”,八味丸方“治腎臟虛損,陽氣痿弱……面色黧黑”[5]。南宋的治療思路基本未變,《三因極一病證方論》用安腎丸“治腎虛腰痛,陽事不舉……面色黧黑,耳葉焦枯”[6]。《楊氏家藏方》記載賜方膃肭臍丸可以補虛壯氣溫暖下元,“治……面色黧黑”,賜方鹿茸丸“治真元虛憊……面色黧黑”,鹿角膠丸“治下元冷憊……面色黧黑”[7],都是以溫腎陽為主的方藥來治療面色黧黑。
2.3 發展階段 明朝仍以溫腎陽為主,明朝末期開始出現滋腎陰的新思路。此時期的診斷學專著《診家正眼》肯定并發展了《千金翼方》中腎病顴黑的觀點,論述到“顴與顏黃黑者,腎病”[8],此處“顴與顏黃黑”用來描述黃褐斑較之前更加的準確。明朝前期從腎論治黃褐斑仍以溫腎陽為主,《外科理例》在談及八味丸治驗時講到“面白,或黧黑,以上諸癥皆屬腎。非用附子不可”[9]。《證治準繩》也支持腎陽虛致黃褐斑的觀點,在治療產后發熱時論及“面色黧黑,兩尺浮大,按之微細,此因命門火虛……用八味丸補土之母而痊”。明朝末年,中醫外科正宗派的開山之作《外科正宗》首次提出了腎陰虛的觀點,書中將黃褐斑稱為“黧黑斑”,病因為“水虧不能制火,血弱不能華肉,以致火燥結成斑黑”,治療上“朝服腎氣丸以滋化源”,看似方證不符,實則相符。該書所提的腎氣丸,并非含附子、肉桂的桂附地黃丸,從組成看就是六味地黃丸,又有《外科正宗·雜瘡毒門腦漏》“六味地黃丸(藥見肺癰門腎氣丸)”為證。由此說明黃褐斑的辨證產生了腎陰虛水虧火燥的新思路。清朝及以后腎陰虛成為主流。清朝的正宗派《外科大成》及《外科心法要訣》沿用了腎陰虛的觀點。之后何夢瑤在《醫碥》中更是明確寫到“面上黧黑斑,水虛也,女人最多,六味丸”[10]。此觀點影響至今。七年制大學教材《中醫外科學》便將黃褐斑分為了肝郁氣滯、肝腎不足、脾虛濕蘊及氣滯血瘀四個證型[11],五年制教材也大體一致,其中肝腎不足選擇的方藥亦是六味地黃丸。
3 驗案舉隅
如今中醫治療黃褐斑,分型十分豐富,但不外乎臟腑辨證辨肝、脾、腎,氣血辨證辨氣滯或血瘀,從腎論治是一非常重要的內容。從古籍記載、當代文獻[12-14]及臨床觀察中發現,黃褐斑確實存在腎陽虛的證型。現舉一筆者臨床驗案。
患者,女性,45歲,顴部褐色斑片近10年,對稱分布,緩慢增大,面無光澤,無癢痛。冬季四肢冰冷,夏季從不開空調風扇,小便頻數,清長,夜尿多,月經量少,舌淡胖苔白,脈沉遲。西醫診斷:黃褐斑,中醫診斷:黧黑斑,腎陽虛證。處方:黑附片(先煎)12 g,肉桂9 g,熟地黃24 g,山藥12 g,山萸肉12 g,茯苓9 g,澤瀉9 g,牡丹皮9 g,水煎服,每日1劑。半月后黃褐斑雖無明顯變化,但面色漸有光澤,畏寒肢冷有改善,繼續服藥半月,面部褐色斑片開始顏色略變淺,整體面色進一步改善,皮損與周邊對比減弱。由于煎煮中藥不方便,改為口服桂附地黃丸,4個月后黃褐斑顏色明顯變淡,面積減少近一半,后間斷服藥近一年后停藥,面部褐色斑片基本全消,畏寒怕冷、小便頻數、清長、夜尿多等癥狀均得到明顯改善。
4 討論
腎為水火之臟,藏真陰而寓真陽,為先天之本,陰平陽秘,功能才能正常。從腎論治黃褐斑的辨證思路,源自于《黃帝內經》關于黑色屬腎的理論,于是古人將面部黑色或黃而黑的疾病歸于腎。開始用補腎的藥物治療面部黧黑萌發于唐朝,但只有何藥治何癥,沒有明確指明腎虛,北宋《圣濟總錄》首次明確了腎虛可致黃褐斑,且病機及處方用藥多以腎陽虛為主,這一觀點一直影響到明朝。明朝末年《外科正宗》首先提出了“水虧不能制火”的腎陰虛觀點,對清朝乃至當今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以上討論及臨床應用提示我們,尤其是剛學完教材便入臨床的年輕醫師,認真學好教材的同時不應拘泥于教材,遇到書上沒有的證型更需四診合參,整體把握,準確辨證,只有這樣才能發揮中醫的療效優勢,更好地服務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