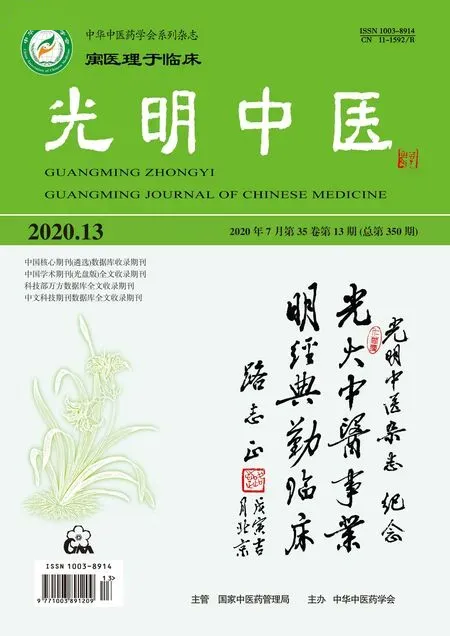溫膽湯治療抑郁性失眠芻議
魏稚力 張小波 沈 濤
當前由抑郁癥所帶來的健康與社會問題愈加突顯,這引起了醫學與社會多方面的關注與研究。抑郁癥是指以顯著而持久的情緒低落、活動能力減退、思維與認知功能遲緩為主要特征的一類心境障礙[1]。抑郁癥常以失眠為主癥,而失眠又進一步加重抑郁癥患者的身心負擔。據報道,約90%抑郁癥患者存在失眠癥狀,5%~30%失眠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礙,如抑郁與焦慮[2]。因此,如何有效治療抑郁性失眠,探析其病機與治法,對于深入認識抑郁癥以及提高其臨床診療效果具有積極意義。
1 抑郁性失眠的中醫病機
中醫典籍里并無抑郁性失眠的記載,根據本病的臨床表現可將其歸于“郁證”和“不寐”范疇。《醫碥·郁》云:“郁則不舒則皆肝木之病矣。”抑郁性失眠既有“郁”的一面,又兼具邪擾心神之“不寐”一面,其病機核心可概括為肝郁膽虛,心神不寧。在此基礎上,若痰濁內生,凌心擾神,則加重不寐。
1.1 肝氣郁結,膽腑虛怯,發為不寐《證治匯補·郁證》指出:“郁病雖多,皆因氣不周流”,《素問·舉痛論》也有“百病皆生于氣”的說法,二者皆表明抑郁癥以“郁”為病機關鍵所在。與之相關的臟腑中,“郁”與肝的關系最為密切。肝主疏泄,司情志。全身氣血的和調,情志的暢達有賴于肝的正常生理功能。肝又為剛臟,喜調達,惡抑郁。肝之疏泄功能正常,則人體氣血平和,氣機調暢,既不亢奮,也不抑郁,各臟腑間相互協調,各司其職,故精神愉悅,心情舒暢,思維靈敏。一旦情志失調,肝氣郁結,司疏泄功能失職,則見心情抑郁寡歡,悲傷憂愁而多疑慮。肝藏血,血舍魂。魂以血為依附,藏于肝中。若肝郁不疏,氣血失和,則魂失潛斂,神不潛藏,浮動于外,陰陽失交而見不寐[3]。正如《醫鈔類編》所言:“肝不藏魂,故不寐,血不歸肝,臥亦不安”。除肝外,膽也是調節情志的重要臟腑。《素問·靈蘭秘典論》云:“膽者,中正之官, 決斷出焉”。膽在精神意識思維活動過程中具有判斷事物、作出決定的作用。膽虛則決斷無權,遇事善驚,亦或優柔寡斷,心無所倚,神無所歸,發為不寐。誠如《太平圣惠方》中所言:“膽虛則多恐……膽氣衰微,故令神思恐怯而多驚悸也。”《類經·藏象類》云:“足少陽為半表半里之經……所以能通達陰陽,而十一臟皆取決乎此也。”少陽膽之樞機不利,則衛氣無以由陽入陰,陰陽不交,繼而不寐。肝與膽互為表里,屬木,共司疏泄,同主勇怯。“肝之余氣,泄于膽,聚而成精”。膽腑已虛,若肝氣郁結,不能流注于膽,膽氣愈加虛怯,不能決斷,表現出精神抑郁、情緒低落,意志活動減退。如此肝膽不濟,則進一步加重氣機郁結。
1.2 肝郁膽虛,痰濁內生,凌心擾神,加重不寐《醫宗金鑒》云:“心靜則藏神,若七情所傷,則心不得靜,而神躁不寧也。”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七情內傷總關乎心,心神無主則發不寐。肝屬木,心屬火,二者互為母子關系,病理上相互傳變,肝氣郁結,則氣滯痰阻,上擾心神。《靈樞·本藏》云:“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膽虛不旺則脾胃失其健運,痰飲內生,而“膽氣通于心”,痰濁凌心擾神則不寐,恰如《證治要訣》“有痰在膽經,神不守舍,亦令不寐”之謂[4]。
2 溫膽湯治療抑郁性失眠剖析
2.1 溫膽湯源流概述溫膽湯最早出自姚僧垣所著之《集驗方》,轉載收錄于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和王燾的《外臺秘要》中。其方由生姜四兩、半夏二兩、橘皮三兩、竹茹二兩、枳實二兩、甘草一兩組成,治療大病后因膽寒引起之虛煩不得眠[5]。后世醫家陳無擇在原方基礎上減生姜為五片、加白茯苓一兩半、棗一個,并在其《三因極一病證方論·驚悸證治》中述溫膽湯“治心膽虛怯,觸事易驚,或夢寐不祥,或異象惑,遂致心驚膽懾,氣郁生涎,涎與氣搏,變生諸證,或短氣悸乏,或復自汗,四肢浮腫,飲食無味,心虛煩悶,坐臥不安。”不難發現,從《集驗方》至《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溫膽湯所治病證的論述得到了擴大,又最與心膽相關,并強調了對于氣郁、痰涎等因素以及不寐等病證的治療作用。
2.2 肝郁膽虛,痰濁凌心,以溫膽湯治之溫膽湯解郁溫膽,理氣化痰,調節肝膽疏泄,針對抑郁性失眠肝郁膽虛,痰濁凌心之病機。肝為風木之臟,體陰用陽,肝郁則氣阻,氣阻而痰生。“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故以枳實、陳皮理氣開郁,使氣行木達,氣順痰消。膽屬少陽春木,以溫為常候,膽虛則寒,故以陳皮、半夏、生姜之辛溫燥濕化痰,使膽恢復溫和之性[6]。徐靈胎《蘭臺軌范》明確指出:“生姜一味足散膽經之寒。”肝郁日久,易于化火,而少陽為少血少氣之腑,膽虛勢必經氣不利,變生浮火,故用竹茹解郁除煩,兼清浮火,同時“竹茹甘而微寒,又與膽喜溫和相宜”(《本草思辨錄》)。茯苓功善健脾滲濕,寧心安神,《神農本草經》列之為上品,《藥性論》謂其“開胃,止嘔逆,善安心神”。故佐入方中增加寧心安神之功,同時又可加強健脾化痰的作用。
2.3 臨證多變,病情復雜,以溫膽湯加減化裁疾病的發展是一個漸進且復雜的過程,隨著病情的變化,證候可發生轉變,病機也會更加復雜。抑郁性失眠的病機往往從郁的階段開始演變,郁則可致氣、痰、火、瘀的塞滯。溫膽湯著重化痰利膽,開郁理氣,針對抑郁性失眠的中前期甚為適用。隨著病機證候的轉變,則需進行臨證加減化裁。
2.3.1 肝郁膽虛,傷及脾胃脾胃同居中焦,秉土氣而生,肝氣郁結易橫逆犯胃。而“邪在膽,逆在胃”,肝郁膽虛,中焦氣機升降失常。脾不得升,胃不得降,則可引起患者惡心、腹脹、食欲減退等,雖溫膽湯中有枳實、陳皮之品,但和胃之功稍顯不足,可予佛手、青皮、建曲等藥加減;肝氣郁滯,克于脾土,脾虛濕盛,若失運化之職,則可表現為氣血生化的匱乏以及痰濁內停兩方面:若側重于氣血,患者出現心悸健忘、神疲乏力、面色微黃等表現,則可以溫膽湯合歸脾湯加減;如側重于痰濕,則可加厚樸、蒼術、薏苡仁、白豆蔻等化濕運脾。
2.3.2 肝郁化火,痰火擾心肝為剛臟,體陰而用陽,肝郁日久,易化火傷陰,此時可加入柴胡、香附、郁金、薄荷等增強疏肝解郁的作用,然此類疏肝行氣藥又需兼顧其辛燥之性,以防肝陰耗傷,可酌情加入白芍等柔肝之品;肝郁不達,氣郁津停成痰,肝郁化火灼津,痰火相攜,擾及心神,患者除情緒低落,郁郁不歡,可兼見脅肋脹痛、口苦、口干、腹脹便秘、小便黃、舌紅苔黃膩、脈滑等。此時當在溫膽湯基礎上加解郁瀉火之品。如黃連,用其苦寒燥濕之性,共入心、脾、胃、肝、膽經,以清心化痰,燥濕瀉火;痰飲為濁物,而心神性清凈,痰熱漸進,變生痰火,隨氣上逆蒙蔽心神,患者多現多夢、噩夢等癥狀,此類癥狀可酌情加入膽南星、石菖蒲、遠志等,以增強清熱化痰,清心利竅之功。
2.3.3 久病入絡,耗傷陰血久病入絡,久病兼瘀,頑疾多瘀血。抑郁性失眠是一種慢性、難治性疾病,在整個病變進展過程中,郁的狀態若持續加重,可由氣郁發展為痰郁、濕郁、火郁、血郁等證候,病變中后期則容易出現瘀血證候。氣為血帥,血為氣母,肝氣郁結,氣結日久與血壅阻而成瘀,演變為虛實夾雜的病機。“郁”“虛”“瘀”交錯共存,共擾心神,加重不寐,此時可用溫膽湯合血府逐瘀湯化裁。患者如陰血耗傷較重,可在二方基礎上加酸棗仁、熟地黃等藥以滋養肝血。
3 驗案舉隅
張某,女,58歲。2019年6月26日初診。患者以“反復失眠3年+”就診。近3年來反復出現入睡困難,睡后易醒,服用艾司唑侖1年余,曾診斷為抑郁癥,并長期服用抗抑郁藥物。平素郁郁不樂,時感手腳心發熱,訴既往月經多夾有血塊,舌質暗紅苔黃厚,脈弦滑。診斷為抑郁性失眠,辨為肝郁膽虛,痰濁凌心證,予溫膽湯加減化裁。藥用如下:麩炒枳實15 g,陳皮10 g,法半夏15 g,竹茹20 g,茯苓20 g,炙甘草10 g,梔子15 g,黃連10 g,膽南星15 g,木通15 g,滑石20 g,白豆蔻10 g,澤瀉15 g,南沙參20 g,瓜蔞皮15 g。4劑,水煎服,1日半1劑。二診時患者訴服藥后失眠癥狀較前有所改善,入睡時間比以往縮短,但仍眠淺易醒,醒后難寐,緊張、害怕,苔微黃,但較前已變薄。在一診方基礎上加減,膽南星改為10 g,加石菖蒲15 g,制遠志15 g,首烏藤20 g。三診時患者訴上方服后易入睡,在服中藥的同時將艾司唑侖劑量減半。其苔白微厚,故在二診方基礎上去梔子、黃連,繼服3劑后,以逍遙丸鞏固2個月,并囑患者平時保持良好情緒,后訴睡眠已能達5~7 h每晚。
按:患者失眠已多年,本有抑郁癥病史,平素憂思不悅,肝氣郁結,久則氣阻津停,痰濁內生,氣郁而見手腳發熱。肝郁膽虛,共失疏泄之職,痰濁凌心擾神,加重不寐,痰濁郁久化熱,患者故見苔黃厚,脈弦滑等。以溫膽湯解郁溫膽,理氣化痰,開氣、痰之郁,加入黃連、梔子、膽南星等清化熱痰,兼解郁熱。二診時考慮患者病程較久,痰熱隨氣上逆蒙蔽心神,故加石菖蒲、遠志清心開竅。三診時,苔已不黃,故去方中寒涼之品,以“暢中”“滲下”等藥繼續鞏固。
4 小結
抑郁性失眠最與心、肝、膽相關,并常受痰濁凌擾。對于肝郁膽虛、痰濁凌心證之抑郁性失眠,于溫膽湯基礎上加減多能獲得良好療效。對于抑郁性失眠患者的診療,應結合患者身心情況。一方面,需兼顧不同臟腑,根據氣、血、痰、火“郁”的不同程度,合理配伍藥物以改善失眠癥狀;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視心理治療對于此類患者的重要性,應多從醫生角度給予患者更多的聆聽與鼓勵,幫助患者走出抑郁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