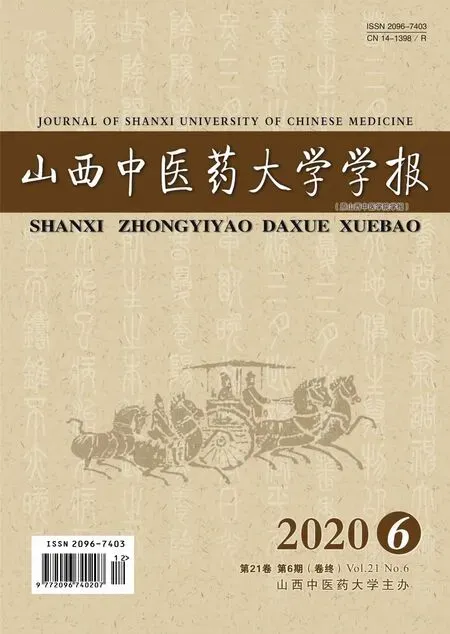基于能量代謝物質探討胃潰瘍大鼠足三里穴的敏化反應
朱小香,薩喆燕,萬 隆,周麗莉,葉笑然,楊廣印,林靜瑜,許金森
(福建省中醫藥科學院 福建省經絡感傳重點實驗室,福建福州350003)
足三里穴是胃之下合穴、胃經之合穴,為治療胃病的首選穴,《四總穴歌》“肚腹三里留”則是對其主治作用的經典概括。足三里與胃是經穴-臟腑相關理論的代表之一,然而,課題組在以往的研究中,通過觀察伊文思藍(evans blue,EB)滲出的方式確定胃潰瘍大鼠的體表敏化穴位,發現EB滲出點多出現在督脈背段及膀胱經第一側線,足三里穴未發現EB滲出點[1]。這與程斌等[2-3]的研究基本一致。但是足三里與胃疾病的相關性是勿庸置疑的,這不僅在古代經典文獻中有不少記載,在現代臨床中也普通應用。漆學智等[4-5]臨床研究也發現,足三里在胃腸道疾病中出現穴位壓痛敏化現象。那么,胃潰瘍時,足三里穴是否發生了敏化?是否以其他方式來表現其敏化?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及其代謝產物二磷酸腺苷(adenosine diphosphate,ADP)、一磷酸腺苷(adenosine monophosphate,AMP)是體內物質代謝和能量代謝的重要中間產物。研究表明,ATP等腺苷酸類物質參與針灸對多種疾病的良性調節作用[6]。因此,本研究以ATP、ADP和AMP為觀察指標,探討胃潰瘍大鼠胃組織和足三里穴區組織的能量代謝情況,為探討穴位敏化的表現形式和物質基礎提供實驗基礎。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材料
1.1.1 實驗動物 健康SD大鼠32只,雄性,清潔級,體質量(250±25)g,購自福建醫科大學實驗動物中心,許可證號:SCXK(閩)2012-0001。購入后于福建省中醫藥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清潔級實驗室中適應性喂養1周(恒溫、12 h光照/d)。實驗動物條件符合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頒布的《實驗動物管理條例》要求。本實驗過程中對動物的處置符合2006年科技部發布的《關于善待實驗動物的指導性意見》要求。
1.1.2 儀器和試劑 寵物剃毛器(廣州科德士電子公司);全波長掃描式多功能酶標儀(美國Thermo公司);吲哚美辛(上海羅恩試劑公司);BCA蛋白濃度測定試劑盒(江蘇凱基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ATP、ADP和AMP ELISA試劑盒(均購自上海酶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實驗方法
1.2.1 分組與造模 32只大鼠隨機分為正常對照組(正常組)和胃潰瘍模型組(模型組),每組16只。胃潰瘍大鼠模型制備采用吲哚美辛腹腔注射法。即大鼠禁食不禁水15 h,按15 mg/kg劑量腹腔注射吲哚美辛(4 mg/mL,溶于5%NaHCO2溶液中),6 h后制成大鼠胃潰瘍模型。模型成功的標準:大鼠安靜,萎靡不振,拉柏油樣便;形態學上可見胃黏膜有出血點和潰瘍灶。
1.2.2 胃潰瘍指數觀察 每組各取6只大鼠用于胃潰瘍指數(UI)計算。10%水合氯醛麻醉大鼠后剖腹取胃,將幽門部和賁門部用線結扎,向胃內注入4%多聚甲醛2 mL,在兩結扎線外摘下全胃,置于4%多聚甲醛中固定30 min。然后沿胃大彎剪開并用水清洗胃內容物,參照GUTH′S法計算UI:全胃各病灶長度之和為損傷指數。損傷≤1 mm(包括糜爛點)為1分,1 mm<損傷≤2 mm為2分,2 mm<損傷≤3 mm為3分,3 mm<損傷≤4 mm為4分,依此類推。損傷寬度>2 mm者UI加倍。
1.2.3 取材 在腹腔注射吲哚美辛造模后的第7天,10%水合氯醛麻醉大鼠后用寵物剃毛器剃掉大鼠足三里穴毛發,取足三里穴皮膚及皮下肌肉組織0.5 cm×0.5 cm×0.5 cm,然后剖腹取胃組織(胃竇和胃體部),置于EP管中,保存于-80℃冰箱待測。
1.2.4 ATP、ADP和AMP濃度及能量負荷(EC)的測定
1.2.4.1 總蛋白濃度的測定 對各標本勻漿后離心取上清液,采用雙辛丁酸法(bicinchoninic acid,BCA)法進行總蛋白濃度的測定,按BCA蛋白濃度測定試劑盒使用說明書進行測定。
1.2.4.2 ATP、ADP和AMP的測定 分別按大鼠ATP、ADP和AMPELISA試劑盒的使用說明書進行測定。
1.2.4.3 ATP、ADP和AMP的最終濃度(單位為μmol/μg)計算 ATP、ADP和AMP的檢測濃度/BCA總蛋白濃度。
1.2.4.4 EC計算 EC=(ATP+0.5×ADP)/(ATP+ADP+AMP)。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兩組大鼠UI的比較
正常組3只大鼠胃黏膜結構完整,未見潰瘍,3只大鼠胃組織可見幾個點狀小潰瘍;模型組大鼠胃組織潰瘍明顯,多呈線狀。模型組大鼠胃黏膜UI值較正常組明顯升高(P<0.0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大鼠胃潰瘍模型復制成功。正常組大鼠出現潰瘍可能與實驗環境應激有關,體現了設定正常組的意義。結果見表1。
表1兩組大鼠胃潰瘍指數比較 (±s)

表1兩組大鼠胃潰瘍指數比較 (±s)
注:與正常組比較,1)P<0.01
組別 n UI正常組 6 1.33±1.75模型組 6 58.33±34.741)t值 -4.014 P值 0.002
2.2 兩組大鼠胃組織能量代謝物質含量及能量負荷的比較
與正常組比較,胃潰瘍模型組大鼠胃組織ATP、ADP含量顯著降低(P<0.001,P<0.05),AMP含量顯著升高(P<0.001),能量負荷顯著降低(P<0.001)。結果見表2。
表2 兩組大鼠胃組織能量代謝物質及能量負荷比較 (±s)

表2 兩組大鼠胃組織能量代謝物質及能量負荷比較 (±s)
注:與正常組比較,1)P<0.05,2)P<0.001
?
2.3 兩組大鼠足三里穴區組織能量代謝物質含量及能量負荷的比較
與正常組比較,胃潰瘍模型組大鼠足三里穴區組織ATP、ADP含量顯著降低(P<0.001,P<0.01),AMP含量顯著升高(P<0.01),能量負荷顯著降低(P<0.01)。結果見表3。
表3 兩組大鼠足三里穴區組織能量代謝物質及能量負荷比較 (±s)

表3 兩組大鼠足三里穴區組織能量代謝物質及能量負荷比較 (±s)
注:與正常組比較,1)P<0.01,2)P<0.001
?
3 討論
穴位是人體臟腑經絡氣血輸注出入的特殊部位,是經絡-臟腑相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古代文獻和現代臨床均表明,穴位對于疾病不僅具有治療作用,而且具有診斷作用。《靈樞·背腧》記載:“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此乃描述了古人以壓痛點進行揣穴并以此作為治療部位進行針灸的一種方法,也說明了穴位敏化是中醫診斷和針灸治療作用的基礎。現代針灸臨床中也多有通過診察穴位局部感覺等變化來診斷和治療疾病的報道[7-8]。隨著穴位敏化研究的不斷深入,朱兵在《系統針灸學》中提出的穴位本態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即穴位是機體在病理狀態下能與相應靶器官/組織發生交互作用的體表位域[9]。穴位的功能活動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會隨機體的生理病理變化而產生對應的“靜息態”和“激活態”,從而存在“開/合”的動態變化。穴位由“靜息態”向“激活態”的轉化過程被稱為穴位的敏化,穴位敏化過程是針灸發揮治療作用的基礎[10]。
既往研究表明,穴位敏化的表現形式主要有痛敏化、熱敏化、光敏化、電敏化、聲敏化、壓力敏化、化學敏化、形態敏化和微循環敏化等[11-12]。其中痛敏和熱敏的研究較為多見,化學敏則作為一個較新的概念出現于近些年的文獻中。化學敏是指穴位局部組織細胞化學成分的改變,如敏化狀態下釋放神經肽、致敏物質等[11]。目前研究較多的穴位敏化相關物質有P物質、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CGRP)、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組胺等。羅廖君等[13]在對足三里穴位敏化相關文獻的研究中,將借助針灸等干預后采用生物化學手段進行的檢測均計入化學敏范疇,歸納足三里化學敏研究主要指標包括強啡肽、β-內啡肽、P物質、血漿5-HT含量、中縫核5-HT表達等,檢測指標主要依據研究病種不同而存在變化。本研究基于能量代謝物質ATP、ADP和AMP探討胃潰瘍大鼠足三里穴的敏化反應,屬于化學敏的范疇。
ATP作為細胞的主要供能物質參與體內的許多代謝反應。當ATP作為能量物質被消耗時,則隨著能量的釋放逐級轉化為ADP、AMP。當細胞內能量富余時,則會使ADP磷酸化轉換成ATP來存儲多余的能量。組織內ATP、ADP和AMP可根據機體的代謝狀況相互轉化,從而產生能量負荷比率的變化。因此,通過組織中ATP、ADP和AMP的含量可推測機體或局部組織的能量代謝情況。研究發現,心肌缺血、腦缺血、膀胱機能障礙等均可出現相應臟腑ATP、ADP和AMP的代謝變化,針灸對其具有良性調節作用[14-16]。然而研究多集中于觀察臟腑中的ATP等能量代謝變化,對所干預穴位局部的相關觀察則較為少見。本研究發現,胃潰瘍大鼠的胃組織和足三里穴區組織ATP、ADP含量和能量負荷均顯著降低,AMP均顯著升高。可見,當發生胃潰瘍時,不僅胃組織ATP的能量消耗增加,足三里穴區也隨之發生ATP能量消耗的增加,這可以說是中醫“有諸內必形諸外”在生物化學層面的一個體現,說明了足三里是與胃腑經絡之氣相通并隨之活動變化的反應點之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足三里與胃的相關性提供了實驗依據。我們在前期運用EB滲出觀察胃潰瘍相關的穴位敏化研究中,EB滲出點多在督脈背段及膀胱經第一側線,并未發現足三里穴區有EB滲出點,但本研究進一步實驗發現,胃潰瘍狀態下,足三里穴區的能量代謝物質ATP、ADP和AMP含量均發生明顯變化,這可能是胃潰瘍疾病在體表穴位的一種化學敏化反應,說明同一疾病不僅具有多部位的穴位敏化,而且穴位敏化形式也具有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