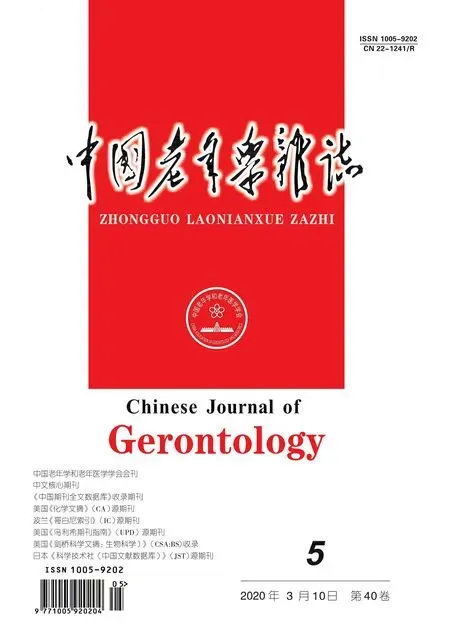高齡老人家庭虐待傾向與照顧負擔、照顧者心境的相關性
辛惠明 葉毅敏 陳芬菲 李輝 楊士來 紀小鳳 陳月
(泉州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福建 泉州 362100)
隨著經濟發展及醫療水平的提高,人口預期壽命不斷延長,高齡老人數量不斷增加。高齡老人的激增使養老照護產生巨大挑戰。目前大多數高齡老人選擇居家養老,這使照護家庭承受著各種壓力,甚至可能引發照顧者出現負性情緒或虐待傾向。本研究旨在通過問卷調查分析高齡老人家庭虐待傾向與照顧負擔、照顧者心境的關系。
1 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采取方便抽樣方法抽取福建閩南地區147名高齡老人及其主要家庭照顧者。納入標準:①老年人≥80歲,照顧者≥18歲;②照顧者為配偶、子女或其他親屬;③照顧時間≥6個月。排除標準:①收取報酬的照顧者;②不愿參加本研究者。
1.2調查工具
1.2.1一般資料調查表 研究者通過查閱相關文獻,自行設計一般資料調查表,分為高齡老人一般資料調查表與主要照顧者一般資料調查表。高齡老人一般資料調查表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原職業、患慢性病種類、經濟來源、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DL)等。主要照顧者一般資料調查表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職業、與老人關系、是否同住、平均每日照護時長、主要照顧項目等。
1.2.2照顧者虐待老人評估量表(CASE) 該量表由 8個封閉性問題和 1 個開放性問題組成。封閉式問題為是否存在身體虐待、心理虐待、疏忽照顧等相關內容陳述,回答“是”得1 分,“否”得0 分,條目累計分值即為總分,分值0~8分,≤2分無虐待傾向,≥3分即存在虐待傾向,得分越高則虐待傾向越大。開放性問題由照顧者根據經驗填寫。該量表信效度良好,Cronbach α系數為 0.77〔1,2〕。
1.2.3照顧負擔量表(ZBI) ZBI Cronbach α系數為0.87,表明具有較好的信度。 量表包括量表包括個人負擔和責任負擔2個維度。 量表總分<21 分為無或輕度負擔,21~39 分為中度負擔,≥40分為重度負擔〔3〕。
1.2.4簡明心境狀態量表(POMS) POMS量表包含7個分量表,分別是正性情緒(精力與自尊感) 及負性情緒(緊張、疲乏、憤怒、壓抑及慌亂),信度為0.62~0.82。共計40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計分,每個量表評分均換算為百分制,分數越高表明情緒控制越差〔4,5〕。
1.3調查方法 調查人員均為培訓合格的護理志愿者,采取入戶調查法。調查過程中調查人員采用統一指導語,并由研究對象獨立完成或者在不影響調查結果的前提協助完成,當場回收。共發放問卷161份,回收有效問卷147份,有效率91.30%。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8.0軟件進行秩和檢驗、Spearman相關分析、線性回歸分析。
2 結 果
2.1不同特征高齡老人照顧負擔得分比較 高齡老人照顧負擔總分為(32.29±1.74)分,屬于中度照顧負擔。不同文化程度、ADL、慢性病種類的高齡老人的照顧負擔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不同特征照顧者家庭虐待傾向、心境狀態得分情況 高齡老人家庭虐待傾向得分(3.43±0.23)分,存在虐待傾向。照顧者的心境狀態總分為(114.76±2.44)分,屬于中度水平。并且家庭虐待傾向、心境狀態在年齡、性別、與老人關系、是否同住、平均每日照護時長、主要照顧項目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P<0.01),心境狀態在不同文化程度的照顧者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2。
2.3家庭虐待傾向與照顧負擔、照顧者心境的相關性 將家庭虐待傾向、照顧負擔、心境狀態得分進行Spearman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家庭虐待傾向、照顧負擔、心境狀態三者間有顯著正相關關系(P<0.01)。見表3。

表1 不同特征高齡老人家庭照顧負擔得分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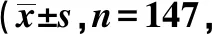
表2 不同特征照顧者家庭虐待傾向、心境狀態得分情況分)
1)P<0.01;2)P<0.05

表3 家庭虐待傾向與照顧負擔、照顧者心境的相關性(r值)
1)P<0.01
2.4家庭虐待傾向線性回歸分析 以家庭虐待傾向為因變量,以照顧負擔、心境狀態為自變量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照顧負擔、心境狀態對家庭虐待傾向具有預測作用。見表4。

表4 家庭虐待傾向線性回歸分析(n=147)
3 討 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高齡老人存在虐待傾向,照顧者的負擔總分、心境狀態總分均屬于中度水平。不同特征的高齡老人及照顧者的家庭虐待傾向、照顧負擔、心境狀態有所不同。其中照顧負擔隨著老年人的年齡、慢性病種類的增加而增加。高齡老人隨著年齡增長,各方面功能會伴隨老化而加速衰退,再加上慢性病對身體的損傷,使高齡老人需要他人的照護量增加。因而高齡老人年齡越大、慢性病種類越多,給照顧者造成的負擔也越重。照顧者的照顧負擔還與高齡老人生活自理能力有關系,生活自理能力越差照顧負擔越重,與Rezende等〔6〕的研究結果一致。高齡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越差,需要照顧的時間越多,照顧的難度也越大,因此,照顧者常常會覺得照護任務繁重,從而容易產生不良情緒,并將情緒轉嫁給高齡老人,導致有意或者無意的虐待行為的產生。
本研究中,照顧者是高齡老人的女婿或媳婦,其家庭虐待傾向和心境狀態得分較高,即存在較為嚴重的虐待危險和不良的情緒表現。可能與血緣親疏及福建閩南傳統婆媳難處理念有關。在“是否同住”這項中,與高齡老人同住的照顧者比不同住的照顧者出現家庭虐待傾向更為明顯。有研究也顯示,老年人與配偶之外的人員同住時,老年人和照顧者發生摩擦的概率顯著增加,其受虐風險大大提高〔7,8〕。相對不同住的照顧者,與高齡老人同住的照顧者不良情緒反而減少,可能是與高齡老人同住的照顧者通過虐待老人,已將部分不良情緒發泄。每日照顧時長在>6 h且<12 h的照顧者對高齡老人施虐的概率最多,≤6 h的照顧者存在虐待行為最少。每日照顧時長在>6且<12 h的照顧者雖然花在照顧老人的時間不是最長,但正是照顧時間不夠長的緣故,這類照顧者總想利用空暇時間兼顧其他事務〔9〕,而照顧之余并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其他事務,因而容易歸責于高齡老人。每日照顧時長在≤6 h的照顧者,除了照顧老人,仍有足夠的時間處理個人事務,因而存在虐待行為最少。而每日照顧時長在≥12 h且≤18 h或>18 h且≤24 h的照顧者,雖然照顧老人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但是這類家庭,一般會采用專人全心照顧的生活方式,照顧者除了照顧高齡老人并不怎么承擔其他事情。但是每日照顧時長在≥12 h且≤18 h或>18 h且≤24 h的照顧者不良情緒仍是較多,可能與長期每天長時間照顧高齡老人失去個人自由有關。主要承擔日常生活照護的照顧者,不良情緒較明顯。日常生活照護內容一般是進食、更衣、洗漱、移動、如廁等照護,這些照護較煩瑣甚至骯臟惡心,所以照顧者不良情緒最多。雖然這類照顧者不良情緒最多,但是虐待傾向卻低于協助家務,可能是因為需要日常生活照護的高齡老人幾乎都是癡呆、腦卒中、疾病等導致自理能力受限或喪失,照顧者雖然有不良情緒,但仍對這些癡呆、腦中風、疾病等弱勢老人心存同情體恤,因而虐待行為反而減少。主要照護項目是心靈慰藉與陪伴的照顧者并不存在虐待傾向與不良情緒。主要原因是心靈慰藉與陪伴,可能是促進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雙方的情感交流和家庭歸屬感。其實,幾乎所有的高齡老人都渴望心靈慰藉與陪伴,可能是因為高齡老人日漸退出社會主流,交流范圍縮小,導致老人心理弱化,渴望慰藉與陪伴〔10〕。提示高齡老人照顧者除了滿足老人生理需求,還要注意其心理需求。應多給予老人心靈慰藉與陪伴,不但有利于雙方關系進一步和諧化,還能促進家庭氛圍進一步融洽。
高齡老人家庭虐待傾向與照顧負擔、心境狀態均呈顯著正相關,表明照顧負擔越重、心境狀態越差家庭虐待傾向越嚴重,意味著減輕照顧者的照顧負擔或調整心境狀態,有助于緩解高齡老人家庭受虐問題。長期繁重的照顧負擔容易引發照顧者生活疲潰,不但會危害照顧者的身心健康,還會影響高齡老人的照顧質量。如果照顧者的身心疲潰感無法得到及時適當地緩解,長期處于抑制狀態,極有可能增加照顧者的心理應激和負面情緒,進而將應激和情緒投射給被照顧的高齡老人,繼而對其實施虐待。提示要加強高齡老人照顧者的指導與教育,提高照顧者的綜合素質和應對方式,減輕照顧者的照顧負擔與負性情緒,進而降低家庭虐待行為的發生率,提高高齡老人與照顧者的生活質量。此外,還應給照顧者提供心理疏導及發泄途徑或建設高齡老人日間護理站,給照顧者喘息機會和調整時間。同時,需要進一步增加照顧者的社會支持,鼓勵家庭的其他成員,協助照顧者分擔高齡老人的照護責任,從而緩解高齡老人受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