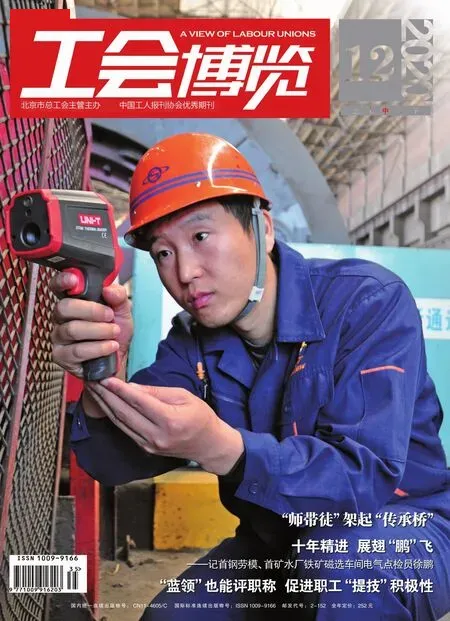燕歌戲:京西戲曲“活化石”
在北京市門頭溝區的齋堂鎮柏峪村,一代一代傳承著一個獨特戲種——燕歌戲。燕歌戲是北京市的傳統戲曲劇種之一,有著“戲曲活化石”之稱,不僅戲曲題材豐富,還有著九腔十八調,雅俗兼備。已有數百年歷史的燕歌戲于2006年入選北京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宣傳和保護工作不斷完善。為了實現進一步傳承,燕歌戲傳承人,78歲的陳永祿帶著老藝人們成立劇團,并嘗試著不同形式的創新,為燕歌戲注入新的活力。
燕歌戲的源起與歷史
蒼莽的京西山區,各類文化集聚于此,多種戲曲蔓延于村里鄉間。齋堂川里,愛唱戲的,能唱戲的村子不下二三十個。門頭溝區齋堂鎮的柏峪村,是燕歌戲表演中最具代表性的村莊,亦被稱作燕歌戲開始的地方。
燕歌戲,始于宋元,興于明清。《元史》載:元代有宮縣登歌,分文武,舞于太廟,稱“燕樂”,民稱“燕歌”。柏峪由于當地口音之故,也俗稱“秧歌”。“燕樂”,始見于《周禮·春宮》,指天子與諸侯宴飲賓客使用的民間俗樂。
據傳,“燕歌”由江西虞集親自教戲,并請司樂人掌之。宋文宗時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有數百里無孑遺者。時任奎章閣侍書學士的虞集,從帝詔救關中之災,來至當地。柏峪曾有一位與虞集同窗的王姓學士,因尚未就任便與虞集一起創建戲劇,教習當地百姓演唱,于是便有了“燕歌戲”的出現。
自春秋戰國時期,京西成為燕國的西部邊界,便開始在道路的易守難攻處設置關口、關城,大道為關,小道為口,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明朝天子們本欲憑借長城之險,御敵于國門之外,卻不料長城防線兩次被攻破,其中第一次,御駕親征的明英宗,甚至做了蒙古軍的階下囚,史稱“土木之變”。
從此,明廷開始建御城、筑敵樓、建烽火臺,設置邊關,大力加強西山防御,柏峪村東北一公里處的“天津關”便由此而建。天津關,又名“天井關”,位于進京古道和內長城的結合部,是防御西北來犯之敵的第一道邊關。朝廷于此修建守御城池——沿河城,并設守御千戶所駐防,駐軍最多時達兩千余人。而后,又建齋堂輔城,與沿河城成掎角之勢。京西門頭溝區星羅棋布著近200個大小村落,其中的軍戶村落就有幾十個。這些軍村的名字,大都帶有“軍、城、口”等字眼。柏峪村,原名柏峪口。早年,這里常年駐軍,后來,當年駐扎的軍人留了下來,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漸而形成典型的軍村,至今仍保留著軍隊的習俗。眷屬從天南地北而至,帶來了各地不同的文化,當地以燕歌戲為主的戲劇,吸納了不同戲種的腔韻,形成一種獨特的、含有南北九腔十八調的地方戲,其藝術行當涵蓋生旦凈末丑、詩曲媚俗白、說唱念坐打、吹拉彈唱走,行當齊全。
柏峪人唱燕歌戲,簡直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村里人張口閉口全是戲,事情有了著落,就說“有戲了”;事情沒希望,就說“沒戲了”等等,嬉笑怒罵都是戲詞。村中從天真的兒童,到鬢發斑白的老年人,好歹都能唱兩嗓子。
村人愛戲如此,村劇團的人就更甭說了。大凡唱戲的,只要聽到鼓點兒聲,便嗓子發癢,手里哪怕有兩塊石頭,都會磕打出個鼓點兒來!村里有個老戲骨,有一天,他不知村里要唱戲,照例上山放羊。他見大雨將至,趕忙往山坡上趕羊避雨。此時,恰巧村里來人,叫他回村演《張花娶妻》。他是村中飾演張花的不二人選,有他在村里沒人敢上場。救場如救火,他二話不說,立馬回村登場。當他聽說山洪沖走了羊,立改戲詞,唱道:“眾人臺下我臺上,為唱大戲舍了羊。我人急得貓抓心,臺上依然笑臉放。只要大家能開心,俺家丟羊算個啥?”又唱道:“身穿戲裝入洞房,無名大水沖我羊。誰要撈得羊在手,當我結婚發喜糖。”臺下觀眾得知實情,立刻掌聲雷動,紛紛喊道:“戲人,戲人!這才是角兒呀!”還有不少人往戲臺上扔“打喜錢”。老藝人舍己事救戲場,戲臺上靈動,唱詞妙改,真個是戲比天大。這就是戲曲的力量!
在村里,不但唱戲的有癮,看戲的癮更大。聽說要唱戲,很多人家早早就搬上凳子、馬扎去“占地兒”;有的提前把親戚朋友請到家里來,大老早的就做飯,吃飽喝足,就憋著看戲!山區的鄉村里,流傳著一段順口溜:“拉大鋸、扯大鋸,姥姥家門前唱大戲;接閨女、請女婿,外甥兒臊著臉兒跟了去!”說的是無論哪個村演戲,都得去請鄰村的親友,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一同去看戲。山村人熱情好客,今兒個你請,明兒個我喚,如此你來我往,就像拉大鋸似的,久而久之,便成了鄉俗!
陳永祿5歲與燕歌戲結緣
幾百年來,燕歌戲的流傳并非世襲,也不像正規的江湖戲班要拜師學藝,而是有興趣的就可以參加。茶余飯后、田間地頭,會唱戲的老人們往往就會唱上幾段,有興趣的人也可請教,因此藝人們都是靠耳濡目染、心領神會學習,沒有固定師傅。但這其中,燕歌戲也有自己獨特的規定。“咱們這戲還有這個說法,口傳心授,傳男不傳女,傳內不傳外,你是柏峪村里的男孩子就教,這是老人一直傳下來的規矩。”陳永祿坦言,這也正是為何燕歌戲只在柏峪村獨有,而沒有流傳到其他村落的原因之一。
陳永祿告訴記者,從前柏峪村每當年節、廟會或是農閑之時,人們都要唱戲:二月二,八月十五……特別是過年時最為隆重,從臘月二十三小年一直唱到正月十五鬧元宵,晝夜不停。一部《羅衫記》就要唱上十幾個小時。至今,陳永祿還能講述整本兒的《羅衫記》。陳永祿介紹,柏峪燕歌戲的戲曲題材非常豐富,可以說是無事不記,無事不唱。大到王公貴族,小到平民百姓,從小草到太陽、從狼虎到神話……戲詞深奧,雅俗兼備。在戲詞中,有詩人的名句,有百姓心里話,也有俚語番情,可謂“南北九腔十八調”,頗具雅俗共賞的綜合性。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清代及民國時,柏峪燕歌戲以戲班形式進行表演,不僅在本地,還時常應邀到外地演出,這是燕歌戲歷史上最為繁盛的時期。抗戰時期,由于日寇入侵,山鄉的演戲傳統一度中斷,當年戲班保留的清代中后期的行頭、道具等經歷戰亂,與村中的老戲臺一同被化為灰燼。新中國成立后,村中建起禮堂代替戲臺,村民們平時仍以務農為主,閑暇時又唱起了燕歌戲。
陳永祿開始學戲的時候才5歲,那個時候他對燕歌戲還沒有什么認識,然而一次偶然,讓他與燕歌戲結緣。當時,年僅5歲的陳永祿去鄰居家玩耍。鄰居家里貼著兩幅“炕瓷扇”(炕瓷扇就是當地百姓床上擺的一種柜子,柜子上鑲嵌著陶瓷版畫,由于版面像扇子,故名炕瓷扇),畫里的內容都是戲曲故事。陳永祿看到“炕瓷扇”入了迷,趴在那里目不轉睛地看著。眼看到了吃飯的時候,陳永祿的母親去找他,發現陳永祿正盯著“炕瓷扇”咿呀咿呀地喊著什么。此時鄰居家的老爺爺走了過來,便勸說陳永祿的母親讓孩子學習當地的燕歌戲。經過陳永祿的不懈努力,他的唱功也與日俱增。
陳永祿年輕時唱小生,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改唱花臉,而這種一人客串多個行當的情況在柏峪非常多,一般演員都能通曉幾種行當,并可相互替補。現在,因為嗓音失潤,陳永祿已經不在舞臺上唱戲了,但是從他的眼神里還能看得出來他對燕歌戲,對舞臺的熱愛。采訪中,聊到高興,陳永祿又過了一把癮,為我們清唱了一段《還魂曲》。
成立專業劇團讓“老戲”薪火相傳
據陳永祿回憶,從前燕歌戲的劇目大約有100多出,每出都有長達幾萬甚至十幾萬字的唱詞,后來很多劇目就因久久不唱而失傳,很多老藝人也記不清臺詞了。隨著他們相繼辭世,使得陳永祿感到深深的憂慮:劇目尚未整理,幾十出戲已經失傳,僅存名目又不知腔調、臺詞。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陳永祿自己買來紙筆,在閑暇時找到村里會唱戲的老人們把唱詞記錄下來,開始搶救燕歌戲。目前,經陳永祿記錄整理的劇目已經有40個之多,他們劇團排練了其中的18出。在搶救和重新排練老劇目的同時,陳永祿還和大伙一起創編了新的劇目,唱的就是柏峪村。
為了更好地傳承和發展燕歌戲,陳永祿還對燕歌戲進行了大膽的改革。而對于過去教戲、演戲的老規矩,陳永祿也帶頭破除。陳永祿的女兒陳全霞就是劇團里的主要演員之一。“2001年時,村中只剩下5位唱燕歌戲的老藝人。柏峪人不忍心傳承數百年的藝術斷送在自己這輩人中,開始竭盡全力地挽救這個劇種。”陳全霞告訴記者,父親從2003年擔任村劇團團長至今,一面將仍留存的劇目記錄下來,一面把村中唱戲的藝人們聚集家中,由每個人將其飾演角色的臺詞口述出來,他逐一記錄,加以整理,一出出戲目就這樣被搶救下來,共形成40個劇本,每一出劇目都浸透著他們的心血。
“2006年,燕歌戲被列入北京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加以宣傳和保護。當聽到這個消息時,我激動得哭了。”讓陳永祿欣慰的是,為了保護好老祖宗留下的瑰寶,村里修建了可容納300余名觀眾的劇場,購置樂器行頭。高大寬綽的戲臺上,幕布、燈光、音響、字幕墻,一應俱全。門頭溝區委區政府重視戲劇的發展,積極為村劇團隊配備服裝、道具、樂器,對村劇場的音響、燈光、機械等進行配置和改造,使其成為兼戲曲、綜藝、會議為一體的綜合文化服務場所。目前,柏峪村成為全市唯一一家村級專業文化劇場。村劇團有演員46人,有完整劇目20余個,每年組織演出40余場。今年9月20日至21日,柏峪村文化劇場舉辦了柏峪燕歌戲文化藝術節,進行了燕歌戲古裝游行,開展了戲劇文化學術論壇。村劇團還專場演出了自編自演的燕歌戲《天津關》。藝術節雖屬村辦,卻引來了眾多戲曲名家。京劇梅派第三代傳人胡文閣,新鳳霞女兒吳霜,河北梆子名家、國家一級演員張樹群,北京京劇院言派老生王寧,梨園春擂主武剛、武朵,以及著名的越劇、晉劇演員,競相登臺獻藝。許多外地人和當地劇團、戲劇愛好者亦紛至沓來。
燕歌一曲醉古今,百年老戲呈新韻。柏峪人,歷經數代的傳承與創新,已為燕歌戲插上夢想的翅膀!柏峪人,要把燕歌戲祖祖輩輩傳下去,讓它唱出村,唱出區,唱出市,唱得更遠,唱得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