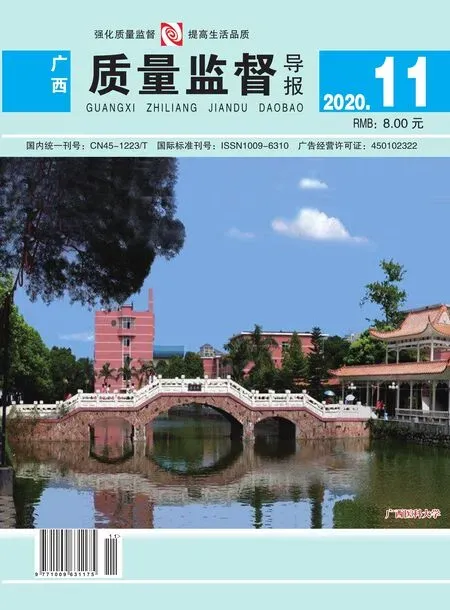受控外國企業的界定問題研究
夏 燕
(中央財經大學 北京 100089)
一、問題意識
我國目前正處于“一帶一路”發展戰略落實的關鍵時期,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境內企業實施對外投資。隨之而來的則是國際避稅問題,這種問題的存在無疑是對國家征稅主權的挑戰,必須嚴肅對待。
受控外國企業(以下稱“CFC”)作為國際避稅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概念于2008年首次出現在我國稅法中,至今雖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但其界定規則仍存在許多模糊之處,導致實踐中企業對該規則認識不清晰,稅務局擁有過大的自由裁量權。隨著對外投資擴張,我國學者對于CFC規則愈發關注。
縱觀我國學者對CFC規則的研究,既有著眼于宏觀層面進行整體稅制的中外對比,提出完善建議的(黃曉珊①,2014;吳頡②,2016;張雨路③,2018);也有從微觀角度入手,選取CFC認定的一個或幾個要點進行專門討論的,這些要點主要有“控制”標準的判斷(趙立濤④,2011;鄭翔宇⑤,2012;張澤平⑥,2014;付迪⑦,2016)、納稅主客體的適用(宋興義⑧,2010;計金標、應濤⑨,2017)以及避稅地的界定(強盛⑩,2010;宋興義,2011;王淼,2016)等。
前人的研究為筆者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參考,不過上述研究大多停留在對理論的總結梳理方面,很少結合案例加以說明。少數學者在文章中引入案例,但大多是稅務機關正確界定CFC的案例,在論證實踐中CFC規則的現存問題等方面缺乏說服力。因此,在CFC規則現存問題的論證視角和案例選擇方面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基于此,筆者通過對CFC的界定規則進行梳理,選取實踐中稅企因CFC認定發生爭議的案例,指出目前相關立法的不足,提出相應的完善進路。
二、稅法相關規定及其不足
我國關于CFC的規定主要體現在《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以及《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國稅發〔2009〕2號文件,以下稱“2號文”)第八章中。2號文第76條對CFC進行定義,由此出發,對于CFC的界定主要需捋清以下三個概念:
(一)何謂控制
控制在本質上表現為一種“支配力”,只要一個公司能支配另一個公司的經營決策,就稱他們之間存在控制關系。
目前我國稅法中對CFC的界定要求滿足的控制標準僅包含股份控制標準,即只要居民企業,或居民企業和居民個人在納稅年度任何一天直接或間接單一持有外國企業10%以上的有表決權股份,且其共同持有的股份達到50%以上,就認為其滿足CFC規則的控制標準。需要注意的是,對于間接持股比例的計算,應當將各層比例相乘,若中間層持股超過50%,則按100%計算。換句話說,如果居民企業持有的股份未達到稅法規定的標準,即使該居民企業在實質上對該外國企業具有支配力,仍無法將其認定為CFC。這顯然不符合實質優于形式原則的要求,容易給納稅人留下避稅的空間。隨著公司制度的不斷發展,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現象越發明顯,單一股份控制標準的管理方法顯然已經滿足不了現實中對于CFC規則的要求。
國家稅務總局于2015年9月17日發布的《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征求意見稿)》曾對控制標準的修改提供了以下思路:第一,建議在界定居民個人單一持股比例時,將其近姻親、直系血親以及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系的居民所持有的股份也考慮在內;第二,對居民企業持有外國企業股份的認定,還需要考慮其關聯企業的持股情況;第三,尊重實質優于形式原則,引入實質控制概念作為控制標準的兜底性條款,即當依據股份控制標準無法將外國企業認定為CFC,但該外國企業在資金、經營、購銷等方面又確實被我國居民企業或居民企業和居民個人控制時,稅務機關可以啟動實質控制標準來對CFC進行判定。
(二)何謂實際稅負
CFC應當是設立在低稅率國家(地區)或者避稅地的外國企業,我國稅法規定,實際稅負低于12.5%的國家或地區即為滿足條件的低稅率國家或地區。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此處的稅率指的是實際稅負而非名義稅率。這也是實踐中稅務機關與企業之間對于CFC認定的主要爭議點,大多數企業容易誤將名義稅率作為對低稅率國家(地區)認定的依據。實際稅負的規定對CFC規則的實操性提出挑戰。
(三)何謂非出于合理經營需要
我國稅法對于CFC認定的主觀要件是該外國企業“非出于合理經營需要”的目的不分配或者少分配利潤。《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120條對于“非出于合理經營需要”進行了說明。實踐中,國家稅務總局通常通過判斷CFC的交易活動是否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來判斷是否存在不合理安排:1.存在人為安排;2.公司從該安排中獲取了不正常的稅收利益;3.公司進行該安排的主要目的就是獲取稅收利益。如果同時滿足以上條件,那么就認定該外國企業滿足“非出于合理經營需要”的認定條件。
目前我國稅法中對于合理經營需要的規定都過于原則性,細化合理經營需要的相關規定是CFC規則改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典型案例分析
(一)我國首個CFC避稅案例
1.案例簡述
A企業是注冊地在山東的一個化工品銷售企業;B公司是A公司設立在香港的全資子公司;C公司是B公司設立在香港的全資子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資業務,該公司擁有中國境內D、E、F三家公司各90%的股份,另外10%的股份由A公司持有。B公司于2011年將C公司的全部股權以四億五千萬元的價格轉讓給荷蘭某公司,自此,該荷蘭公司實際控制中國境內的D、E、F三家公司。
B公司在這次股權轉讓中獲益約三億元,但對應當歸屬于A公司的利潤一直未作分配。直到2012年企業所得稅新政將“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歸類為免稅收入,B公司才委托A公司向主管稅務機關申請居民企業身份證明,并計劃向A公司分配股權轉讓利潤。最終國家稅務總局未予通過B公司的申請,B公司也因此將利潤分配計劃擱淺。稅務機關經過調查,認定B公司為典型的CFC,調增A公司利潤3億元。
2.對案例的思考
對于“非出于合理經營目的”的認定需要考察公司這一獨立法人的主觀心理狀態,而國家稅務總局對于這一問題并沒有給出具體的測試方法和細化的判斷標準,僅強調考察企業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一詞本身就極具爭議性,何謂主要目的?如何確定逃避稅負是否為該公司的主要目的?目前我國稅法對這些問題還沒有做出相應回答。
實踐中,地方稅務機關只能根據經濟實質原則,綜合考慮公司的客觀表現及自身經驗加以把握,易導致“同案不同判”的問題。
(二)朝陽地稅BEPS計劃反避稅案
1.案例簡述
本案例主要涉及四家公司:S公司的注冊地為中國香港地區,B為注冊在英屬維爾京(BVI)的一家公司,A公司的注冊地在北京。2015年5月5日,A公司將自己的全部股權作價21058400元人民幣,轉讓給S公司。
朝陽區地稅局對這兩筆交易進行調查發現,S公司實際上是B公司的子公司,B公司通過其他幾家設立在避稅地的公司間接控制了S公司的全部股權,而經過第二次股權轉讓后,B公司實際通過S公司間接控制了A公司的全部股權。此外,稅務機關還發現,B公司的唯一控股股東徐某與A公司原控股股東閆某實際上是夫妻關系,兩次股權轉讓交易的目的就是間接轉讓北京的A公司。通過這種安排,A公司的股權轉讓利潤都會歸屬于設立在英屬維爾京的B公司。于是,稅務機關判定徐某及其丈夫閆某,通過在BVI設立B公司,間接轉讓A公司股權,并將股權轉讓利潤滯留在B公司,B公司實質上屬于CFC(該案公開時尚未完結,稅務局仍在對相關股東進行約談和審查)。
2.對案例的思考
筆者認為,案例1是稅務機關正確認定CFC的案例,案例2屬于稅務機關因對稅法中關于CFC控制主體的規定認識不清而導致錯定的情形。我國稅法規定的CFC控制主體僅有兩種情形:(1)我國的居民企業;(2)居民企業和居民個人共同控制,不存在由居民個人單獨控制的情況。案例2中,徐某雖然是我國的居民,但也是B公司唯一的控股股東,沒有居民企業與其共同持有B公司的股份,因此B公司并不滿足CFC的認定條件。
四、域外經驗借鑒
(一)關于“控制”標準
1.股份控制方面
我國與美國一樣,都采用股份控制標準,且在計算所持股份時都會綜合考慮直接持有和間接持有的問題。但是,美國除了規定了間接持股規則外,還規定了推定所有規則,即將納稅人的特殊關系主體所持有的外國企業的股份視同納稅人自己持有一般并入計算,這里的特殊關系主體主要指家庭成員、合伙企業、信托關系等。這種推定所有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納稅人通過特殊安排分散持股來規避股份控制規則的約束,值得學習借鑒。
與我國不同的是,德國采取的股份控制標準的界定方法并不強調表決權,而強調資本所有權和選舉權。只要德國的居民企業或個人共同持有某外國公司一半以上的資本所有權或者選舉權,就稱其滿足CFC判定標準中的控制標準。與表決權相比,用資本所有權或選舉權的多少作為判斷標準的優點在于其更具直觀性,稅務機關在實際審查過程中可直接根據公司的相關材料做出判斷,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2.實際控制方面
目前我國CFC規則中尚未引入實際控制標準,雖然征求意見稿曾提出過相關建議,但最終并未正式實行。實際控制標準的缺位弱化了CFC規則的國際反避稅力度,企業容易通過內部安排規避CFC規則的管理。實際控制規則發展較成熟的當屬英國。如果英國居民企業或個人對外國企業的下列收入擁有大部分的所有權,就可判定該外國企業被英國企業或個人實際控制:(1)轉讓股權或資產產生的收入;(2)可歸屬于股東的收入;(3)清算后的資產。
(二)關于控制主體的規定
美國稅法中關于控制主體的規定采用“美國居民”一詞,其認為不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都可能利用遞延納稅制度和各國之間的稅差進行避稅安排。而我國雖然規定了居民企業和居民個人共同控制的情況,但僅有推定向境內居民企業分配股息的規定而沒有推定向居民個人分配股息的規定,同時也忽略了個人單獨控制外國企業的情況。因此,關于CFC規則的規定,我國存在個人所得稅法與企業所得稅法脫節的現象,容易被企業利用進行避稅安排。
(三)關于避稅地的判定
縱觀各國用于判定避稅地的方法,主要有比較法和列舉法兩種。比較法是指將該外國企業所在國的稅率與股東居民國的稅率作比較,如果低于一定標準即視為符合要求的避稅地。美國采用這種方法,且規定不能局限于名義稅率,需要將外國企業所在地的稅率扣除隱性優惠政策后的實際稅負與本國稅率作對比。列舉法又可分為正向列舉法和反向列舉法,即俗稱的“白名單”和“黑名單”。日本自1978開始采用列舉法,于1992年廢棄列舉法轉而適用比較法。我國CFC避稅地的認定采用比較法與白名單法并存的制度。
(四)關于“非合理經營需要”的認定
英美法系國家一般都為合理經營需要設定了適用的條件。以美國為例,其一般通過交易的盈利程度、免稅的原因等多項因素進行綜合判斷。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相比,更加重視合理經營需要的穩定性與持續性。例如法國就有一項反避稅理論叫“反常的管理行為理論”,即如果納稅人在以往任何理性的狀態下都不會像現在這樣與其他公司進行該項交易,就可以認為該納稅人出現反常行為,這起交易就自動歸于無效。
五、我國CFC規則的立法建議
(一)細化控制標準的判定規則
對比中外關于控制標準的判定規則,對我國控制標準的完善提出以下兩點建議:1.在股份控制方面,繼續實施直接持股與間接持股相結合的判斷方法,同時借鑒美國經驗,將特殊關系主體的持股比例也考慮在內,防止企業通過內部安排分散持股比例規避CFC規則的約束;2.引入實際控標準,并借鑒英國經驗,在稅法中給出具體的、細化的判斷規則,統一口徑,提高稅法的可預測性和穩定性。
(二)將CFC規則引入個稅制度
個人和企業都可能成為外國企業的股東,都有機會利用遞延納稅機制和國家間的稅差進行國際避稅安排。將CFC規則引入個人所得稅法可以將居民個人單獨控制外國企業的情況納入到CFC規則的審查機制中,也可以對應當歸屬于居民個人的利潤部分做視同分配安排,追征個人所得稅,提高稅收體制的完整性。
(三)簡化避稅地判斷方法
我國目前采用稅率比較法與列舉法相結合的方式進行避稅地的判定。稅率比較法在實際操作中存在很大的不便,不同的稅務局在處理案件時,可能面對同一國家,但是由于沒有權威界定,這些稅務機關都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資料整理、計算等步驟才能判斷其是否屬于避稅地。這明顯屬于重復工作,會降低稅務機關案件處理效率。
筆者認為應當發揮列舉法直觀、高效的優點,契合“一帶一路”政策的大背景,重點測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際稅負及綜合特征,明確是否符合OECD范本對于避稅地的定義。將符合的國家納入“黑名單”,給予重點關注,不符合的應當納入“白名單”,我國居民企業或個人對該國進行的投資應該受到鼓勵。同時,國家稅務總局對于名單列舉法的管理應采取定期測試與重點測試的方法。定期測試是要求國家稅務總局每隔一年對所有名單中的國家進行一次測試;重點測試要求國家稅務總局密切關注重點國家的稅制變化,一旦發生可能影響其成為避稅地的變化時,就要進行一次測試,及時更新名單,提高認定的精準性。
(四)完善“合理經營需要”規則
我國對于“合理經營需要”規則的規定較為簡單,缺乏可操作性。筆者建議我國對于CFC規則中的“合理經營需要”原則出臺相關解釋性法規,統一認定口徑,避免不必要的稅企爭議。首先,借鑒日本成功經驗,將固定經營場所作為判定外國企業是否出于謀取避稅利益而設立的標準之一。其次,學習法國的做法,密切關注企業的反常行為,具體列舉可歸于無效的反常交易的類型。再次,對經濟實質原則加以具體化,將“主要從事積極的生產經營活動所得”具體定義為從事積極經營活動以外的其他活動而產生的所得不得超過全部所得的50%。最后,規定不適用CFC規則的外國企業的主要交易對象和合作伙伴不能是其股東,這里的“主要”也可通過與股東的交易收入占所有主營業務收入的百分比來判斷,未超過50%即符合規定。
注釋:
① 黃曉珊:《受控外國公司稅制的國際比較與經驗借鑒》,碩士學位論文,河北經貿大學,2014年。
② 吳頡:《BEPS背景下我國受控外國公司稅制的重構》,碩士學位論文,華東政法大學,2016年。
③ 張雨路:《完善我國受控外國公司稅制的研究——基于反避稅視角》,碩士學位論文,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8年。
④ 趙立濤:《受控外國公司稅制比較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中國政法大學,2011年。
⑤ 鄭翔宇:《國際避稅中受控外國公司的界定問題研究與借鑒》,碩士學位論文,華東政法大學,2012年。
⑥ 張澤平:《國際稅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5頁。
⑦ 付迪:《受控外國公司規則中控制標準的界定》,碩士學位論文,華東政法大學,2016年。
⑧ 宋興義:《我國CFC稅制中存在的不足及完善》,載《涉外稅務》2010年第4期,第40-44頁。
⑨ 計金標,應濤:《國際經驗視閾的我國企業跨境稅收管理問題與對策研究》,載《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61-74頁。
⑩ 強盛:《受控外國公司進行法律規制問題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上海社會科學院,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