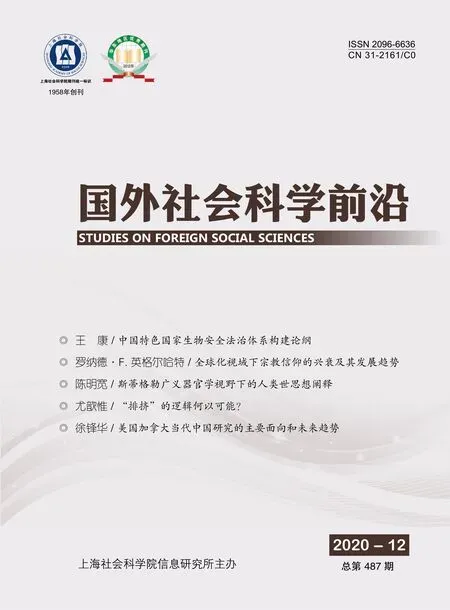斯蒂格勒廣義器官學視野下的人類世思想闡釋 *
陳明寬
內容提要 | 斯蒂格勒認為,人類缺乏內在的本能,必須依賴于外在于軀體的技術而生存。技術是人類的軀體外器官。軀體內器官和軀體外器官共同構成了人類的廣義器官系統。這是斯蒂格勒哲學理論的廣義器官學視野。在此視野下,工業革命成了一種開啟人類世時代的器官學革命。由于知識的被清除和自動化,人類世成了熵大規模增長的時代。機器剝奪了身體器官中“怎樣去做”的知識,數字技術則剝奪了心理器官中“怎樣去生活”和“怎樣去思考”的知識。人類成了徹底的無知者。當前的人類世充滿著毒性,已到達極度危險的臨界狀態。人類要想順利渡過人類世的極端狀態,必須構想一種克服人類世的可能性。
作為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為我們分析和理解技術現象以及由于當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而引起的各種問題,提供了一種原創性較強的哲學理論。斯蒂格勒善于吸收其他學科領域的成果和概念來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我們在此要討論的“人類世”(Anthropocene)1國內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一些學者,經常將“anthropocene”翻譯為“人類紀”,這種譯法是有問題的。克魯岑提出此概念時,是在將“anthropocene”與“全新世”(holocene)地質年代作比較,因而“anthropocene”相應地應該翻譯為“人類世”。如果將其譯為“人類紀”,就似乎顯示它是在與包括全新世和更新世在內的第四紀(quaternary period)作比較,而“紀”是比“世”在時間尺度上更大的地質年代單位。并且,國內地質學界對“anthropocene”的通用譯法就是“人類世”。,就是斯蒂格勒從地質學中借用而來的概念。“人類世”概念最初由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等人在2000年提出。2Paul Crutzen and Eugene 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IGBP Newsletter, vol. 41, 2000, pp. 17-18.其旨在表明“人類活動也是一種重要的地質營力,其對地球改造的程度與后果足以與傳統意義上的地質營力(地震、造山運動等)產生的影響相匹敵”。3劉學、張志強、鄭軍衛等:《關于人類世問題研究的討論》,《地球科學進展》第29卷,2014年,第646頁。克魯岑認為:“人類世開始于18世紀晚期,對這個時期的極地冰中空氣成分的分析表明,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濃度正是從此時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升高。”4Paul Crutzen,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vol. 415, 2002,p. 23.與克魯岑等人關注人類世中環境熵的增長不一樣,斯蒂格勒則在廣義器官學的視野下,關注人類世中人類熵(antropy)5“人類熵”(antropy)一詞是斯蒂格勒原創的詞匯,即將“entropy”中的“e”換為“a”。的增長。人類熵表示人類的愚蠢程度,即無知化(proletarianization)6這里的“proletarianization”以及后面的“proletariat”,是斯蒂格勒從馬克思那里借用而來的概念。馬克思的這兩個概念通用的中譯法分別為“無產階級化”和“無產階級”。但在斯蒂格勒哲學理論中這兩個概念準確的翻譯應該為“無知化”和“無知者”。因為,在斯蒂格勒看來,馬克思所說的機器對人類勞動的“異化”只是人類世中的技術對人類所具有的知識之剝奪的第一個階段。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所具有的知識會不斷地被剝奪,即人類會繼續地被無知化,直至成為徹底的無知者。的程度。對于斯蒂格勒而言:“由于知識被(從軀體內器官)清除并變得自動化,以至于根本不再有知識,……人類世中的熵也在大規模地增長。因此,人類世就是一個‘熵世’(entropocene)。”1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 51.
與克魯岑一樣的是,斯蒂格勒也認為工業革命是人類世的開端。由于蒸汽機這種技術器官的出現,工業革命成了一次器官學革命。2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 221.器官學革命使人類具有的知識被機器自動化所清除并取代,知識成了機器中標準化的運作流程,并進一步成為數字網絡中的數據信息。人類成了無知者(proletariat)。斯蒂格勒在廣義器官學的視野下審視人類世的基本狀況:人類世是熵(毒性)大規模且迅速增長的時代,目前人類世的熵已經最大化。3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 52.克魯岑對人類世的未來非常失望悲觀,人類世只會越來越壞下去,直至大災難的出現。而斯蒂格勒雖然對人類世現狀非常擔憂,但他并不對人類世的未來悲觀失望。在廣義器官學視野下,人類世當前的狀況已經蘊含著克服人類世的可能性。那么,克服人類世的可能性是什么呢?人類世當前的狀況又是怎樣的呢?這種狀況又是怎樣演進過來的呢?要理解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將斯蒂格勒的廣義器官學闡釋清楚。
一、斯蒂格勒的廣義器官學
在斯蒂格勒看來,人類之為人類不僅有軀體內器官(endosomatic organs),而且也有軀體外器官(exosomatic organs)。4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2: The Catastrophe of the Sensibl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p. 136.這種觀點來源于斯蒂格勒哲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人類天生缺乏足以維持其生存的本能,必須依賴于外在于軀體的技術而進化。這句話并不是指生物學意義上的缺乏本能,而是一種神話學意義上的假設:宙斯吩咐普羅米修斯和愛比米修斯為每一個會死的族類分配相應的本能和屬性。由于愛比米修斯粗心大意而無遠見,他給其他的動物分配了所有的本能和屬性。而輪到人類時,任何本能和屬性都沒有了。愛比米修斯把人類遺忘了,人類從起源處就一無所有。在此意義上,斯蒂格勒說,人類天生缺乏足以維持其生存的本能。5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87-192.而后來,普羅米修斯盜來了火和使用火的技藝,人類才能夠生存下去。不過,“普羅米修斯為了彌補愛比米修斯的過失,給人類的禮物是置身人類軀體之外的。……人類的存在就是置身于軀體之外的存在。”6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3.而外在于人類軀體的即是技術,這樣,技術就構成了人類的本質和存在方式。
為了支撐此種神話學假設,斯蒂格勒從勒魯瓦-古蘭(Leroi-Gourhan)的外在化(exteriorization)思想中找到了實證性的論據。“對于勒魯瓦-古蘭而言,外在化概念,是其所描述的人類化進程的中心議題。”7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6.外在化不僅是指將人類后生成的記憶外在化于軀體,也是指將軀體內器官本身就具有的記憶外在化:“人類整體的進化,傾向于將其他動物通過物種適應而獲得于內的東西置于其自身之外。”8A. Leroi-Gourhan, Gesture and Speech, Boston: The MIT Press, 1993, p. 235.石制工具的使用是將骨骼功能外在化,弓箭的發明將肌肉功能外在化,自動感應裝置將神經記憶外在化,人工智能則是將思維能力逐漸地外在化,即“通過技術來實施其器官功能的外在化”。9A. Leroi-Gourhan, Gesture and Speech, Boston: The MIT Press, 1993, p. 257.而這個時候,技術實則就構成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軀體外器官。不過,動物并沒有技術作為軀體外器官,人類和動物實際上是遵循著兩種不同的模式而進化的。
在斯蒂格勒看來,生命機體共擁有三種形式的記憶:1.基因記憶(genetic memory);2.后生成記憶(epigenetic memory);3.后種系生成記憶(epiphylogenetic memory)。1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7.動物的進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記憶決定的。動物通過基因遺傳從其前代獲得種系特征和生存本能。種系特征保證了其與前代的統一性,生存本能則保證此物種種系的延續。不過,動物在其生命過程中,也會獲得后生成記憶。但是,動物的后生成記憶絕不會通過外在化的技術傳遞給后代。“靈長類動物學家普遍地認同,即使是與我們最近的非人屬的親戚所使用的工具,也只是被每一代碰巧重新發明的。倭黑猩猩用木棍釣食白蟻的技能,并不作為累積的文化技能而被下一代所接納。這種關于前代的有利的(后生成)記憶不會遺傳給倭黑猩猩的下代。”2Gerald Moore, On the Origin of Aisthesis by Means of Artifici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T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Boundary 2, vol. 44, no. 2, 2017, pp. 208-209.那些能夠被寫入動物基因之中逐漸累積起來而影響物種進化的后生成記憶,只是極其微小的一部分,后生成記憶絕大部分會在代際間傳遞丟失。因此,動物的進化遵循著由基因記憶決定的漸進的種系生成(phylogenesis)模式。
“基因記憶的遺傳隔離在于保證動物物種的單一穩定性。”3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0-51.比如,貓科動物和熊科動物能夠比鄰進化幾千年卻從不互相混雜,并且,在這幾千年的過程中,其各自的種系特征也只是發生著極其微小的變化。人類的生物種系特征也是如此。“從解剖學上看,人類的身體從舊石器時代中期,到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再到青銅時代的原始書寫,直到我們所謂的數字時代,也一直沒有發生變化。”4Gerald Moore, On the Origin of Aisthesis by Means of Artifici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T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Boundary 2, vol. 44, no. 2, 2017, p. 199.不過,與舊石器時代打制石器的早期智人相比,因技術的進化而導致的我們與其之間的差別,就如同貓科動物與熊科動物之間的差別那么大。5A. Leroi-Gourhan, Gesture and Speech, Boston: The MIT Press, 1993, p. 247.人類的身體從早期智人時代至今,沒有發生過明顯的變化。但人類的技術水平已經進化了無數個量級,以至于早期智人和現代人雖沒有先天的種系差異,但二者在后天文化上的差異卻已無限大。甚至從旁觀者的視角來看,早期智人與現代人似乎已根本不屬于同一物種。
為什么會這樣?其中的關鍵原因在于,人類與動物對待后生成記憶的方式的差別:人類能夠將其認為是有利的后生成記憶,運用技術保存起來。人類“生命的后生成層次并不隨著生命的死去而喪失,相反,它把自身儲存沉淀起來,……這種后生成的沉淀,是對已發生之事的記憶,也就是過去,是我們以人類的后種系生成命名的東西。”6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0.這些被保存在技術載體中的后生成記憶,以及作為記憶的技術本身,就構成了人類的后種系生成記憶。因此,人類的進化遵循的實則是后種系生成(epiphylogenesis)的進化模式。它標志著人類與外部環境之間構成了一種新的關系,連接這種關系的就是技術。7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7.技術承載著人類生命過程不可或缺的器官功能,與人類軀體內器官一道共同構筑了人類生命的本質。“以至于構成人類生命之進化的負熵分化,就不再只局限于胚胎記憶和軀體記憶之中。”1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2: The Catastrophe of the Sensibl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pp. 139-140.在此意義上,技術就是一種器官,是人類的軀體外器官。后種系生成概念擴大了人類生命的范圍,它將承載著生命后生成記憶的技術納入人類生命的范圍。因此,人類之為人類不僅是由其軀體內器官定義的,更主要地是由其軀體外器官定義的。
我們可以將軀體外器官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技術器官,包括書籍、手機、汽車等技術物體,也包括書寫系統、交通運輸系統、數字網絡等技術體系;第二類則是因技術器官在與軀體內器官互動的過程中累積沉淀下來的制度、風俗、律法等集體精神器官(collective psychic organs)。相應地,軀體內器官也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身體器官(physical organs),如手和腳;第二類是心理器官(psychic organs),如欲望和理性。2斯蒂格勒在論述他的廣義器官學時,一般只提到三種器官系統:軀體內器官、技術器官和社會器官(集體精神器官)。就是說,他并沒有對軀體內器官的物理部分和心理部分做出劃分。斯蒂格勒有時候用軀體內器官僅指身體器官,有時候又僅指心理器官。這樣論述起來十分不方便。因此,為了將斯蒂格勒的廣義器官學思想更清晰地闡釋出來,筆者將軀體內器官劃分為身體器官和心理器官。這兩種器官系統構成了人類之為人類的廣義器官系統。它們彼此互相影響,處于亞穩定平衡(metastable equilibrium)之中,它們的器官功能總有著變化的可能。3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p. 104-105.斯蒂格勒將廣義器官系統中器官功能的變化稱之為器官的去功能化(de-functionalization)和再功能化(re-functionalization)。4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2: The Catastrophe of the Sensibl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pp. 118-124.于是,對軀體內器官和軀體外器官之間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的穩定與沖突的研究,就是一種廣義器官學(general organology)。這樣,斯蒂格勒哲學理論的廣義器官學視野就形成了。
二、器官學革命與人類世開端
技術器官是廣義器官系統中最不穩定的器官,幾乎每一次器官學革命的發生都有著新技術器官的出現作為誘因。作為一次器官學革命,工業革命的發生是因為蒸汽機這種新技術器官的出現,破壞了廣義器官系統原有的亞穩定平衡。不過,蒸汽機出現的意義遠大于此。蒸汽機是一種技術器官,但并不是自人類誕生以來就有的技術器官。更重要的是,它是第一種完全意義上的機器,是全新的技術器官。它的出現開啟了技術向著自動化方向進化的趨勢,直到今天甚至更遠的未來,自動化都將會成為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發展的動力和目的。
那么,什么是機器?所謂機器是指具有自身獨立動力來源的機械設備。以生物驅力(畜力)為動力的機械——比如馬拉的車、牛拉的犁等——都不是機器,因為此類機械與其動力之間是分離的。而以風力或者水力驅動的機械也不是機器,雖然它也有動力來源,但其動力來源屬于它所處的自然環境,不屬于它自身。離開了具體的自然環境,它們就無法獲得動力。蒸汽機既是機械,其動力又與機械本身合為一體。蒸汽機的動力來源于自身,又構成自身。因而,蒸汽機的出現就是完全意義上的機器的出現。機器是一種技術個體(technical individual),人類軀體也是一種技術個體。機器的出現開啟了生產勞動中的人類軀體逐漸被取代的過程,這是一種技術個體取代另一種技術個體的過程。當然,并不是所有的技術物體都是技術個體。對于斯蒂格勒而言,只有機器和人類才是技術個體。
斯蒂格勒對技術物體的論述采用了吉爾伯特·西蒙棟(Gilbert Simondon)的方案。在西蒙棟看來,技術物體的器官發生與動物生命體的器官發生是不一樣的。動物生命體已經是具體化(concretization)的,它不需要再在其機體中添加任何器官功能。所謂具體化過程,“就是把各種不同的功能濃縮進一個單一有效的結構中。”1Andrés Vaccari and Belinda Barnet, Prolegomena to a Future Robot History: Stiegler, Epiphylogenesis and Technical Evolution, Transformations, vol. 17, 2009, p. 6.而技術物體則是趨向于具體化。最先出現的技術物體是工具。從南方古猿時代的燧石開始,工具就是以人類軀體外的某種零散的器官出現的,但這種所謂的器官只有在被人類所使用時,才可以被稱為器官。一種剛剛被發明出來的工具,并不像動物個體一樣是已經具體化的東西,它所具有的功能非常抽象。它需要被別的個體承載起來才能發揮作用。正是在此意義上,西蒙棟將人類進化初期產生的燧石等工具稱為“技術元素”(technical elements)。它是人類骨骼器官功能外在化的表現,它成了對人類的骨骼功能進行替補的軀體外器官。之后出現的錘子、弓箭、犁耙、刀劍等,同樣是技術元素。它們與燧石的不同在于,其與人類軀體的連接對軀體的磨損更小,它們與軀體之間的聯系更像骨骼與肌肉通過關節相聯系那樣緊密和自然。
而承載工具這些技術元素的個體,則被西蒙棟命名為“技術個體”。技術個體可以分為兩類——人類與機器。在西蒙棟看來,技術個體能夠將各種不同的技術元素聚合起來,也即將各種工具聚合起來,并成為工具的承載者和使用者。以這種思路來看,人類就是一種天然的工具承載者和使用者,是一種天然的技術個體。但是隨著機器的出現,人類這種技術個體的地位便逐漸被同樣是作為技術個體的機器所取代。“西蒙棟認為,在機器出現之前,人類是工具的承載者,并作為技術個體。但在現代工業時代,機器成了工具的承載者,人類不再是技術個體。”2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1: 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 48.“ 機器取代了人類作為技術個體的功能。”3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inneapolis: Univocal Publishing, 2017, p. 78.人類作為技術個體的地位被機器所取代,正是開始于蒸汽機之出現的工業革命時代。工業革命與之前人類社會中所出現的技術革命有著根本的不同:之前的農業技術革命和書寫技術革命的發生只是由于新的技術元素的出現,而工業革命的發生則是由于新的技術個體的出現。工業革命之前,人類作為技術個體可以通過自身所掌握的各種勞動技能來勞動,他們掌握著使用工具的技能。但是,機器工業生產使勞動者掌握的技能失去用武之地,他們只能在流水線上執行固定的動作和姿勢。這一過程造成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說的“人的異化”現象。然而,在斯蒂格勒的廣義器官學視野中,機器對人類的取代并不構成對人類的異化。
技術元素是人類之軀體內器官功能外在化的產物,機器也是這種功能外在化的產物。當技術元素被人類這種技術個體承載起來之后,人類必須采用固定的動作和姿勢來使用這些技術元素,比如,使用錘子捶打的姿勢,使用刀具切割的姿勢。當機器取代人類技術個體的地位時,機器就同樣是“通過固定并具體化人類的姿勢而起作用”。4David Scott, Gilbert Simondon’s Psychic and Collective Individu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而且,作為技術個體,機器工作的姿勢要比人類勞動的姿勢更加標準和流暢,而且更有效率。人類勞動時的姿勢則極易受情緒和身體狀態的影響。人類并不是很好的技術個體,只是人類長時期占據著本屬于機器的位置。“在只有工具存在的時候,人類在其自身中已經集中了所有的技術個體性。現在,機器取代了人類作為工具承載者的位置,因為人類過去做了機器現在所做的工作。”1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inneapolis: Univocal Publishing, 2017, p. 21.因此,機器對人類的取代并不構成對人類的異化。
然而,機器對人類的取代卻是對人類軀體內器官所具有的知識的剝奪。這種剝奪過程貫穿由機器的出現所開啟的整個自動化趨勢之中,一直延續至今。在斯蒂格勒看來,人類的勞動技能是一種知識,是“怎樣去做”(how to do)的知識。
2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1: The Future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224.這種知識并非像物理、化學等顯性知識那樣可以通過口述和文字來傳授,它們是只能意會而無法言傳的動作和姿勢等隱性知識。機器的出現將勞動者所具有的“怎樣去做”的知識給剝奪了。這種知識被離散后寫入機器,使機器能夠自動地執行人類勞動的動作和姿勢。人類則在流水線上執行著程序化的、單一的動作和姿勢,他們相對于機器這種工具持有者,也只是成了機器環境中另一種早晚會被取代的技術元素。人類雖然沒有被異化,但人類已經不具備“怎樣去做”的知識,人類在廣義器官系統的地位被貶低了。而且,隨著自動化程度的逐步升高,人類的地位會不斷降低,人類所具有的知識也會不斷被自動化剝奪去。3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1: The Future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50.但并不意味著,人類最終會被驅逐出廣義器官系統。人類軀體是不可能被驅逐出去的。一種沒有人類存在的、完全自動化的未來技術世界是不可被想象的,也是無意義的。
不過,自動化過程仍然會繼續。一旦人類軀體內器官所有的知識都被軀體外器官所剝奪,人類就會成為徹底的無知者(generalized proletariat),會成為廣義器官系統中僅提供數據蹤跡和消費需求的高級電池。人類將既不是這個系統的動力,也不再是這個系統的目的。因此,對于斯蒂格勒而言,第一種完全意義上的機器的出現,標志著工業革命的開始。“從工業革命,即器官學的工業化以來,當代器官學系統上大規模的毒性(熵)顯現了出來。”4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 35.這樣一來,“工業革命既是一場器官學革命的開端,也是人類世的開端。”5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p. 38-39.
三、人類世的演進及其當前狀況
斯蒂格勒認為,“知識是一種開放的系統:它總是包含著能夠生產負熵的去自動化的能力。”6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p. 51-52.“ 各種形式的知識,就是定義人類諸種生存領域中所存在的負熵的方式。”7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 54.然而,“19世紀,生產負熵和知識的手工勞動被無知化的雇傭所取代,即被無知者所取代。無知者被迫服從生產熵的機器,這不僅是因為機器燃燒礦物燃料,也是因為機器標準化的運行流程,導致了雇傭者知識的喪失。”8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 52.機器對人類“怎樣去做”的知識的剝奪是對人類身體器官的去功能化,然而,機器卻沒有使身體器官再功能化,它只是讓身體執行著程序化的、單一的動作和姿勢。這意味著,人類身體器官在與機器這種技術器官互動的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它們之間的亞穩定平衡被打破了。勞動者既然不再具有“怎樣去做”的知識,就無法再繼續生產負熵。人類世中的熵隨著機器的大規模使用而大規模增加。
不過,19世紀的機器生產的自動化程度畢竟還比較低,它還無法將人類身體器官完全驅逐出廣義器官系統。人類雖然成了不知道“怎樣去做”的無知者,但人類的身體器官還能夠在流水線上執行某些動作和姿勢。但隨著機器自動化程度的提高,機器取代人工的狀況會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不僅一些舊的流水線作業的工人逐漸地被機器所取代,而且現在一些新的崗位,自其誕生之始就已經完全自動化——它們在誕生之前,就已經具備了完全取代人工的條件。甚至,機器也會原創出在人類身體勞動中不存在的動作和姿勢。這時,人類身體的動作和姿勢的介入,可能會使機器無法正常作業。人類在這些機器面前成了完全不知道該“怎樣去做”的無知者。
嚴重的無知化程度仍然會繼續加深,人類世中的熵也會繼續增長。機器所剝奪的只是身體器官所具有的知識,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廣義器官系統中有心理器官的存在,它也具有知識,甚至可以說是更重要的知識。斯蒂格勒將知識分為三類:“怎樣去做”的知識,“怎樣去生活”(how to live)的知識,以及“怎樣去思考”(how to think)的知識。1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1: The Future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9.機器能夠剝奪第一類知識,因為它們屬于身體器官,但它不能夠剝奪后兩類知識。后兩類知識是人類心理器官所具有的知識,是心理器官產生負熵的能力。不過,由機器的出現所開啟的自動化趨勢仍在繼續,這也就意味著,后兩類知識早晚會被新的技術器官剝奪而變得自動化。對應于身體器官和心理器官這兩類軀體內器官,我們將自動化也分為兩類:動作和姿勢的自動化;欲望與理性的自動化。機器引發了動作和姿勢的自動化,大數據和算法等數字技術則可以引發欲望和理性的自動化。
在斯蒂格勒的哲學理論中,欲望一直具有積極的面相。“欲望作為一個客體并不存在,但欲望能夠作為理想化投射的支撐而被理想化。”2Bernard Stiegler, Ben Roberts, Jeremy Gilbert, et al.,Bernard Stiegler: A Rational Theory of Miracles: on Pharmacology and Transindividuation, New Formations, vol. 77, no. 1, 2012, p.182.正是這種意義上的欲望使人們的生活產生意義,使人們對生活擁有積極的追求。它是人們對未來的某種美好的或者充滿抱負的預期,或者說是人們對某種振奮人心的事件之必然會發生的信仰。欲望因此就是“怎樣去生活”的知識。“欲望的對象本質上也是一個不可計算的事物,它超越了一切計算。就因為它不可計算,所以我們才渴望它。”3斯蒂格勒:《手和腳:關于人類及其長大的欲望》,張洋譯,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78頁。然而,數字技術使得欲望也變得可以計算了。數字技術以數字標準對視覺、聽覺等感覺進行離散化,并模擬這些感覺形成視聽影像等數字虛擬對象和滿足這些感覺的商品,以刺激人們真實的感覺。數字技術培養出了心理器官對數字虛擬對象上癮的記憶和習慣,欲望對象之不可計算的理想性被數字虛擬對象之可計算的理想性所取代。人們執著于現代感十足的數碼產品,執著于五光十色、眼花繚亂的電影視覺盛宴,執著于受人矚目、光鮮亮麗的生活方式。人們把這種由數字技術所模擬和催生出來的對象當成自己理想化的欲望對象,每當全新的數字虛擬對象出現之時,便自動地認為只要獲得了它便獲得了真正的生活。實際上,數字技術破壞了欲望,剝奪了心理器官中“怎樣去生活”的知識,使人們的生活被數字技術自動化了。離開了數字技術,他們既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也不知道該怎樣生活,他們成了一個短視的、盲目的消費者,成了不知道“怎樣去生活”的無知者。
數字技術不僅能夠剝奪心理器官中“怎樣去生活”的知識,使人們的欲望變得自動化,而且可以剝奪心理器官中“怎樣去思考”的知識,使人類的理性變得自動化。根據斯蒂格勒的廣義器官學,理性是一種器官,它能夠產生“怎樣去思考”的知識。1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 238.“ 所有的思考都是通過實踐而去清除自動化的能力”,2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1: The Future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72.這種能力是產生負熵的能力。理性會使個體變得明智,有自己獨立的判斷,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如果欲望的對象在本質上是不可計算的,那么,“理性的功能就是去保護不可計算的東西”,3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 209.即去保護欲望的對象。可是數字技術形成的數字網絡把萬事萬物放置在同一平臺,“它基于個人數據、網絡個人臨時資料(cookies)、元數據(metadata)、標簽和其他跟蹤(tracking)技術的蹤跡,建立起‘算法治理術’(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4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1: The Future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19.這種治理術依賴于人們在數字網絡中留下的蹤跡,使用算法對這些蹤跡進行分析:它會給人們分類,為他們打上標簽,能夠分析出具有某種標簽的人何時處于活躍期、何時購買什么東西、何時處于什么情緒狀態中。進而根據算法所得出的結論,在大腦做出理性的判斷或決定之前,自動地給出推薦的建議和方案。算法治理術使理性全天候地處在它的引導和監管下,它“減少了大腦做決定的時間,并進而清除了大腦反思和沉思的無用時間”。5Jonathan Crary,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London: Verso, 2013, p. 40.然而,算法治理術只給出結果,這意味著它將人們的理性思考能力排除出作判斷的過程,大腦的思考過程被排除了,理性的官能也被短路了。于是,“在21世紀,理性已經變成了算法的計算”。6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 267.算法治理術這種數字技術就剝奪了心理器官“怎樣去思考”的知識,人們成了懶得去思考和不知道“怎樣去思考”的無知者。“數字自動化短路了理性的功能,而造成了系統性的愚蠢。”7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1: The Future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25.
由于知識的自動化是從工業革命開始的,而工業革命又是人類世的開端。因此,整個人類世就是,軀體內器官中的知識逐漸被軀體外器官所接管并變得自動化的過程。“由于數字技術使得整體的自動化成為可能”,8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1: The Future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25.“ 今天所有的人類知識都被整合進單一的數字技術系統中了”。9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2: The Catastrophe of the Sensibl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p. 136.而由于“總體的自動化就是總體的無知化”,10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 18.人類的身體器官和心理器官所具有的知識既然已經完全被剝奪,那么,人類就成了徹底的無知者。斯蒂格勒認為,廣義器官系統中自動化程度的增加就是熵的增加,因而“目前的人類世已經達到其極限:人類世進入了其最終的狀態”。11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p. 209.
四、克服人類世的可能性
人類世的最終狀態意味著,人類世中因機器和數字技術的全面應用而產生的毒性已達到最大值。那么,在人類世的這個狀態中存在不存在克服人類世的可能性?對于海德格爾而言,或許不存在這種可能性。斯蒂格勒認為,海德格爾所思考的“座架”(Gestell)就是他所思考的“人類世”。數字技術把全球范圍內的自然數據、政治數據、經濟數據聯結成了數字網絡,使數字自動化在全球范圍內鋪展成為可能。于是,海德格爾所說的全世界范圍內的技術座架產生了。“海德格爾早期的《存在與時間》還在討論如何去占有技術,但是20年代以后他……開始拒斥整個技術和現代文明。”1張一兵、斯蒂格勒、楊喬喻:《人類紀的“熵”“負熵”和“熵增”——張一兵對話貝爾納·斯蒂格勒》,《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3期,第6頁。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在技術座架之中存在著克服此種座架的可能性,即在人類世之中存在著克服人類世的可能性。但是,對于一種廣義器官學來說,卻存在著這種可能性。
廣義器官學是對軀體內器官和軀體外器官之間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的互動關系的研究。無論是機器作為新的技術個體對人類這種舊的技術個體的取代,還是數字技術對心理器官所具有的知識的剝離,都是對軀體內器官的去功能化過程。但是,自人類世開始以來,由機器所開啟的自動化趨勢一直都只是對軀體內器官去功能化,而沒有對其進行再功能化。這導致的結果便是,人類既不具有“怎樣去做”的知識,也不具有“怎樣去生活”和“怎樣去思考”的知識,人類成了徹底的無知者。然而,既然人類之為人類本質上是由軀體內器官和軀體外器官這兩種器官系統構成的,那么,自動化過程就不可能將人類的這兩種器官系統完全剝離開來。人類世的毒性目前雖然已經達到最大值,但這也正意味著,對軀體內器官的進行再功能化的契機已經到來。然而,要開啟這種再功能化的過程并非被動地等待就可以了。機器和數字技術對人的勞動技能、生活方式和理性判斷等知識的剝奪,會使人變成感覺自身無用、對生活冷漠、缺乏智慧的無知者。要對抗人類世的毒性,人們必須主動地去恢復對知識的激情。“只有對知識充滿著激情,人類才是有知識的存在者。……知識不會令人冷漠,知識會感染人:知識不是無趣的。”2Bernard Stiegler, Philosophising by Accid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63.人們必須重新成為有知者,必須主動地在與機器和數字技術的互動中形成新的負熵性的知識,以對抗自動化社會的熵增。斯蒂格勒給出的建議是:人們要主動地使用身體器官進行體力勞動,最好掌握一門勞動技能;人們要學會放棄對消費市場上那些像病毒一樣到處傳染的消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依賴,要學會拋棄那些虛假的欲望;人們應該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做判斷,去反思整個人類世時代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而不是僅僅依靠機器和數字技術自動化地推薦的建議和方案。總之,就是人類作為知識主體要重新恢復對技術器官這種知識客體的激情。
“人類世是熵大規模生成的時代,它是虛無主義在事實上的完成。”3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2018, p. 238.而完成的虛無主義正是指,對時代未來的積極期望消失了,整個社會中表現出一種急功近利、大肆浪費而不考慮未來之可持續發展的虛無主義。這一狀況是機器和數字技術帶來的總體無知化所導致的集體精神器官被短路的表現。如果對虛無主義不加以遏制,它所產生的破壞效果可能會更嚴重。在某種程度上,斯蒂格勒所說的對人類世的克服就是指對這種急功近利的虛無主義的克服。為了對抗虛無主義的人類世,必須要從人類世當中構想出一種克服人類世的可能性。斯蒂格勒稱這種可能性為“負人類世”(neganthropocene)。4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2018, pp. 44-45.這種負人類世能夠再次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出終極的目的和意義,使生活在這一時代的人能夠去考慮后面幾代人的未來長期發展,而不只是為眼前當下的利益破壞長期利益和未來的可能性。斯蒂格勒的人類世思想表達了他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懷以及對科技高速發展的當今時代的深深憂慮。這也表明,斯蒂格勒本人是一位有著時代憂患意識和人類命運責任感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