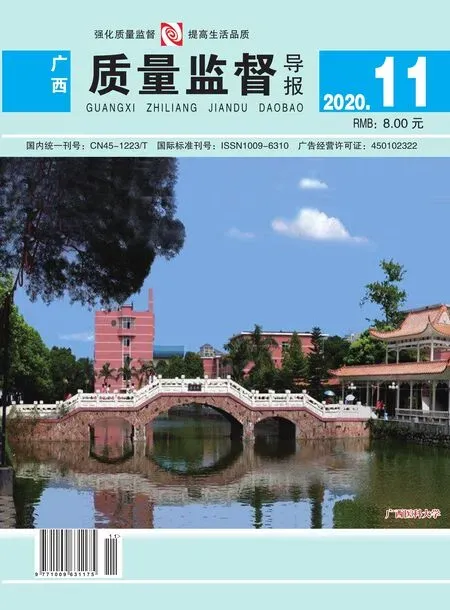勞動規章制度效力原則分析
徐丹萌
(廣東財經大學 廣東 廣州 510320)
勞動規章制度是世界各國勞動立法所關注的重點,也是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工作行為進行管理約束的重要方法。隨著相關立法逐漸完善,用人單位利用勞動規章制度規避法律責任的現象屢見不鮮,勞動規章制度漸漸成為用人單位、勞動者、勞動立法這三者之間進行力量博弈的焦點。具體體現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勞動糾紛案件里出現針對勞動規章制度的爭議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如何正確處理此類爭議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關鍵。
關于勞動規章制度的效力適用問題,雖然法律上規定了關于勞動規章制度生效的實體要件與形式要件,但司法實踐中依舊存在許多勞動規章的適用爭議,裁判機關在處理勞動爭議案件時,常常需要對用人單位的勞動規章制度的內容進行審查,不僅僅是單純地依照法律規定審查勞動規章制度的合法性,更要站在保護勞動者弱勢地位這一立場上,審查勞動規章制度是否合理,用人單位能否憑借該規章條文對勞動者進行規范甚至是解除勞動關系,裁判者應從不同角度認定勞動規章制度的有效性,只有當勞動規章制度同時滿足合法與合理兩個要求時,才能用于規范勞動者的行為,因此有必要建立勞動規章制度之效力原則,以供司法審查,如此既能保護勞動者權益、又能防止用人單位懲罰權與解雇權的濫用。用人單位勞動規章制度的效力原則主要有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和除外原則,下文將針對這三個原則進行進一步討論。
一、明確性原則
明確性原則是指勞動規章制度應當是具體且明確的規定,不應該含有抽象性、概括性的內容,理由在于用人單位在依據勞動規章處罰勞動者時,必須要有書面且明確的理由,如果僅依據高度概括的勞動規章條款對勞動者行使懲戒權,不免存在用人單位任意解釋勞動規章內容,濫用懲戒權的嫌疑,并且抽象程度高的倡導型條款難以預見,束縛了勞動者的行為,間接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因此,明確而具體的勞動規章制度才能作為用人單位懲戒勞動者的有效依據。
明確性原則考慮到勞動者天然的弱勢地位,主張用人單位不得隨意以勞動規章制度為依據懲戒勞動者,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是否能作為勞動規章制度的效力審查標準則有待商榷。
(一)明確性原則不符合國際通行的相關法理
該想法最初源于19世紀興起的“解雇自由說”,該學說從提高生產效率、追求經濟效益的角度出發,認為應當賦予用人單位充分的自由解雇的權利,認為用人單位根據自制的勞動規章制度決定是否與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屬于用人單位的自主經營權的范圍,考慮到經濟發展效率問題,法律不應過多地干涉其自主經營活動。由于懲戒與解雇實際上是用人單位用工自主權與自主經營管理權的具體化,“明確性原則”過分限制用人單位的這兩項權利會導致用工機制僵化,因此,許多國家在立法上并不要求雇主在解雇職員時必須給出“具體且詳盡”的理由,我國也有學者贊同此觀念。關于用人單位解雇勞動者的理由,許多國家在立法上不作較為詳細的列舉式規定,只作一般性與原則性的規定。在實踐中,則由裁判人員對具體的解雇理由進行解釋與定性。[1]
根據《瑞士債法典》中關于雇主解除勞動合同的規定,雇主在解雇雇員時只需要給出正當的理由即可解除雙方之間的勞動關系,無需過多的解釋與理由。至于其給出的解雇理由是否正當,應當由法官根據誠信原則進行“自由判定”,即使是雇主與雇員已經事先對正當解雇理由進行了約定,法官依然可以對該理由進行自由判定。[2]法國勞動法也是一樣:不論是勞動合同,還是集體合同,或者是企業勞動規章都不得事先規定勞動者的何種過錯構成解雇理由之“嚴重過錯”;另外,即使有這樣的規定,也不能約束法官對解雇理由的判定。這樣的制度設計既充分考慮了企業的用工自主權,又能保障勞動者避免不公平的處分。
(二)明確性原則與我國勞動法規定相矛盾
在立法方面,考慮到用人單位自主管理與經營的性質,我國《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都未對勞動規章制度的形式要件進行過分嚴苛的限制,因此采用書面形式并非制定勞動規章制度的必然要求。對此,學界有關于“勞動規章制度的內容包含了勞動者應當遵守的法定的默示義務”的觀點。比如我國的《勞動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了“勞動者應當遵守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這就是勞動者的隱含義務之一,屬于勞動者忠誠義務的范疇。因此,即便勞動規章制度中的一些內容并沒有以書面形式表現出來,只要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就該條款內容達成合意,沒有其他違反法律法規的情況,該條款就是合法正當的,就可以成為解決勞動爭議的有效依據。[3]但是,口頭形式的勞動規章制度,并不符合“明確”這一要求。
綜合以上兩種原因,勞動規章制度并不一定要求具有明確且具體的規定,“明確性”不能作為評價勞動規章制度的硬性標準。
二、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又稱謙抑性原則,主要體現在用人單位在制定勞動規章制度中的懲戒規則時,應考量勞動者違規違紀程度的輕重或次數的多寡等情節,而分別予以適當的處罰,如果采取較輕的懲罰措施就能夠達到應有的處罰效果,維護正常的經營管理秩序,就不應該適用更重的懲處措施。究其原因,主要是勞動權是憲法性基本權利,直接關系到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情況。因此除卻嚴重的情況,勞動合同不能任意解除。[4]
比例原則應當作為判斷評價勞動規章制度的基本原則,域外許多國家的勞動法都體現了比例原則,值得我國借鑒。
(一)法國勞動法
法國勞動法規定“雇主進行解雇時給出的理由應當具有嚴肅性”,根據司法案例,在因雇員過錯導致被解雇的案例中,將雇員的過錯程度分為四個層次:輕微過錯、嚴肅過錯、嚴重過錯和重大過錯。只有當勞動者的工作行為存在嚴重過錯或重大過錯的情形時,才能啟動“解除勞動合同”的措施。任何勞動合同的合法解除都應當有“實際的、嚴重的”原因,是否嚴重只能由法官而不是用人單位來判斷。若勞動者的過錯程度僅為“輕微”,則不能解除合同,只有當雇員的行為屬于“嚴重過錯”或“重大過錯”時,才可以作為辭退的合法理由。[5]
(二)德國勞動法
德國法律規定,如果解雇雇員是基于其多次失職行為,原則上有必要對該雇員進行事前的警告。換言之,用人單位必須向員工明確表示,如果員工一再或持續失職,將會對其予以解雇。[6]由此可見,在德國相關立法方面,用人單位立即解雇也應當遵循合理的比例,不會僅因一次的、偶發的違規行為,就解除雙方之間的勞動關系。這也是我國根據勞動法規解除勞動合同時應特別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說,不能因為一次偶然性的違規行為而加重處罰,甚至解除勞動合同,這也體現了違反勞動規章制度之懲戒權的比例原則要求。
概言之,比例原則是對用人單位用工自主權的合理限制,即便根據勞動規章制度,勞動者存在嚴重違紀的行為,用人單位的懲戒權的實際運行應經受“比例原則”的檢驗,裁判機關在處理相關糾紛案件時,應秉持“比例原則”的精神內涵,綜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來判斷“勞動者是否嚴重違反了勞動規章制度”,不僅僅只局限于勞動規章制度的書面條款與用人單位的經濟利益損失,也應盡可能多地將勞動者違紀頻率、工作性質、用人單位過錯、社會影響程度、群體接受度等因素考慮進來。
三、除外原則
在適用勞動規章制度時,要特別注意針對違規違紀行為的懲戒權的排除范圍或對象,勞動規章制度其內容應當規避的情況有二:一是勞動者的非職業行為,即勞動規章制度不能將勞動者的私人行為納入懲戒權的適用范圍,也即違規違紀懲戒權之豁免制度;二是職工社會保障問題,不能將其納入違紀處分權的范圍。
(一)勞動者非職業行為即私人行為不能適用勞動規章制度
正如法律不能過度干涉用人單位的用工自主權,勞動規章制度也不能過度干涉勞動者的日常行為,即“非職業行為”,將“非職業行為”排除也是為了防止用人單位為維護自身利益,制定明顯不公平的規章制度以限制勞動者的正常活動,侵犯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如工廠員工下班途中騎電動車、自行車可能會導致工傷賠償率提高,若企業為了躲避承擔工傷賠償的責任,在勞動規章制度中規定員工不得乘坐非機動車上下班,這種行為就是利用勞動規章制度的制定權限,將勞動者的與工作無關的生活行為進行了不合理不恰當的限制,顯然不能用于規范勞動者的行為。
對于勞動者的非職業行為,內部勞動規章制度不能涉及勞動者的私人空間,這已經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例如,根據意大利勞動法,一般認為勞動者私生活的事實原則上無關緊要,除非這些事實直接影響雇員的職業能力,給用人單位接下來的經營管理造成不良影響,例如銀行雇員的盜竊。[7]而我國有關勞動規章制度或勞動紀律的立法都缺乏針對“非職業行為”的明確規定,可以借鑒俄羅斯的做法,在法律中明確規定非職業行為之解雇的限制適用條件。
(二)勞動者之社會保障權不能適用勞動規章制度
用人單位行使處罰勞動者違紀行為的權利,不應觸及到勞動者的基本社會保障,這是勞動規章制度效力排除原則的第二大內容。社會保障權是公民的基本人權。無論勞動者是否違反勞動規章制度或者用人單位的紀律,勞動者應當享有的基本社會保險權和社會保障權都不能排除在外。
從一般法理上來看,勞動規章制度含勞動紀律一般被認為是屬于用人單位的意識自治或“私法公法化”的范疇,但其部分自主經營與管理權不能夠完全意思自治,還要受到公權力的審查與監督,用人單位權力的行使不能損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否則將是違法無效的處罰,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應由用人單位承擔。根據我國勞動法的規定,為勞動者辦理社會保險是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具有公法上的強制性,不能為用人單位的自主意識所左右,用人單位亦不得隨意減免其法定義務。
從主要內容看,《勞動法》明確規定,只有當勞動者“嚴重”違紀時,用人單位才能解除勞動合同。此時,勞動關系的合法終止必然導致用人單位履行其法定社會保險繳費義務的終止。但是,這并不一定導致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權的完全喪失。被辭退的勞動者依舊可以從國家或者社會層面獲得相應的物質幫助,辭退前已繳納社會保險費的勞動者應當享受的社會保險待遇仍可以享受。勞動者社會保險待遇的終止并不等同于社會保障權的完全喪失,[8]勞動規章制度不能隨意剝奪勞動者這一部分的權益。
勞動規章制度的效力問題具有較強的爭議性,針對其深層次的理論研究還存在諸多不足,立法方面也存在相應的缺失,這使得勞動規章制度的適用更加具有討論性與研究價值。而勞動規章制度的效力原則就像司法審查時的工具,能夠在裁判機關處理相關案件時,得以較為清晰明確的審查方向,在效力原則的指引下,公正公平地判斷勞動規章制度是否符合合法兼合理的要求,勞動者的職務行為是否應當受其約束。通過對上述關于勞動規章制度效力原則的分析與討論,可知明確性原則由于不符合相關法理以及我國勞動立法,不宜作為勞動規章制度的司法審查標準,比例原則與除外原則具有平衡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利益、保護勞動者弱勢地位、限制用人單位懲罰、解雇權的功能,值得我國引入或借鑒相關的立法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