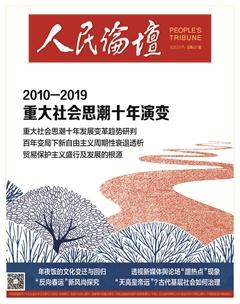“反向春運”新風尚探究
魏傳光

【關鍵詞】“反向春運”? 社會變遷? 新風尚? ? 【中圖分類號】D669? ? 【文獻標識碼】A
每年臨近春節,“春運”都會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經過民工潮、學生流、旅游熱等三波推進,“春運”越發成為顯示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現象級概念。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社會進入現代性轉型時期,高速發展的經濟、不斷變遷的社會結構、快速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在春運中得到顯現。被稱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人類遷徙”和“如史詩一般的人口遷徙”的春運,成為多年來困擾整個社會和考驗我國運輸系統的周期性大問題。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進步,春運敘事悄然發生著變化,充滿嘈雜聲和混亂無序的春運現象少了,通過高鐵、航空和自駕等多種方式回家的故事多了。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反向春運”現象開始凸顯,儼然成為一股潮流。據統計,2019年從農村和城鎮到京滬穗深等大型城市過春節的人數增加了兩倍以上,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不再是大家想象中的“春節空城”,全國鐵路春運傳統高峰路線的反向客流增加近9%左右,高于總體增速。
2020年春運,預計全國旅客發送量將突破30億人次。據高德地圖發布的《2020年度春運出行預測報告》顯示,2020年春運高速擁堵程度或為近三年來峰值,而反向春運的持續增長也將成為今年春運出行趨勢中的一大特色。可以說,“反向春運”正在成為現代意義的一種春運形態,成為不少“80后”“90后”陪父母過年的新方式,成為人們過年團聚的新形式和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
多種因素催生了“反向春運”
相比外出務工人員年前返鄉過年、年后回城務工的傳統春運,“反向春運”主要指年前從鄉到城、從小城鎮到大城市方向的新型春運。如果說傳統春運主要是民工流、學生流、探親流的“三流合一”,是在城務工、在城學習的青年人回老家過年、品味鄉愁,看望親人,感受家鄉變化,那么“反向春運”更多是指年輕人將農村或城鎮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到大城市過春節或旅游。更通俗地講,“反向春運”就是和以往年輕人回家過年相反,由老人或孩子提前到子女或父母工作地過年的社會現象。這是大城市近年流行起來的過年“新常態”。
“反向春運”的出現,有多方面的原因。客觀上,與春運運輸資源倒掛有關,反映了民眾對傳統春運瞬時集中的出行需求與運力相對不足之間的基本矛盾開始自覺調整。出于一票難求,回鄉路途擁堵,以及經濟上考量等因素,一些人開始反其道而行之,尋找既能照顧工作、消減旅途疲乏,也能和家人過年團聚的替代方式。另外,家庭結構變遷也是重要原因。“80后”“90后”已成長為職場主力軍,并在城市安家樂業,成為家庭的核心,在這種情況下,父母隨在外子女同住的情況越來越多。在核心家庭逐漸成為主流,而主干家庭和家族逐漸趨弱的情況下,如果年輕一代忙于工作沒時間回家過年,他們的父母往往遵循“小家”之所在,即“大家”之所依的觀念,選擇去子女所在的城市過年和旅游,團圓之余,也可以感受子女的生活。所以在“反向過年”的購票群體中,“85后”的占比超過了60%。他們把父母接到城市過年,感受不一樣的春節,成為表達孝心的重要方式。
“反向春運”的出現也與社會變遷下人們過年觀念的轉變有關。社會變遷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斷重塑和更新人們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一是故土難離的觀念逐漸淡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社會流動的加速,鄉土情結漸漸弱化,返鄉過春節、借春節尋根的觀念逐漸淡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只要家人聚在一起,在哪里過都是團圓年,所以在工作的城市“闔家團圓”,成為了人們逐漸認同的生活方式。不少老人選擇了在春運開始前“反向探親”,去子女家里過年,既避開繁忙的春運,也省去子女往來奔波。二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旅行”取代傳統意義上的“團聚”成為新時尚。三是隨著鄉村過大年的氣息越來越寡淡,不少人感慨即使回老家過春節,也找不到童年的感覺,難以滿足鄉土情結。再加上回家過年人情負擔過重,尤其是一些農民工難以承受春節回家人情往來上的經濟支出,導致弱化了家鄉認同,疏離了血緣之間的親情關系。種種因素下人們回老家過年的愿望也沒有以往那么強烈了。
“反向春運”具有正向意義
從根本上講,“反向春運”具有歷史進步意義。過去外來務工人員之所以認為春節一定要回老家,除了傳統觀念的原因之外,其實還有現實性考量:對于很多外來務工人員來說,務工的城市并不是他們認同的“家”,對工作城市還沒有融入感和歸屬感。這些年,隨著城鄉二元鴻溝的逐漸填平、城市化的推進,以及便捷的交通等極大縮短了城鄉之間的時空距離,讓“流動的中國”邁出更輕松的步伐。再加上城市良好的生活、教育、醫療等環境也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到城市定居。可以說,戶籍改革、住房改革等政策的疊加效應,使得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落戶城市。那些有能力接父母進城過年的人員開始考慮把親人接到城市來過節,于是“反向春運”逐漸流行。總體而言,無論對于緩解交通壓力、保持城市正常運行,還是對于留城人員及其家人來說,“反向春運”都具有正向意義。
毫無疑問,“反向春運”對于緩解交通部門的春運壓力,平衡交通運力,填補閑置運力資源具有重要意義。破解春運難題,無非一靠“減流”,二靠“增運”,“減流”不是限制流動,而是指減少春運需求,幫助外來務工人員融入城市生活,選擇在城市過春節。面對每年一度的“人口遷徙”運動,航空、公路、鐵路、水運等部門每年擔負“載之不盡”的出行需求。春運運力供給存在結構性困境,“反向春運”是減輕運輸壓力,使運輸工具發揮最大化效用的良方。另外,受國家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因素影響,春運的最大特點是單向流動,尤其是“北上廣”地區基本上都是單向客流,年前回鄉運輸緊張,去程人滿為患,但返城運力閑置,人流稀少、寥寥無幾。年后則完全相反,返城運輸緊張,但回鄉動力閑置,這造成春運期間的鐵路產能一半是浪費的。據統計,春運期間的單向客車實際上座率不足30%。而“反向春運”可以有效減少運輸壓力和增加上座率,緩解集中返鄉的壓力,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春節期間被閑置的資源,均衡配置運力,實現利潤增長。
“反向春運”對于維持城市在春節期間的正常運營也意義重大。每逢春節一線城市就會出現季節性缺工,服務行業的工作者大量返鄉影響了城市的正常運轉和居民生活。這主要是由于當前大城市的餐飲、收銀、家政服務等傳統服務業和外賣、快遞、網購等新興服務業的崗位大多數是由外來務工人員承擔,而這些領域對城市居民的生活越來越重要。外來務工人員留城過年,有利于緩解春節期間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保障春節期間服務的正常供應和城市生產與生活的正常運行。另外,“反向春運”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春節期間的閑置資源,刺激大城市餐飲、娛樂、購物等旅游相關行業的消費。據統計,2018 年“反向過年”的人群為餐飲、娛樂、購物消費帶來的提升同比增長近 100%。
“反向春運”就個體而言也益處良多。把父母和孩子接到城市過春節,實現“反向團圓”是一種方便實惠的選擇。首先反向躲開了春運交通的高峰,不必把時間精力用在搶票上,也不必面對回家途中擁擠不堪的車廂,同時能降低出行成本,讓家人體會到自己所在城市的風光,紓解歸鄉的資源焦慮,延長團聚的幸福時光。可以說,不管從出行成本還是回家花費來看,不管是從時間還是過年樂趣審視,“反向春運”無疑都是一種更為經濟的“團圓”。
合力推進“反向春運”
鑒于“反向春運”帶來的多贏效應,有必要加以因勢利導,讓“反向春運”成為趨勢和潮流,釋放出更大的正能量。但“反向春運”是個復雜的社會概念,它具有政治性、經濟性、社會性等多重屬性,推進“反向春運”僅僅依靠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各方力量都應該及時關切“反向春運”新風尚,出臺鼓勵性精準政策,提供便利性條件,從各方面、各階層協同推進。
首先,鼓勵“反向春運”要寫入春運工作指導意見,正式進入有關部門的決策視野。交通運輸部門可成為“反向春運”的推動者,尤其是推行回空方向列車票價優惠措施。如果從鄉鎮到城市方向的列車票價便宜,對于外來務工人員無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與票價優惠的實際價值相比,鼓勵“反向春運”的導向價值更為重要,因此公路、鐵路、水運、民航都應積極推出優惠政策,在運用價格杠桿盤活運力資源的同時,提高反向團圓的性價比,讓利于民。這樣可以向社會傳遞出積極信號,引導個體與社會同頻共振,共同解決春運難題。
當然,鼓勵“反向春運”不應是交通運輸部門的獨角戲,還需要有關部門和全社會形成合力。例如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從根本上打破制度壁壘,創造條件讓外來務工人員在享受戶籍平等的同時,能與城市居民一樣擁有同等的教育、衛生、社保待遇和獲取社會資源的平等機會。文化部門可精心準備文化大餐,發放各種旅游“禮包”,讓“反向春運”一族不虛此行。旅游管理部門可面向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家屬免費或優惠開放公共文化設施和旅游景點。城市社區可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和聯歡活動,提高娛樂性、群眾性、參與性,使來到城里過年的老人和兒童能夠樂在其中。
更為重要的是,大城市的管理者在吸引外來人口的同時,還應通過完善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福利的措施留住人,使人安心。如果外來務工人員真正融入這座城市,將之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反向過年就會成為一種常態。所以,管理部門要通過切實有效措施增強外來人口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讓外來人口不僅成為城市的建設者和守護者,同時也能產生“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感受。一些企業也可出臺“反向春運”的鼓勵措施,諸如鼓勵員工的配偶、孩子來企業所在地過年,為員工家屬報銷路費、組織游覽活動等。
不可否認,多數中國人都有著揮之不去的鄉愁情結和“愛家、愛鄉、愛故土”的思鄉情懷,春節回家相當于一種“剛需”。但在文化導向上不宜過多宣傳過年回家就是“盡孝不忘本”,不回家過年就是“沒心沒肺”,反而應該加大宣傳“在春運中有一種逆行,叫進城過年”的理念。當然還可通過彈性的假日經濟舉措,鼓勵人們在出行時間的選擇與方式上盡可能的分散化、多元化,滿足人們闔家團圓、其樂融融的內心情感需要,而不是鼓勵外來務工人員在春節期間一次完成拜年、祭祖、訪友等系列活動。其實,思鄉戀家的情感可以通過中秋節、清明節、重陽節等節日的情感分流來疏導。總體而言,通過反向團圓的方式疏解客流的措施,雖然還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春運的格局,但畢竟是緩解春運壓力的一種新方式。
【注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廣東率先實現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化的實證研究”(項目編號:GD17CMK0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陳友華、苗國:《春運難題的建構與消解》,《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
②董才生、陳氚:《春運問題的人口社會學分析》,《人口學刊》,2008年第1期。
責編/常妍? ?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