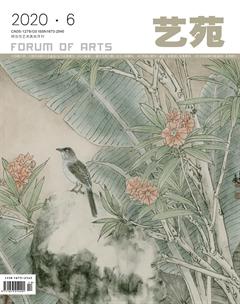傳統京劇的現代表現

【摘要】 王安祈是臺灣“京劇新美學”的代表人物,她以女性形象的重探為導引,致力于對傳統京劇進行現代化、文學化的開掘和重現,為京劇的傳承與創新開辟了一番新天地。其所編創的《青冢前的對話》,以女性視角多維審視女性,突破傳統觀念的劇本格調,延續傳統的表演體系,聚焦于古典與現代舞臺藝術的交融,以小劇場的形式顛覆性地展示了傳統京劇的現代樣態,創作出符合現代文化思潮的新編京劇。
【關鍵詞】 王安祈;《青冢前的對話》;傳統;現代;新編京劇
[中圖分類號]J82 [文獻標識碼]A
戲曲危機已經存在很多年,傳統京劇在現代文化的沖擊下,主體地位受到撼動,針對此,如何實現戲曲的現代化發展?如何在已有的戲曲傳統上進行別樣創新?如何破解傳統戲曲與現代文化的二元對立?如何建立一種符合現代思潮的表達方式?這些是長久以來不少戲曲家探索追問的問題。
著名戲曲家王安祈,祖籍浙江吳興,曾任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2002年擔任臺灣國光劇團藝術總監,代表作有《新陸文龍》(1985)、《淝水之戰》(1986)、《通濟橋》(1987)、《袁崇煥》(1990);與雅音小集合作創作《劉蘭芝與焦仲卿》(1985)、《再生緣》(1986)、《孔雀膽》(1988)、《紅綾恨》(1989)、《問天》(1990)、《瀟湘秋夜雨》(1991);還有《王有道休妻》(2004)、《三個人兒兩盞燈》(2005)、《金鎖記》(2006)、《青冢前的對話》(2007)、《歐蘭朵》(2009)、《孟小冬》(2010)、《畫魂》(2010)、《百年戲樓》(2011)、《水袖與胭脂》(2013)、《紅樓夢中人——探春》(2015)等等。王安祈對傳統京劇的改革、創新保持著高度的關切,其所在的臺灣國光劇團多年來一直推動京劇的現代化發展,致力于傳統京劇的自我變革,并以小劇場戲劇不斷對傳統進行探索和改造,尋求符合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念和心靈需求。在王安祈看來,追求現代化的方向是挑戰亦是創新,但絕非一味推翻傳統。因此傳統戲曲的現代化并不意味著摒棄傳統或者單純從戲曲的外部形式創新,而是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的創作,是一條“由內而外”的道路。《青冢前的對話》(以下簡稱《青冢》)的上演表現出傳統與現代戲曲創作模式的碰撞與交融,劇作家將《園林午夢》《昭君出塞》《文姬歸漢》這三部作品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全劇以傳統經典文本為基礎,以蔡文姬、王昭君跨時空的靈魂私語為創作中心點,解讀和重探兩位女子在同一語境下內心的情愫與思量。編劇在保留傳統表演藝術本質的同時,以實驗、顛覆的筆觸向我們展現現代女性的自由氣息和靈魂。因此筆者以《青冢》為“切入點”,試圖分析王安祈如何在傳統戲曲的基礎上創作符合現代文化思潮的新編京劇。
一、劇本文學的格調:打破傳統觀念的性別新圖景
王安祈女士在擔任臺灣國光劇團藝術總監之初,就有意避開家國政治的宏大敘事背景,以女性題材為主,貼近現代人物心理,展現女性內心情感的描摹與剖析。她曾提到傳統京劇:“不以劇本曲文為主要根據,而以唱念表演為關鍵載體,劇本對于女性幽深情緒的鉤掘,依舊付諸闕如。”[ 1 ] 4 8 1 - 5 0 2傳統戲曲的欣賞與觀看都是以唱念表演為主,京劇在形成的過程中更是建立起了形式大于內容的隱性規范,相較之下女性性格和氣質的刻畫相對簡單。比如《三娘教子》中的王春娥是一個受封建禮教文化熏陶的女性,遵守“三綱五常”,認為“三從四德”便是封建社會中女子最重要的美德。她守節不嫁,含辛茹苦養育其夫之子,世人皆感動于她的忠貞和偉大。對王三娘而言,是否保持貞潔專一、恪守婦道是衡量其善惡的標準,在此基礎上能犧牲自己、成全義子,她的形象就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類似的還有《武家坡》里的王寶釧、《御碑亭》里的孟月華等等。女性在愛情婚姻中無條件的付出和奉獻往往被視為一種美德,可她們自身特有的魅力與自我價值隨之被忽略。1950年大陸頒布戲曲改革政策后,在政治作用的推動下,女性從被壓迫、被束縛的封建倫理綱常中解放出來,創作的作品以反對封建傳統為主,女性形象的塑造直至當代逐步多元化。而當時的臺灣由于特殊的政治環境,只能上演傳統劇目和老戲,且帶有濃厚的政治宣教色彩,導致戲曲的創作和發展遠遠落后于大陸。至20世紀70年代末期,臺灣戲曲開始逐步探索和轉型,借鑒大陸戲曲改革的新編戲經驗,運用西方戲劇表演理論作為支撐,締造了當時臺灣戲曲文化的新風潮。直至21世紀,臺灣戲曲開始大踏步向前發展,他們以尋求“本土”為依據,著力探求傳統的現代化路徑以創造新的自我走向。編劇王安祈就是現代化拓新者之一,她非常偏重以現代意識挖掘文化意涵和哲理情思,不把人物當作簡單的“時代傳聲筒”,樹立女性主體的自我樣態,以女性編劇的情感角度打破傳統觀念上的性別話語權。因此劇本里女性幽微情愫的探索和自我重塑就變成了王安祈劇本文學中不斷拓展和創新的重要面向。
(一)解構古典傳統中的“他者”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 2 ] 8 1千百年來,以男性話語權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機制里,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還是在其他方面,男人是絕對的權威和中心,女性處于附庸和邊緣地位。而在男權制社會標準下的女性形象都是被形塑而成的產物,是為維護男性特權和政治利益目的下的另類書寫。傳統戲曲里的性別形象也是時代社會中在大眾性別認知的基礎上建構,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時代的性別圖景。在戲曲作品中,男性將自己定義為主體,女性成為附屬的“他者”。女性身份和地位的創造取決于父權制社會的文化語境,因而在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文化語境中女性塑造的形象氣質各不相同。我們所“熟知”的崔鶯鶯、李亞仙、王昭君、蔡文姬是古典傳統中的產物,是男權社會的“他者”,女性作為“主體”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是歷史中的“缺席”,她們沒有自己的“聲音”。盡管其中有些女性她們的身份位于上層,但實際上依舊處于被壓迫的地位。
王實甫筆下的崔鶯鶯,端莊美麗、溫柔賢淑,是身份高貴的相國小姐,不嫌張君瑞一介白衣秀士,突破封建傳統婚姻倫理觀念,追求自由的愛情婚戀,與張生修成正果。但是從結果來看她并沒有跳出男權對女性的束縛,而是從父權跳到了夫權的牢籠。李亞仙雖是個妓女,身份低微,但對鄭元和的愛情忠貞不二,即使其淪為乞丐也毫不嫌棄,可謂是至情至性。婚后也謹守婦道,相夫教子。由此可見,無論兩者地位或高或低,她們都是作為被男性觀賞、需要的完美女性客體而存在,除了愛情沒有其他的訴求和愿望,并且這種愛情幾乎等同于為男性無私付出和奉獻。崔鶯鶯和李亞仙在夫權的影子下,以“妻子”的身份逐漸湮沒了曾經擁有獨立意識和自立精神的自我。馬致遠《漢宮秋》中的昭君, 盡管內心有諸多不舍和無奈,仍大義凜然出塞和番,懷著對國家、對漢皇濃烈的情感投河自盡,以保清白貞節,她的事跡流芳百世,她的品德受人景仰,被后人稱為民族典范。蔡文姬留下了《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她自有彩筆繪身,但文姬書寫的詩篇都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嗎?她真能舍下辛辛苦苦懷胎十月的兒女嗎?她和胡人丈夫之間不存在鸞鳳和鳴的深情厚誼嗎?作為名門之后,她的一言一行都被關注和品評,內心遠離家人而不得見的苦楚只能獨自承受。可見以男權為主導的社會中,女性被歌頌的大多是犧牲和奉獻精神,作為生命存在的個體,她們合理的訴求和自我價值往往被忽略,這既是女性自覺的追求,也是封建社會普遍對女性的評價標準。編劇王安祈在作品中有意識的重新省思古代傳統女性的命運,顛覆和解構文學傳統,展現了女性受到的社會束縛,發出了在男權制話語體系下被遮蔽的另一番世界的景象,著力刻畫了王昭君和蔡文姬兩位女性角色的內心情感和幽微情愫,在某些方面傳達了男權社會主導下女性“失語”的困境。
(二)重塑現代文化中的“自我”
王安祈說:“‘京劇現代化(創新)的具體方向是:用傳統唱念身段表演藝術來體現新編劇本里的新情感、新人物,而女性內在的探索與女性形象的重塑,是臺灣京劇創新的重要表現。”[3]96-106那么如何在現代文化的語境下用女性話語重構“自我”?首先,《青冢》塑造的全部是女性角色,它把大眾所熟知的、相對固化的形象用“陌生化”的手法搬演上舞臺。作品中崔鶯鶯和李亞仙對話時的世俗、市儈讓人大吃一驚,她們不同于以往古典戲曲中塑造的端莊美麗、追求愛情的形象,被前人肯定的優點完全拋擲腦后,兩人互相用奚落的語氣你來我往地公開較量,比誰比較“高貴”,誰比較“堅貞”。并以男權社會的標準來戲謔地嘲弄對方。編劇撕掉了她們歷來的標簽,從兩人的爭吵中隱喻了男性視角下女性形象的矯飾性,也間接映射出歷史背景下的女性沒有自我言說和表達的權利。蔡文姬和王昭君的形象在此部作品中也有了新的解讀。歷史沿革下的兩位女性都是遠走故國他鄉,嫁到番邦和親,際遇坎坷,又飽受離亂之苦。離家時柔腸寸斷,歸國時亦是惆悵枉然,心中滿腔悲怨苦楚,只能深埋心底。《青冢》相較其他同時期戲曲劇作中的王昭君和蔡文姬形象別有不同的是:盡管命運不公,遭遇悲慘,但是她們活出了真實的自我,兩位女性內心深處都有渴求的愿景,便是在絕境中也要找尋自身價值,皈依本真。
另外,作品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她們的內心世界,注重情感表達和書寫,整部劇作滲透著女性“自我”言說和女性主體身份“自我”建構的意識。王昭君和蔡文姬兩個擁有相似悲劇命運的女人走到一起會碰撞出什么樣的火花?王安祈以其獨有的女性關照思索現代文化語境下女性的“自我”價值訴求。被世人稱贊的民族典范昭君有這么大義凜然嗎?她對漢皇真的有情嗎?她最后殉國了嗎?面對漢弱胡強、夫主婚、妻嫁人的屈辱和惆悵,面對生命的挫折、人生的悲苦,昭君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獨特的自我意識和人生樣態。背井離鄉,獨自一人承受巨大的苦楚,她心念的不是家國和愛情,唯一想做并且能做的就是儀式化的辭別漢家君臣,“豐容靚妝,登臨別殿”,憑借著嫣然美姿,在絕境中扳回一局,以慰藉她長期的愁情。面對自己的命運不斷被文人矯飾的苦悶,一句“豈能如人所愿”表達出自我見識。而文姬呢,遠離家鄉十二載,胡地已然成為她的另一個故鄉,她擁有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侶和家人,“靠著他的肩頭,我竟安然入睡”,這種簡單平凡的幸福何嘗不是文姬心之所向?因為是大儒之女,她不得不返回闊別已久的家鄉,繼承父親蔡邕未竟的事業,拋卻那“一茶一飯,一幾一座”的夫妻之情、天倫之樂。離鄉多年,故人不在,田園荒蕪,好不容易在異國他鄉扎根,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血脈,又要全部放下,試問誰能那么輕易割舍?又有誰能理解她“只想做個母親”的心境!劇中的王昭君和蔡文姬渴望自我身份的認同,不愿做他人的談資,不甘成為男權社會下的犧牲品。其可貴之處在于她們并不是扮演著世人所期盼、認可或粉飾的角色,沒有將自己束縛在封建倫理綱常的枷鎖中,而是拋開一切,真實的做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女子。
王安祈以極具女性個性、富有巧思的編劇風格重構了王昭君、蔡文姬兩位在歷史上德才兼備的完美形象,展現出編劇別樣的思想觀念和情感表達。她以細膩的筆觸和女性的敘事打破王昭君和蔡文姬傳統的刻板印象,描繪出一副以女性視角和現代思維相結合的心靈景觀。如若她們拋開家國,以平常的姿態,作為一個女人、一個母親向內凝視,呈現出的必然會是另外一番風景。
二、舞臺藝術的呈現:傳統與現代的多元交融
舞臺藝術在戲曲傳承和發展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外在表現。它在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戲曲創作者有意識地從傳統戲曲元素中發掘和探索符合當下時代審美理念的表達方式,借鑒融合多種舞臺藝術表現形式已經成為戲曲創新的重要手段。王安祈也不例外。傳統與現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它們可以互相融合,加以“修繕打磨”,形成精品。“如何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如何以古典優美的表演闡釋出屬于現代的情思,是王安祈‘新京劇的‘現代化努力的方向。”[ 4 ] 1 7 - 1 8如何在保留傳統藝術和人類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創作出符合當下價值觀念的作品一直是王安祈鉆研的方向,而“內在的現代”和“傳統的外在表演形式”的結合正是其用來延續傳統文化的手段。《青冢》是劇作家實現這一理念的重要代表作品,她選取經典劇目進行改編與顛覆,將京劇規范且嚴謹的程式放入小劇場進行實驗,綜合文化語境和藝術本體兩者的考量,創造出既保存傳統又符合社會文化思潮和審美變遷的“新作”。盡管《青冢》不乏外界批判、不認同的聲音,被認為是在褻瀆經典,但是實踐證明,遵循傳統戲的原貌已經不太符合時代語境和歷史趨勢,這種創新方式更容易為大眾所接受。如戴錦華所言:“任何一部經典之作之常新,不在于永恒的審美價值,而在于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語境下的重讀,重要的是講述
神話的年代,而非神話講述的年代。”[ 5 ] 3正因為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念會發生變化,不同歷史時代人們對經典作品所表達的思想意蘊和文化內涵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和表現,才使文學作品呈現出多元化的藝術世界。
(一)戲曲舞臺的傳統延續
在舞臺時空上,《青冢》繼承了傳統戲曲舞臺的自由時空。演員在假定的情境里通過虛擬的動作完成虛擬的表演,觀眾只有承認戲曲舞臺上的假定性,才能給演員足夠的空間去施展和發揮。《青冢》并不是平鋪直敘的講述,故事的整體脈絡就好像是一場夢:初入夢境的無理荒誕——沉浸夢中的混亂顛倒——破除夢境的理性秩序。它從一個漁婦的夢境展開,夢境是無意識領域的,自然可以憑空想象,任由馳騁,于是我們看到崔鶯鶯和李亞仙相互譏笑、對罵、拌嘴,蔡文姬和王昭君進行靈魂對話,互訴衷腸,惺惺相惜。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漁婦時不時地在她們的對話中穿插、游走、念白,仿佛對整個劇進行著干擾與打斷。從整體框架上看,劇中人物的故事因她的夢境而起,也因她的夢境而止,情調隨著江上漁婦的介入由喜變悲、轉悲為喜,可以隨意變換。劇情和時空來回的轉換打破了傳統戲曲的線性結構,觀眾一次一次地在鏡花水月之夢里來回兜轉,沉淪其中。編劇和導演通過這樣巧妙的設計,導引觀眾走進人物的心靈世界,并對歷史、現實、情感、人性進行多維觀照和重新審視。
延續傳統京劇表演體系。京劇傳統老戲的價值,建立在表演體系之精準嚴密,唱念即本體,形式即內容是京劇表演體系的深刻內涵。王安祈說:“傳統戲曲表演體系,這就是傳統的內涵,傳統就在戲曲演員舉手投足唱念做打揚袂轉身顧盼之間。”[6]76傳統京劇以演員的表演為焦點,以此吸引觀眾。從《青冢》看,它不是一味地顛覆古典和簡單的消解,舞臺上依然可以看到中國戲曲“唱、念、作、舞”的融匯。比如,劇作向觀眾傳達的是現代的思辨,但整個唱詞和念白的精雅、巧妙無不流露出中國戲曲古典美的氣息。王安祈先生在劇本臺詞創作的過程中達到了文字的考究,佳句警言比比皆是,既不落俗套,也擺脫了書卷氣,能把歷史掌故以典雅富麗,如彈丸脫手般的詞藻呈現,展現出古典戲曲優美的韻致,也給王昭君和蔡文姬的故事增添了一份華麗而蒼涼的美感。另外,演員在表演過程中沿用了程派的唱腔,把程硯秋先生的經典作品《文姬歸漢》中的唱段做了些許的保留,但又明顯帶給我們截然不同于在劇場觀看經典的感受,舞臺表演有相應的細致、真實、自然,因為小劇場的特性,演員的形體表情,呼吸眉眼不必像大舞臺那樣夸張用力。它打破了傳統老戲比較沉著、穩重、悠然的節奏,是另一種引人入勝的新穎的藝術樣態。《青冢》的表演保有了借鑒小劇場話劇多樣技法之外的“以歌舞演故事”,一方面它跳脫出了傳統的藩籬,又依然讓鐘愛戲曲的人能品咂古典的幽香。可謂是戲曲生命力的另一種延續,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更多元、更深刻的藝術發揮。
(二)舞臺藝術的現代表達
傳統戲曲怎么現代?王安祈說:“新本子沖撞了表演經典,這是京劇由傳統走向創新過程中最根本的沖突。”[6]34傳統戲曲講究的是從演員的表演和唱腔中抒情,現代戲曲講究的是全面整體的展現,不只是演唱和表演。時至今日,有許多成功的作品在實戰中呈現了怎么與現代接軌,精品佳作也時有出現。以臺灣國光劇團的創作理念來說:外在的表演形式和傳唱模式是傳統和典雅,內心的情感是絕對的現代視角,他們本著尊重傳統精神,表達現代思想的原則,恰到好處地將古典唱腔、表演、意境,現代的舞美、服裝、音效、燈光等相融合,既有古典的韻味,又有現代的美感。
《青冢》在傳統戲曲文化基礎上進行了現代的轉型與顛覆,是嘗試給傳統京劇賦予新的時代意義,是以現代人的審美觀念為落腳點,對傳統戲曲元素的進行現代的表達。在舞美設計上,一改京劇的雅正典麗,以蒼涼凄婉風格為基調,自我言說和理性思辨勝過婉約抒情,于是劇中舞臺美術也交相映襯。圓弧形的開放結構,舞臺與觀眾席咫尺之距,四個鬼魂搭配戲劇情境的需要隨時變換角色,一會兒是漁婦夢境中的崔鶯鶯、李亞仙,一會兒又充當起了歌隊,其動作和服飾全然迥異于傳統古典的京劇樣式,是小劇場的另類嘗試。舞臺上光影變幻,陰沉交錯,王昭君和蔡文姬兩人一步一徘徊,一步一惆悵,面對著鏡花里的浮影,往昔種種映入眼簾,當年被迫的抉擇、萬般的悲戚、對前事的懷念、對未來的惶惑,透過光影的映射,兩人心境上的得意與失落強烈凸顯,在搖曳飄蕩、歸途遼遠的路程中女兒家的心事得以被“窺探”。在音效設計上,古典樂器與電子音樂相互交錯,營造了多層次的戲曲氛圍,能較好地輔助于舞臺演出,也給觀眾一種亦真亦假,孰是孰非,時而現實時而虛幻,時而幽靜深遠又撲朔迷離的感受。場景中時而閃爍著微光,時而水滴穿透,是涓涓細流的河水還是時光易逝的隱喻。地板上一方透明圓鏡和舞臺上方的明月相對照,或說是文姬、昭君的孤影徘徊,抑或是波光粼粼的海面,搭配著張若虛的“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和劉希夷的“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透露出一片虛實相生、光影流離,可嘆“人生歷史,何為虛幻,何為真實,誰又能真正分得清呢?”。另外,縱觀整片,它不是大段舒緩的唱腔,它把戲曲的韻白、普通話的對白以及戲曲的唱段巧加組合,而且加大了念的分量,演員一直在戲曲唱腔和和源自話劇的臺詞中切換。昭君和文姬也在這一來一往的對話和交談中,強烈地凸顯出女性自我言說的意圖。
舞臺藝術的創新只是劇場手段,最終目的還是要回歸戲劇文本,回歸到人物性格和情感表達。《青冢》在這方面的設計恰到好處,它既沒有打破傳統舞臺的寫意性,又能兼顧現代色彩,烘托出劇作家設定的以漁婦夢境為線索的情境氛圍、巧妙地外化劇中人物的內心活動,同時也輔助了演員的表演,讓王昭君與蔡文姬的靈魂對話像一幅融入人物心境的山水畫,并轉化為縹緲虛妄的頭銜和女性命運的隱喻,為觀眾展現出了一種美麗又蒼涼的意境。
三、結語
傳統戲曲的現代表現不是全盤地顛覆與否定,也并非大刀闊斧地博取眼球,而是以一個小的切入點進行嘗試與實驗,并在此基礎上廣泛借助中西方的表現手法來開巧和拓新。王安祈的《青冢前的對話》以個體微觀的角度,交出了京劇由傳統走向創新過程中的答卷。從劇本文學的格調上看,劇作以人性為基礎,哲理性的思辨文學、歷史、情感,深刻細膩的探索古代女性被壓抑的心理,以女性視角去審視女性,消解之后再塑人物形象,對性別意識有嶄新的解讀,可以說是另辟出了現代化創新的一條路徑。從舞臺藝術的呈現上看,它以延續傳統為基礎,創造性地設計舞臺、表演、唱腔,用現代化的手段靈活銜接了傳統表演藝術,透過對古典作品的挪移、剪接、重塑,賦予劇作全新的主軸和生命。從王安祈《青冢》的成功實踐可以得出,外在形式創新不應是主流之勢,內在深掘現代的情感才是可行之徑,這也是王安祈在傳統戲曲的基礎上,以期建構符合現代文化思潮的京劇的嘗試。
參考文獻:
[1]王安祈.臺灣新編京劇的女性意識——從女性形象為何需要重塑談起[C]//中國戲曲學院.京劇與中國文化傳統——第二屆京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戲曲學院研究所,2007.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3]王安祈.“乾旦”傳統、性別意識與臺灣新編京劇[J].文藝研究,2007(09).
[4]王安祈.華麗與蒼涼的劇場設計[J].福建藝術,2006(05).
[5]戴錦華.文學和電影指南[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張啟豐,曾建凱.王安祈評傳[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
作者簡介: 沈翠,武漢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戲曲史、當代戲曲。
[責任編輯:萬書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