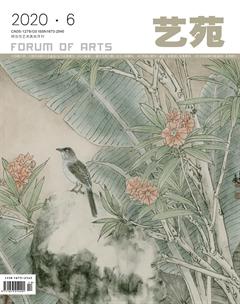從話劇到有聲漫畫
闞梓睿 胡天麒 蘇瓊
【摘要】 《戲子與珍珠》是廈門大學“中文有戲”演出季2020年夏出品的由同名話劇改編而來的線上展演有聲漫畫作品,主創團隊由廈門大學中文系戲劇影視文學專業本科生組成。劇本基于閩南民俗故事,講述偏遠海島上,戲子因島民貪婪的欲望而不得不用戲曲與被當作神明供奉的“漂客”進行交易,逐漸沉溺于戲,并最終失去一切的悲劇故事。文章從劇本創作、劇本改編及劇本演繹的角度,對該劇目是如何從話劇改編成有聲漫畫的創作歷程、創作思路,及在對創作中遇到的困難進行的思考進行詳盡的闡述。
【關鍵詞】 話劇;廣播劇;有聲漫畫
[中圖分類號]J82 [文獻標識碼]A
從2019年6月到2020年6月,《戲子與珍珠》這個劇本一共經歷了大小六次的修改、經歷了演出改期、經歷了臨時換角……但是,作為一個關于大海的傳說,它始終寄托了戲劇初學者對于原創戲劇最初的想象。
一、劇本創作——立足真實空間
《戲子與珍珠》故事的靈感,來自于距離廈門大學不遠處的一座小型廟宇“天上圣媽宮”。偶然間得知這座關乎生與死、關乎陸地與海洋之間奇異的連接的廟宇的傳說,給予了戲劇創作者強烈的創作熱情。于是,在2019年6月的田野調查活動中,我們仔細觀察并記錄了“天上圣媽宮”及其對面古戲臺的詳細特征,為日后戲劇劇本的完善及演出提供現實環境的參照,使得虛構的戲劇情節在延展想象的同時不失去其立足的現實環境的土壤。短暫而翔實的田野調查,為我們日后的創作提供了相當重要的靈感,也讓藝術作品與現實環境、民俗傳統建立了一種內在的聯系。
劇本故事中,戲臺與大海是兩個非常重要的空間,海包圍著島嶼,伸展向無限的未知;而戲臺則坐落于塵世,其上演繹著光環陸離的戲劇,憑借著演員凡俗的肉軀,似乎也昭示著一個超脫于塵世的未知而奇幻的境地。大海所代表的自然與戲臺所代表的藝術同質性的神秘感,這是在最初創作的大綱中尋得的主題。
戲,最初是娛神的。古希臘悲劇起源于酒神祭祀,而中國戲曲最早的源頭也是巫覡的歌舞;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后世戲劇 ,當自巫、優二者”的結論,為國內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其中“巫”便指以“巫”與“覡”為主體的原始宗教性質的歌舞活動,《國語·楚語(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祭祀活動中包含著角色轉化和原始扮演成分,“巫”在演出中會變為降臨人間的神鬼,通過原始的歌舞儀式連接著未知的神明,承載著溝通人與神關系的重要使命。因此,即使到了之后的世俗社會,戲臺也往往會設在神龕對面,這使得戲曲并未與神秘事件完全斷絕聯系。戲臺的空間設置也昭示著在我們的文化中,戲,先是娛神,而后才是娛人。
而“神明”這個概念,出現在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啟蒙理性的光輝照耀之后。在藝術擺脫宗教獲取自身的獨立性之后,似乎已經失去了往昔的神秘感。于是在故事中我們特地把時間模糊掉,沒有留下太多可以定位在人類歷史的具體時刻的印記。同時,我們嘗試恢復神明這一概念在最初的原始社會的含義:對于未知卻無法抗衡的異己神秘力量的代稱。故事選擇了“海女”作為這種神明概念的具象化體現,一個從海上而來的“漂客”,自始至終充斥謎團與未知,卻被劇本中的島民奉為神明。在劇本最初的設想中神明是緘默的,她的意志僅存在于人們口中的解讀。可是當進行第一次劇本改編的時候,我們發現神明不一定只存在于人心靈的神龕之上,而可以成為一個鮮活的角色。在加上田野調查記錄中顯示,“圣媽”曾托夢于當地居民,祈求他們請戲。于是故事中出現了夢境的段落設計,在夢境中主人公可以與“海女”對話,這樣的設計不僅呈現出一種朦朧而神秘的氛圍,也讓故事的內容可以被更清晰地表達。于是,一切事件的起因便被演繹為:“海女托夢”。至此,大海與戲臺得以加強聯系,話劇劇本的藝術性和故事性都得到了加強。
二、劇本改編——加強故事戲劇性
《戲子與珍珠》在經歷了一些系列的交流討論、田野調查以及資料查閱之后,這個唯美的故事逐漸變得更加豐滿,實際排演也就提上了日常——《戲子與珍珠》劇組誕生了。根據故事原始大綱我們進行了全新編寫,注入許多象征含義,比如大海的象征、死亡的終極意義以及戲子唱戲的原因等。為了將故事主題清楚闡釋,在改編劇本中用了非常多的個人獨白來解釋,這便造成了這一版劇本的繁冗。因此,這一次的改編不盡人意。其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主題不明”。縹緲的主題——“人對藝術的不懈追求”在現有的劇本中不能夠被闡釋清楚,沒有強有力的情節作為推動;過于寫實文風又在故事情節上顯得十分突兀,編改進入了瓶頸期。
1968年謝克納提出“環境劇場”的概念,并且文章中說明:“空間的充實,空間可以用無盡的方式改變、連接,以及賦予生命——這就是環境戲劇設計的基礎。”“空間的范圍是占有空地的空間,包含,或包括,或與此相關,或涉及到一切有關演員的表演區域。”[ 1 ]在進一步閱讀謝克納的理論文章之后,我們發現,他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認為:“劇場本身是劇場外的大環境的一部分。這個劇場外的大空間是城市生活;也是暫時的歷史的空間——時空的一種方式。”[ 2 ]我們逐漸意識到戲劇并非一定要建立在割裂生活和藝術的基礎之上,而是可以實現二者的交融,并且可以完全靈活運用戲劇文本、舞臺環境以及現實的環境交疊。
在改編的時候,可以將劇本創作和舞臺實踐當作兩件事情來看,作為一個時間和地點完全架空的故事,編劇完全不需要用一個現實眼光來看待這個故事,相反的,編劇所要做的就是要讓這個故事邏輯通順,讓故事有一個結實的框架。而當真正進行舞臺實踐的時候,也可以摒棄最開始的某些細小的設定,從一個更適合演出的角度重新為戲劇下定義。在重新探討了故事的整體內容之后,我們強化了人物形象和故事內涵,增加了劇本文學的不確定性,讓故事在未來的排演之中更可能發生一些“偶然事件”。 “二十年”這一時間限制變得相對隨機,順序敘述被徹底拆解。與此同時,“夢境”的設計也成為了劇本中的另一大看點,幾乎在每一次的夢境設計中,故事的前因后果和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都逐漸清晰,因此整個故事才能夠名正言順地推到了高潮——死亡帶來的震撼。
三、劇本演繹——有聲漫畫的初探索
《戲子與珍珠》這個劇本本來計劃在2020年6月的時候在建南大會堂作為戲文專業的一個實習作品演出。后因新冠疫情的影響,演出未能正常進行,雖然有些遺憾,但是出于對于表演的熱愛,我們還是積極參與了2020年夏季“中文有戲”的云展演活動。
受到地域限制,團隊甚至一度想要放棄音頻、視頻展演的方式,僅以文本作為演出記錄,但這不免有些遺憾。于是,我們想到了廣播劇,運用聲音手段創造聽覺形象的廣播劇,但高校的話劇演員并非專業配音演員,因此對于劇本的演繹也勢必會有一些折損。并且,廣播劇的聲音創作過程相對話劇來講更為復雜,需要把握好人物形象塑造、環境營造、時空轉換以及節奏控制這四個核心要素。于是,廣播劇這個計劃被放棄了。隨著排練的不斷深入,劇本中設定的背景和環境逐漸浮現在劇組每一個成員的眼前,團隊萌生了一個十分大膽的想法——制作有聲漫畫。這一方面可以彌補聲音演繹的缺陷,另一方面可以給觀眾提供一個想象的空間。于是,我們找到廈門大學藝術學院美術設計類動畫專業的四位學生(劉馨憶、熊錢潔、朱海琦、楊宇杰),開始了有聲漫畫的創作工作。
事實上,話劇和有聲作品完全是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有交疊也有差異,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聲音”。無論是演員聲音的演繹還是音效的運用,有聲作品都會比話劇演出的要求更高。在沒有最直觀的視覺體驗之后,演員的演繹需要更加飽滿。比如在第一幕中,漁夫需要將海女抬上岸,如果是舞臺演繹,觀眾會相當直接地看到一個男子吃力搬運著一具女性的身體,而在表演過程中,男演員的聲音、肢體甚至面部表情都會隨著力量輸出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可是,在有聲漫畫中,聲音和肢體完全割裂,演員需要通過憑空想象來演繹吃力的狀態,這對于非專業的配音演員來講也是一大挑戰。另外,有聲漫畫在音效的運用上也前所未有的多。當塑造環境失去了燈光和舞美的加持,音效就成為了最重要的存在。舉個簡單的例子,廣播劇《茶館》中時不時就會出現茶館內炒勺、面案的敲打聲以及茶館外的各種吆喝聲,這種特殊的音效烘托就能呈現出環境的煙火氣,典型聲音的提煉可以更為準確的定位故事發生環境。[ 3 ]因此,如何體現故事中的環境特點就成了音效組的首要任務。
在整個故事中,主要場所是海邊,因此畫面中時不時會有海浪的音效作為鋪墊。其次,故事的主要場景為:沙灘和夢境。為了區別這兩個場景,團隊在音效處理上將夢境的混響調大,營造出一種幽冥的空靈感覺,并配以一些夢幻、奇幻色彩的背景音;而在現實沙灘中,則突出了人物在沙灘上行走時沙礫發出的摩擦聲,并根據人設的不同進行相應的調整,比如加快或者加重。
有聲作品的節奏也還是相當重要的,一方面是體現在對話上,角色需要通過聲音表現出緩急從容;另一方面,有聲作品整體創作中需要設計好抑揚頓挫的關系,正如《孔子家語·卷七·觀鄉射第二十八》中記載:“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因此,作為導演便不可以只參與演員的排練,還需要進行整體設計,要讓人聲節奏得到控制的同時,也要針對整體音效進行編排,尤其是注重其流動性。通過強弱關系、遠近關系以及音色對比,從而讓觀眾在聆聽的時候可以明顯地聽出聲音的律動。
四、大幕落下——反思與收獲
雖然,《戲子與珍珠》作為首個廈門大學戲劇影視專業的實習作品于2020年6月底在廈門大學“中文有戲”的平臺上以有聲漫畫的形式短暫放送,沒有與大家在舞臺上相見,是特殊時期的無奈,但這也昭示了《戲子與珍珠》還處于“未完成時”的時態。無論是從劇本本身還是排演方式,我們意識到這個作品還有很大的探索空間。因此,我們將繼續創作、完善,希望有朝一日,通過我們的努力與學識的精進,可以呈現出這個故事在我們腦海中所設想的魅力與姿態。
從有聲作品本身而言,《戲子與珍珠》雖然不夠成熟,但是通過這次的實踐,我們發現了有聲作品市場的光明前景。自2020年7月1日上線以來,三個小視頻的總共播放量在短短三天已近3000次,這對于廈門大學中文有戲云演出季的視頻點擊量來說算一個相對理想的結果。為了在未來可以有更加明確的努力方向,團隊針對這一實驗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與調查。事實上,近幾年來網絡廣播劇、有聲書和有聲漫畫等一系列帶動的“耳朵經濟”已經悄然崛起。根據2019年《2018中國移動音頻行業發展盤點》的數據統計顯示,2018年移動音頻行業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用戶總體規模連續12個月呈現上升趨勢,總人數達到了11119萬,全年漲幅50.3%。[4]136-138這一數據,堅定了整個團隊想要將這部作品完結的想法。我們希望在未來的創作中以有聲漫畫作為媒介,通過更加藝術化的聲音來演繹虛擬的場景,構建無窮想象力的空間;與此同時,加入可以更加直接給予觀眾引導的視覺效果,來達到讓觀眾如身臨劇場一般的體驗。
從劇本而言,其最大的不足是在文學劇本創作并未從舞臺角度出發,而是在對于戲劇藝術缺乏整體認知的狀態下,不加選擇地繼承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論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話劇的創作邏輯,以最終在舞臺上塑造現實幻覺的為目的,使戲劇表現完全局限于字句本身,而忽略整個戲劇空間中其它有力的表現手段,如話語的物理屬性,與舞臺空間的交互,與觀眾的交互等。最終結果便是文字劇本僅僅使用貧乏的技巧勉強完成敘事,而無法真正向舞臺敞開,究其根本原因,便是創作時缺乏對于戲劇歷史與戲劇藝術本體的深入思考。
本體概念區別于本質,本體是內涵豐富的整體概念,是由本質與其它特性構成的統一體。本體論是對于存在本身的探討。[5]22-29從戲劇本體論角度思考,首先便要講戲劇藝術作為一種對象性存在去思考。長久以來國內理論界都將“戲劇性”作為戲劇本體屬性的基礎,直到20世紀80年代產生的戲劇觀爭鳴,譚霈生先生系統性的戲劇本體論的提出與實驗戲劇的實踐,推動了對于戲劇藝術本體論的重新思考。[6]87-94
話劇概念于1929年的誕生,在構筑了與由商業環境、近代市民趣味與白話文化主導的“新劇”“文明戲”等概念的差異,提升中國戲劇藝術的品格,賦予“話劇”啟蒙與現代化的使命,并為中國話劇在30年代的成熟奠基,與此同時,也無疑對于中國戲劇創作的發展進行了框定。中國話劇是以易卜生等劇作家的現實主義戲劇尤其是指向明確問題的社會問題劇為模板,在亦步亦趨的模仿中建構的。現實主義的手法、第四堵墻的邏輯、文本中心論長久以來對于在中國戲劇創作實踐中起到統治作用,也導致了對于戲劇本體探討一定程度的遮蔽。
但是作為創作者,對于戲劇本體更立體、多樣化的思考是必要的。創新是藝術的生命,對于不同戲劇體系的思考與了解,無疑會增進創新的可能,而不僅局限于斯坦尼拉夫斯基的幻覺劇場的邏輯。如布萊希特或阿爾托對于戲劇本體異于《詩學》中“模仿說”的思考,對于劇作創作而言也是極具啟發性的,而非單純局限在理論界的探討。
以阿爾托的“殘酷戲劇”觀念為例,1958年在他身故后《戲劇及其重影》的出版,使他的理論影響了彼得·布魯克、格洛托夫斯基、彼得·魏斯等大批導演與編劇,在80年代初期在中國被高行健推廣并在實踐中運用。阿爾托將戲劇視為一種現代的儀式而非對于行動的模仿,他將戲劇比作瘟疫,重拾作為戲劇起源的儀式中的表達手段,使西方現代戲劇實現由文本中心向舞臺中心的轉向。而就其對于中國戲劇發展的影響而言,高行健所稱的“完全的戲劇”,是使戲劇擺脫“單純的說話藝術”,是對于古老戲劇手段的重新使用,擺脫現實主義的戲劇布景,注重演員與觀眾的交流等。[ 7 ] 3 8 - 4 8
結 語
綜上所述,《戲子與珍珠》作為不成熟的學生習作,劇本創作流程折射出的,是缺乏戲劇本體論認識對于劇本創作的巨大限制。這提示著我們無論是理論或是優秀作品的鑒賞方面,都是成熟創作的必要積累,從事一種藝術類型的創作,有必要了解其媒介本身的特質,并對藝術門類進行形而上的本體論思考。《戲子與珍珠》歷經一載時光終于和觀眾見面,其中還存在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無論如何,這部作品都算是團隊的一次用心實驗。在這次實驗中,大家都實現了一定的突破,也都對話劇和有聲作品有了新的了解,并希望在未來可以繼續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理查·謝克納.環境戲劇·空間[J].戲劇藝術,1989(4).
[2]葉志良.環境戲劇:與生活同構[J].戲劇文學,1998(2).
[3]魏曉軍.簡論廣播劇聲音創作的核心要素[J].現代傳播,2015,12(39).
[4]章琰.消費文化視角下的“耳朵經濟”——以付費網絡廣播劇為例[J].科技傳播,2020(8).
[5]徐海龍.“戲劇場”的演進與戲劇本體論的發展[J].戲劇藝術,2020(03).
[6]徐晨,施旭升.情境抑或意象:戲劇藝術的本體之辨——從譚霈生《論戲劇性》及《戲劇本體論》談起[J].民族藝術研究,2020(04).
[7]韓德星.阿爾托“殘酷戲劇”理論在中國大陸的傳播、研究與影響[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2(01).
作者簡介: 闞梓睿,廈門大學中文系戲劇影視文學專業2017級本科生,廈門大學南強話劇社社長;胡天麒,廈門大學中文系戲劇影視文學專業2017級本科生;蘇瓊,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
[責任編輯: 林步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