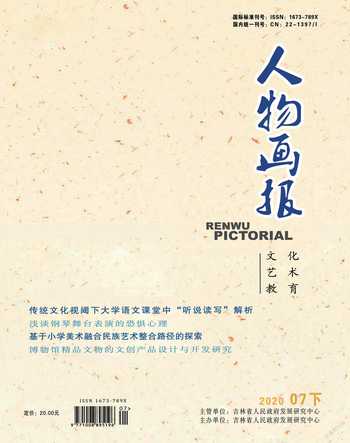最可愛的人
張竹君
摘? 要:本文從細節描寫出發,討論《紅巖》正面人物劉思揚的性格豐富性,進而在個人成長的道路中看革命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練與思想改造。
關鍵詞:《紅巖》;劉思揚;人物形象
“血性”與“人性”始終是十七年紅色小說中的正面形象塑造繞不開的矛盾,然而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人物形象特別是正面人物形象扁平化的問題往往容易被忽視。一方面,小說情節需要正義完美的英雄與反派斗爭,英雄越剛強,碰撞就越激烈,吸引力就越強。另一方面,當個體被拋入宏大的敘事中,個人性格多樣性與跌宕緊張的情節相比顯得不那么重要。這也是故事中的許云峰、成崗等雖然形象扁平但不顯突兀的原因。然而,當一個生動立體的形象出現在讀者面前,不論作者是否刻意為之,都能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劉思揚——小說《紅巖》中的正面人物,正因“血性”后的細膩豐滿的“人性”而區別于丑角般的反面人物,也區別于其他無懈可擊的正面人物,成為革命斗士群像中最獨特、可愛的一位。
一、渴望被認同
來自富商家庭的知識分子劉思揚并未深入基層,富足安定的生活環境決定了他涉世未深的天真與激情,這種純真并沒有隨著閱歷的增加而消失,在整個革命道路中直到犧牲時,純真的天性始終伴隨著他。
資產階級的出身給他的自我認同帶來難以愈合的缺口。“身份”幾乎成為意識中的“原罪”他需要在旁人一次次的理解和認同中反復地鞏固自我,掩飾自卑。尋找,迷失,自卑,再尋找,再迷失……一遍又一遍,讓我們看到他對被理解極其強烈的渴望。于人物本身來說,這或許是性格的缺憾,而于故事中的整體形象塑造來說,則是相當精彩的一筆。
二、細膩敏感
細膩敏感是十七年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最重要的共性之一,劉思揚也不例外。當眼淚被視為軟弱、沉溺,與革命精神不符的東西時,當江姐得知丈夫的死訊強忍淚水并會為想哭的沖動而自責時,會落淚的劉思揚顯得那么可愛。盡管在地下黨人看來習以為常的離別,盡管英雄向來瞧不起眼淚,他依然可以正視自己的情感,沒有激昂的口號,有的是《鐵窗小詩》,沒有憤慨的反抗,有的是真實、淋漓、詩意的淚水。豐滿的人性同樣體現在對未婚妻的感情上,夫妻之情被升至革命友誼的高度,而貫穿始終的溫暖細節總能給人溫柔的安慰。
三、孩童般天真
經歷幾番風雨來到白公館后,劉思揚依然沒有褪去孩子般的幼稚單純,一張小小的馬克思像便能使他投注全部精力,忘我地沉浸與喜悅與激動之中,甚至可以不顧成崗的反對,不考慮后果。
劉思揚躲在房角里,用背掩蔽著自己的動作,牙齒輕輕咬濕筆尖,唾液拌合著墨,在白紙上臨摹著那張馬克思的像。他慢慢畫著,畫得相當像。然后,用留下的飯粒,把畫像貼在已經破舊的《讀書偶譯》的封面上。 ……劉思揚十分愉快、興奮,一種使人陶醉的火熱的欲望,不斷在他心頭沖動。……他被周圍的事物吸引得眼花繚亂,心潮激蕩,不能控制自己了。[1]
四、小資產階級的成長之路與人性的復歸
見到新入白公館的學生胡浩,就像見到了最初的自己。而此時的劉思揚已經改掉了幼稚和沖動,以更嚴謹的態度考量著這位新來的戰友。這標志著一位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誕生,更標志著個體與群體的合流、階級壁壘的打破,標志著人物形象每個不同的側面滲透融合,像一幅終于拼上最后一塊拼圖的拼圖畫,達到了統一、圓融的境界。
時光回到三十年代,巴金先生的長篇《家》中也有這么一位可愛的進步青年——三少爺高覺慧,可當他面對心愛的女孩——丫頭鳴鳳被許配出嫁的花轎面前卻選擇掉頭回避,并用“更偉大”的革命理想為當下的懦弱找借口。那一刻,原本對平等自由戀愛的追求在小資產階級天生的驕傲面前,是那么地脆弱渺小,不堪一擊。所有人都沒有沒有想到,要打破封建,打破伴隨自己出生和成長的藩籬竟然如此艱難。憎惡它,卻只能受限于它。不論接受怎樣進步的思想,成為怎樣一名大無畏的戰士,舊等級觀念依舊如影隨形地生長在他的靈魂中。他與劉思揚一樣,有著只屬于他們階層年輕人的單純天真,一邊向著光明的理想邁進的,一邊以那個與光明一樣遙遠的理想掩蓋原本懦弱自卑的心靈。然而年輕的覺慧無法意識到自己深惡痛絕的等級觀和軟弱性已成為自己性格中難以分割的一部分,在歷盡痛苦的磨礪前,是不可能鏟除的。我們無從知曉劉思揚的早年經歷,包括走上革命道路的過程種種,卻可以從高覺慧身上推測其成長的心路歷程。時代不同,革命任務不同,但兩位小資產階級革命戰士有著共通的起點:高覺慧就是早年的劉思揚,劉思揚就是歷盡苦難后成長的高覺慧,其性格發展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而他們二人中間,隔著一層層肉體的、更是精神的煉獄。故事中緊張艱苦的斗爭已經超出了情節本身,超出了革命本身,成為一次次精神的磨難和心靈的拷問,最終完成了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的改造。
子彈無聲地打中了劉思揚的胸膛,完成蛻變后的他仿佛回到了當初那個懵懂的孩子,帶著全部的單純與熱情回想起那些戰友。沒有昂揚的口號,沒有痛苦的呼喊,沒有無畏的炯炯眼神,一切都歸于平靜,歸于人性本來的樣子,有戰友,也有因獻身革命而遺忘多時的未婚妻,有戰斗的激情,也有溫柔的愛情,喜悅、激動、遺憾、慚愧,堅毅中帶著柔情。如果說面對胡浩的態度標志著成長的完成,那么犧牲則標志著本性的回歸與追問,攀上巔峰后的自省。
“血性”與“人性”,私人情感與革命需要,構成了人物的內在張力,也是人物塑造成功的動因,這與人物的個人決擇是分不開的。劉思揚經歷了至少兩次決擇——是否走向革命、是否堅持革命。和成崗、老許、江姐他們相比,其可貴之處不在于走投無路后的義無反顧,而在于明明可以放棄,卻選擇堅持。這兩次抉擇在成功塑造形象之余,也深化了小說“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煉與思想改造”這部分主題。讀者不再是旁觀者而以參與者的身份,跟隨情節發展陪伴人物的成長,成為故事的一部分,回到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與先烈們共同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因此,與其說經典的《紅巖》成就了劉思揚,不如說是可愛的劉思揚成就了《紅巖》的經典。
參考文獻:
[1] 羅廣斌,楊益言.紅巖[M].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