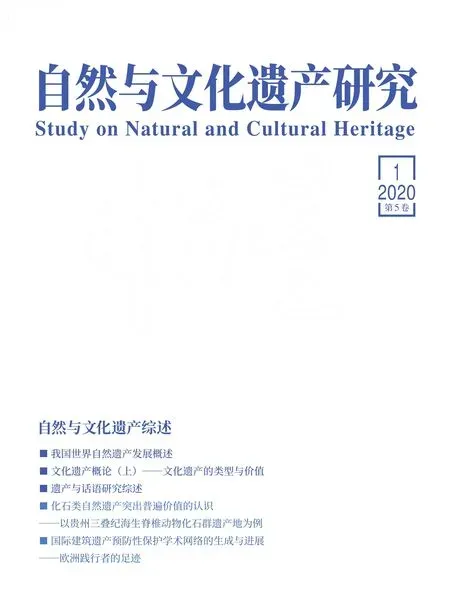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發展回顧
解孫立
(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北京 100029)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 于1965年在波蘭華沙成立。從創立之初,它便致力于保護世界各地的文化遺產地,而今仍舊是這一領域唯一的全球性非政府組織。作為一個文化遺產專家網絡,從誕生之日,它就自帶當今流行的“跨學科”屬性,專業領域涵蓋建筑、歷史、考古、地理、人類學、藝術、工程和城市規劃等。區別于國際博協(ICOM)針對可移動的館藏文物的保護,它的保護領域主要為“不可移動”的文化遺產地,包括建筑、考古遺址、歷史城鎮、鄉村、文化景觀等。
截至2019年2月,ICOMOS有來自全球151個國家的1萬多名個人會員、107個國家委員會和28個涵蓋不同遺產保護類型和主題的國際科學委員會①文中引用的所有關于ICOMOS組織的事實數據均來自ICOMOS國際官網www.icomos.org.[1]。作為聯合國教科文世界遺產委員會唯一的文化遺產申報項目評估機構,ICOMOS已評估審核了869處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和39項文化與自然混合項目,并對其保護管理狀況提供監測評估[2]。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使其成為不可移動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中最大的全球性專業組織,而其誕生和發展也幾乎反映了現代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發展的全過程。
1 背景、誕生與發展
1.1 背景
從某種程度上,保護遺產的意識可以追溯到人類歷史之初。傳統社會中文化遺產可以被看作族群共享的價值,通常與土地和財產相關,也指代代相傳的文化和精神傳統,在諸多古代社會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并通過官方手段加以保護。文化遺產保護在歐洲的興起源于文藝復興對古代(希臘、羅馬)遺跡的欣賞和重新認知。古代建筑、雕塑等自15世紀開始就得到了教皇專門的保護和修復,藝術作品也開始成為收藏和買賣的對象。隨著科技進步、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的發展,18世紀的歐洲進入現代社會,歷史建筑和古代藝術品的保護和修復出現了復雜多樣的理論實踐方向。法國、英國、意大利等不同保護修復的流派間展開了激烈論辯,使得早期的現代保護和修復理念日趨成熟,也促進了不同國家專門的遺產保護立法和管理體系的建立。
直到19世紀末期,文化遺產保護更多局限于國家事務。眾所周知,文化國際主義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產物:“一戰”后成立“國際聯盟”“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1919年),“二戰”后發展為今天的“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45年)。兩次大戰對全球范圍內人類建成和居住環境的空前破壞,以及大量戰后重建面臨的急迫行動,從全球層面推動了對文化遺產認知和保護的國際共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初對文物保護領域的關注點主要在館藏文物上,1926年專門成立國際博物館辦 公室(International Museums Office),1946年改稱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然而,戰爭對歷史城市的巨大破壞必然使這一關注點擴展到更大的層面。
1931年和1933年的兩份同名文件《雅典憲章》,分別由國際博物館辦公室和國際現代建筑大會(CIAM)通過,前者是第一份關于歷史建筑修復的國際文件,由意大利建筑遺產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古斯塔夫·喬瓦諾尼起草;后者則是一份關于城市規劃的綱領性文件,由現代主義建筑大師勒柯布西耶起草。兩份文件立場迥異甚至有根本沖突,但卻共享了一個關注點:建筑和城市遺產。兩份文件都強調了遺產保護對城市發展的價值以及對歷史城市保護和發展的討論進一步國際化的必要性。遺產保護問題成為全球性的問題,而成立專門的全球性遺產保護修復專家組織,區別于已有針對館藏文物的國際博物館協會,就顯著更為迫切和必要,這也是ICOMOS產生的歷史背景。
1.2 誕生
1964年,在威尼斯舉行的第二屆歷史建筑保護專家與建筑師大會通過了13項決議,第一項就是著名的《古跡遺址保護修復國際憲章》,又稱《威尼斯憲章》,第二項是在UNESCO倡議下成立ICOMOS。1965年,ICOMOS成立大會也是第一屆代表大會在波蘭的華沙召開,通過了組織章程,選舉了主席執委等。促成ICOMOS成立的幾大國際組織也都參加了會議: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ICCROM(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1957年在羅馬成立的政府間組織)、ICOM(國際博協)和UIA(國際建筑師聯盟)。以上組織自身的領域和性質也反映了ICOMOS建立的多方需求和基礎。
ICOMOS總部設在巴黎,自誕生便帶有“歐洲/西方中心主義”的印記,此處“歐洲中心”是作為中性詞使用的,畢竟現代遺產保護運動是建立在啟蒙運動后歐洲史學觀和哲學思想的基礎上。1965年大會上選出的首任執委全部來自歐洲,作為奠基人參會的25個國家,即是1964年《威尼斯憲章》起草會議上的25個國家[3]。《威尼斯憲章》確立了ICOMOS的基本價值和原則,而這份綱領性文件基于對之前歐洲(尤其意大利為主導的)保護修復理念實踐的全面總結是顯而易見的。
1.3 發展
ICOMOS成立大會上有25個國家參加,而今正式會員已經覆蓋了151個國家,在107個國家建立了國家委員會。這使得這個國際組織能夠真正從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思考和實踐中汲取營養,例如由澳大利亞國家委員會制定的《巴拉憲章》,就產生了超越本國的國際影響,由中國國家委員會②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ICOMOS CHINA)在國內注冊名稱為: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成立于1993年,詳情見官網www.icomoschina.org.cn.[4]制定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也融合了中國文保工作者的本土經驗[5]。
ICOMOS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從最初的0個發展為1980年的7個,1995年的15個,截至今日共28個,這體現了遺產領域的不斷豐富和細化。同時,這些科學委員會還貢獻了針對不同遺產類型和保護主題的專業討論和具有指導性的國際文件(表1)。

表1 國際科學委員會及相關文件列表

續表1 國際科學委員會及相關文件列表
自1965年起,ICOMOS每3年召開一次全球代表大會和科學研討會,匯聚全球的文化遺產從業者,聚焦遺產保護的當代話題,通過深入討論,形成對行業發展和保護工作有著指引性的成果(表2)。

表2 全球代表大會列表

續表2 全球代表大會列表
1972年對ICOMOS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對全球遺產保護非常重要的一年。隨著國際社會對有限的自然資源和文化遺產價值及其脆弱性認知的不斷增強,1972年6月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大會著重強調了“人居環境”(含自然與文化)。1972年,ICOMOS科學研討會的主題是“歷史古跡中的現代建筑”,也是關于人居環境的。同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大會通過了《關于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的公約》(簡稱世界遺產公約),公約中規定了ICOMOS為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的專業評估機構。自此,ICOMOS的發展也與世界遺產的發展交織并行。
如上文提到,ICOMOS已評估審核了869處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和39項文化與自然混合項目,并對其保護管理狀況進行監測。
ICOMOS為世界遺產的不斷發展提供各種形式的研究支持:包括對“OUV(突出普遍價值)”等核心概念的定義與解讀;促進世界遺產名錄更具全球代表性的《世界遺產名錄填補空白報告》;通過新類型和新概念的引入,擴展對文化遺產的研究和保護方法,如文化景觀、文化線路、系列遺產等;開展專項主題研究,推動對特定類型、主題的文化遺產的認知,并為其申報提供全球比較框架,如運河、巖畫、絲綢之路、工業遺產、天文遺產等(表3)。ICOMOS因此全面參與、見證和體現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發展歷程[2]。

表3 ICOMOS主題研究報告列表
2 從ICOMOS重要文件看遺產保護不斷豐富的內涵與外延
ICOMOS歷年的重要文件中顯示的變化向我們描繪了一幅相對連貫的遺產保護發展路線圖,展示了遺產保護理論框架如何持續演變擴展以容納時代變遷。它適應全球化的趨勢,關注點從藝術品到多元文化表達,從單體文物建筑到需要在區域范圍內以綜合、動態的方式整體認知和管理的活態文化景觀。以下選取幾份ICOMOS文件為例,試圖勾勒出其發展(尤其早期)的大致脈絡和重要節點。
2.1 《威尼斯憲章》(1964年):ICOMOS的奠基石與定音鼓
因建立在之前所有相關的理論思辨和實踐經驗之上(最主要的是意大利現代修復理論,“科學修復”和布蘭迪理論等,摒棄了法國的“風格式修復”)[6],《威尼斯憲章》一經問世就是一個高度成熟的文件,為之后的文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威尼斯憲章》以真實性為核心,批判分析為方法,尊重各時期的歷史信息,涉及現代遺產保護修復中所有重要議題,并提供了之后被全球廣泛認可和應用的基本原則,如真實性、完整性、可識別等。同時,它也具有前瞻和開放的一面:盡管內容側重歷史和藝術價值高的文物建筑和遺址,但它也提到了遺產的背景環境(setting)、普通古跡(modest works of the past),強調遺產保護跨學科合作的屬性,鼓勵遺產合理利用和保護中的新技術應用等。
這一文件的高度凝練使其成為ICOMOS長期的行動參考。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之后的文件都是從不同方面對它持續的更新和補充:例如《巴拉憲章》和《奈良文件》是基于文化多樣性視角的補充;《華盛頓憲章》和《墨西哥城憲章》則是就特定遺產類型的補充,分別為歷史城市和鄉土建筑。
當然,《威尼斯憲章》作為一份20世紀60年代的文件,其中也有很多不足,例如在強調建筑遺產的藝術和歷史價值、考古遺址的科學價值的同時,與保護息息相關的文化和社會價值卻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在談到保護措施時,該文件更局限于保護物質遺存的技術手段,而對其他的如立法、財政、規劃等工具則沒有涉及。
2.2 《巴拉憲章》(1979年,2013年):超越國界的國家文件
《巴拉憲章》全稱為《保護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場所的巴拉憲章》,和其他ICOMOS的國際文件不同,它是一個由ICOMOS澳大利亞國家委員會制定的國家文件,但澳大利亞同行結合本國實踐做出的深入的專業思考使這一文件具有了超越國界的影響力。
在這一文件中,文化遺產由之前的“古跡遺址”(也就是建筑和考古遺產)發展為“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場所/遺產地”;文化遺產價值正式在藝術、歷史、科學價值之外增加了社會和文化價值。這一文件首次嘗試對重要的專業術語加以統一的界定,如最基本的保護、修復、保存、改造、利用等,通過回到詞匯理清概念,繼而被廣泛接受而國際通用。
《巴拉憲章》也對梳理保護原則和程序有很大的貢獻,如更加明確強調了“最小干預”原則③《巴拉憲章》中雖沒有使用“最小干預”的措辭,但在多處提到對遺產本體最小影響和最低程度的干預等,強調行動的必要性原則和謹慎 態度Cristina Ureche-Trifu“,Minimal Interven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onserving the built heritage” Carleton University,Ottawa,2013,P14:“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Burra Charter(1979) is one of the first documents to make reference to minimizing the effect of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on the material fabric.”[7],和基于價值的管理,而其中價值須全面考慮各方面的價值。
《巴拉憲章》將文件使用的目標人群從專業人員擴大到管理者、業主和使用者,使這一行業準則幾乎成為澳大利亞從政府決策者到普通建筑師等相關從業人員的常識,這是這一文件努力結合社會現實的巨大成功,也是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的必要趨勢。
《巴拉憲章》全面總結了澳大利亞自身遺產保護理念實踐,應用于其國內的文化遺產認定和保護,形成了基于多元價值評估的管理體系,也通過其之后多個世界文化遺產的成功申報和管理推動了世界遺產體系的發展,尤其對于文化景觀類遺產認知的推動。
2.3 《保護歷史城市和城區的華盛頓憲章》(1987年):第一份城市保護憲章
這一文件總結了之前幾十年關于歷史城市和城區保護和規劃的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旨在為文化遺產領域積極貢獻一份關于城市保護的文件。憲章強調了城市保護不僅是對遺產區域的保護,更關乎其發展和融入當代生活。融入既是目標也是手段,且應該是各方面和各層級的努力。一方面,城市保護在積極探索如何將其作為整體社會經濟發展和區域規劃的有機構成;另一方面,城市設計和空間規劃的工具和方法也被應用于分析理解歷史城區的特征和品質,以制訂融合性、適應性更強的整體保護方案。其中關于住房改善和公共參與等政策內容,為《威尼斯憲章》增添了令人信服的社會維度。
同年,《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中增加了9段關于歷史城鎮的條款,對這一重要遺產類型的研究、保護管理得到了更廣泛的國際共識。值得回顧的是,1978年最先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兩個歷史城市中心是秘魯的奇多和波蘭的克拉科夫,它們都是以保存完好的建筑杰作列入的。
2.4 《奈良真實性文件》(1994年):并不是一份日本文件
自《威尼斯憲章》起,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原則就是真實性。隨著國際社會對文化多樣性的關注,《奈良文件》對原有的真實性概念做出了重要補充。如果說《威尼斯憲章》更強調物質和有形遺產的真實性,《奈良文件》則通過增加在某些文化中至關重要的非物質維度,如延續的傳統等,使這一概念更加完整。因此,《奈良文件》是基于《威尼斯憲章》精神的延伸,總結和回應當代社會遺產價值認知的新發展—即《威尼斯憲章》問世時未能涵蓋的對文化多樣性的強調和關注。
同年,《操作指南》中增加了8個段落關于“文化景觀”的內容,這也是對鼓勵文化多樣性的回應。不同于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在有些國家中城市文化并非主導,或者說某些文化更珍視其他形式的與自然互動的關系,因而存在與傳統紀念性建筑遺產不同的具有重大文化意義的景觀和場所。《操作指南》的這一修訂豐富了世界遺產的內涵和外延,也有效提升了遺產認知和保護的全球代表性。
略有遺憾的是,《奈良文件》沒有被更好地用作一個融合物質、非物質遺產的契機。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出“人類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非物質文化遺產獲得了應得的國際關注和保護,但因此出現的兩個平行的保護體系也為整合性地管理某些遺產地帶來了一定困難。
3 結束語
本文僅列出小部分文件,其后還有關注文化遺產背景環境的《西安宣言》(2005年),關注遺產地場所精神的《魁北克宣言》(2008年)等。近年來的議題包括:可持續發展、戰后/災后重建、氣候變化和鄉村景觀。ICOMOS作為一個群體,從未停止參與和推動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討論和行動。它關注的議題持續映射著遺產保護工作與生俱來的人文關懷,和參與當下社會發展的努力;也唯有與人的生存與發展緊密相連,遺產保護才有效和有意義。
筆者曾參加過多屆ICOMOS的年度大會,看到荷蘭萊頓大學研究古羅馬帝國交流史的考古學家發起倡議,抵制歐美企業(如殼牌)對非洲自然和文化遺產的負面影響;意大利和法國同行為伊拉克和敘利亞的遺產記錄和分析做的數字重建;ICOMOS瀕危遺產觀察計劃(heritage@risk)每年持續出版觀察報告并建立網絡平臺加強公眾宣傳;加拿大的遺產建筑師在大會上提醒同行重新找回在學術探索和行業實踐上的前衛精神和引領作用。
作為一個組織,ICOMOS曾意氣風發,發現、直面和處理最當下的問題,力求突破邊界。
如今,面臨一個不斷加速的世界,遺產保護可能處理的是最緩慢又最緊迫的問題,真實性仍位于問題的核心。這個群體,經歷半個世紀的起伏,能否不忘初心,繼續在求真、行動和反思中成長,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