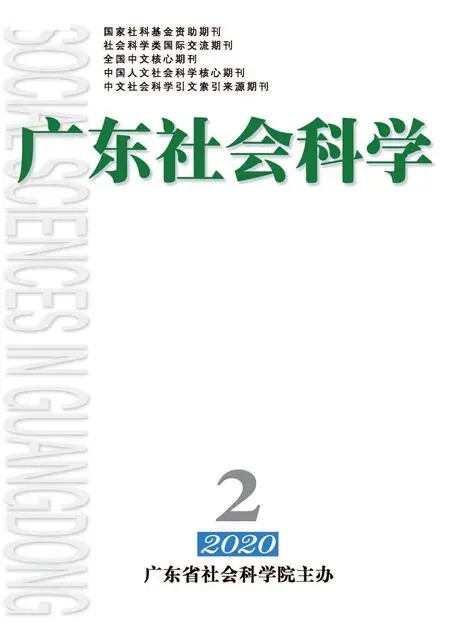論汽車經銷商的締約欺詐及懲罰性賠償
冉克平
1993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頒布后不久,法院就將該法第49條適用于消費者因購買汽車引起的欺詐糾紛。歷經20年,汽車屬于“消法”的調整對象并可適用“退一賠三”的懲罰性賠償已成為共識并被“消法”(第23條第3句)所采納,其中,豪華汽車銷售中的欺詐及懲罰性賠償問題尤其引人注目。①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第17號指導性案例(“張莉訴北京合力華通汽車服務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然而該指導性案例并未明確:哪些情況屬于汽車瑕疵,生產商、經銷商告知義務的范圍和舉證責任以及生產商、經銷商不履行告知義務是否必然構成欺詐并承擔懲罰性賠償。②2016年發生在貴州的“賓利車退一賠三案”引起了媒體和汽車行業的普遍關注。一審判決汽車經銷商返還消費者購車款385萬元,并支付消費者懲罰性賠償金共計16500000元。但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認為,經銷商并不構成欺詐,僅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對消費者知情權的侵害,該案不同于“第17號指導案例”,故經銷商應向消費者賠償11萬元。③
如何擴大消費者的知情權和明確經銷商的信息告知義務,以避免交易過程中的欺詐或誤導行為,一直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制的重心。④結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案例,以下問題亟待討論:(1)從解釋論看,如何確立汽車經銷商的信息告知義務及其范圍,最高人民法院在“楊代寶賓利案”中援引中國汽車流通協會發布的《乘用車新車售前檢查服務指引(試行)》(以下簡稱“PDI”)作為判斷汽車經銷商瑕疵告知義務的依據是否具有正當性?(2)如何判斷汽車經營者締約欺詐的構成及其舉證責任?(3)從立法論看,汽車經銷商締約欺詐承擔“退一賠三”的懲罰性賠償責任是否妥當?
一、汽車經銷商的信息告知義務及其判定
(一)汽車經銷商信息告知義務
與汽車生產商和經銷商(通常為“4S”店)相比,消費者在汽車銷售中處于弱勢地位。經銷商的締約信息告知義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締約中,經銷商不得對消費者提供虛假信息,否則構成違反明示信息告知義務。其中,“車輛合格證”和“車輛一致性證書”是證實車輛的基本規格配置的重要文件,表明經銷商實際交付給消費者的車輛與雙方當事人約定車輛之間的一致性。二是汽車經銷商在締約過程中不得故意或過失隱瞞一些可能影響消費者選擇權的重要信息,否則構成違反默示信息提供義務。經銷商在締約過程中無需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全部信息,但須提供可能影響消費者安全權、選擇權等權益的重要信息。⑤現代汽車構造復雜、零部件眾多、技術程度高。汽車從生產商、貿易商、物流商、經銷商至交付給消費者,其間涉及多個交易環節且信息量巨大。要求經銷商在交易過程中將全部信息不加區分地告知消費者,不僅會導致交易成本的不必要增加,而且不利于消費者知情權的實質性保護。
(二)汽車經銷商信息告知義務的判定
汽車經銷商的欺詐行為表現為違反明示信息告知義務與違反默示信息告知義務兩種方式。前者表現為汽車經銷商在締約過程中對消費者提供的汽車信息與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的不一致,即虛假陳述。例如雙方當事人約定的汽車的原產地與實際交付的汽車生產地不一致即屬于此種情形。⑥虛假陳述亦可依據交易慣例通過可推斷的行為予以認定。在汽車銷售實務中,除非是在二手車市場或者銷售者特別說明的場合,依交易慣例,經銷商所銷售的汽車應當推定為新車。⑦此外,對于二手車交易,若經銷商對該車的特定的事故瑕疵予以了說明,那么由此可推斷為他表示該汽車沒有其他事故損傷。對于消費者提出的問題,經銷商原則上必須予以正確和完整的回答,以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經銷商錯誤的回答可以被歸為通過積極行為而進行的欺詐。經銷商誠實和完整地回答義務的例外情況是,如果某個問題是不允許的,這取決于是否應當肯定經銷商具有一個正當的、應受保護的利益。⑧例如消費者詢問該車是否為全國最低價,或者經銷商的利潤等。對于后者,只有經銷商對被隱瞞的事實存在告知義務時,亦即經銷商有義務對有關交易的某項事實作出說明的情況下,沉默才可構成對消費者的欺詐。經銷商默示信息告知義務的認定是相關理論關注的重點,其不僅可能產生于相應的法律規定,還可以基于個案的情況依據誠實信用原則以及交易慣例而產生。例如《荷蘭民法典》第3:44條第3款規定,如果當事人對于“有告知義務”的事實有意保持沉默,則構成談判中的欺詐,但該法并未規定該義務何時存在。依據《合同法》第42條第2項的規定,“當事人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 實質上也是對“信息提供義務”的高度概括。這些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應當是可能影響消費者選擇權的所有重要信息,包括質量、性能、用途以及有效期等(“消法”第20條)。然而,無論是信息需求還是特殊的專業知識,原則上都不能為締約當事人創設一項廣泛的說明義務,因而立法上的這種一般性表述往往顯得抽象而無濟于事。
經銷商默示信息告知義務的認定,學說與判例對此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如弗盧梅教授認為,應依據適用于某種公平的交易觀點和具體的業務類型來決定,交易一方是否存在信息告知義務。⑨梅迪庫斯教授對此予以詳細的分析,認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信息提供義務必須通過利益權衡予以確定。在進行利益權衡時,首先要看哪一方當事人能夠更容易地獲取信息。例如,對于一輛二手車的行駛里程和車禍記錄,經銷商通常更容易獲取;其次要考察有關信息對另一方當事人具有的重要程度;最后是對信息提供義務的期待應具有合理性。⑩還有學者在此基礎上認為,還應包含另一方當事人對專業知識的特殊信賴。沃爾夫教授強調,信息告知義務是否存在首先取決于雙方當事人的締約目的。拉倫茨教授則進一步指出,信息告知義務的認定取決于交易當事人之間的關系與行為類型。若當事人之間的信賴程度越高,說明義務越容易被確定下來。《歐洲合同法原則》第4-107條規定:“法官在判斷說明義務是否成立之時,應考慮該方當事人是否為專家、對方當事人能否獲知該信息以及該信息對其意思表示的做出及其內容之影響程度、雙方獲取該信息各自所需的費用大小等因素。”《歐洲私法共同參考框架草案》第Ⅱ-7:205條第3款與之相同。我國有學者借鑒比較法學理與規范的經驗性認識,認為說明義務的判斷應當考慮四個因素:信息本身的重要性、義務人提供信息的可能性、權利人期待的合理性以及交易雙方信賴的緊密度,并通過上述要素之間的相互協作形成動態體系予以權衡。
筆者認為,若汽車經銷商的信息提供義務產生于當事人約定、法律明確規定(例如汽車的警示缺陷)或交易習慣,則其不得對消費者保持沉默。除此之外,應當在誠實信用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的框架之下考量汽車經銷商的信息提供義務。這是因為,信息提供義務在性質上屬于先合同義務,系以誠信原則為基礎。汽車經營者在專業知識上占據優勢,而消費者通常沒有經驗,因而雙方當事人之間形成具有特殊的信賴關系。因此,經銷商的信息提供義務亦屬于信賴責任的范疇。要建立信賴與責任之間的直接聯系,必須在信賴事實之外確定責任的正當性基礎。信賴責任的基礎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信賴者的信賴合理性和責任人的可歸責性。信息提供義務的判斷必須強調消費者與經銷商利益的平衡,具體表現為信賴合理性和可歸責性要件的相互配合,并根據二者的程度差異而有所偏重:信賴合理性程度越高,歸責性程度就可以降低;信賴合理性較低,歸責性程度就必須提高。在汽車經銷商的可歸責性(以誠信原則為基礎)與消費者的合理期待(以信賴保護原則為基礎)的框架之下,經營者的信息提供義務的判斷應當考慮以下因素:(1)消費者的締約目的。經銷商應當對有關消費者締結合同的決定具有重要意義的信息作出說明,特別是消費者知道真實情況就不會締結合同的重要信息。例如,新車交易的經銷商必須告知消費者汽車是否屬于試駕車;二手車的經銷商必須告知買方有關汽車的行駛里程、剎車系統的缺陷、汽車之前的事故等關系消費者締結合同目的的信息。(2)對汽車基本現狀的影響。有學者認為,美國法院所提出的購買者合理期待與不影響汽車狀態這兩個標準值得借鑒。若輕微的瑕疵及修復行為并不影響汽車的基本狀態,對此并不構成欺詐。從我國司法實踐來看,汽車經銷商是否應當告知消費者瑕疵信息,需要從合同中是否對此存在專門約定、瑕疵是否嚴重及相應處理措施是否復雜、是否給消費者造成較大不利影響等方面予以考量并綜合判定。申言之,經銷商不負有將顯著輕微的瑕疵信息告知消費者的義務。例如汽車油漆的輕微瑕疵顯然不能與剎車系統中的缺陷相提并論。(3)經銷商信息獲取的成本或者可能性。對于汽車經銷商知道或能夠很容易查明的汽車的瑕疵信息,經銷商有義務將其告知消費者,盡管買方自己也可以取得相同的信息,但可能會付出很大代價。這不僅有利于有效地分擔風險,而且也具有經濟合理性。經銷商應負有依善良管理人的客觀標準收集及調查該項信息的義務。(4)消費者的信賴合理性。消費者對于經營者專業和技術的信賴必須具有合理性,即按照市場交易觀念,經銷商對消費者信息的告知是人們所能夠期待的。消費者的信賴合理性與經營者的可歸責性可以作為雙方利益平衡的機制彼此牽連。例如對于汽車是否改裝或者是否更換過部件總成,消費者具有足夠合理的信賴要求經營者予以告知。
(三)“PDI”作為汽車經銷商信息告知義務的正當性分析
所謂“PDI”(Pre-Delivery Inspection的英文縮寫),是指經銷商對未經注冊登記的“乘用車新車”在交付消費者之前所進行的售前檢查(3.5)。這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也是汽車行業獨特的服務,其目的是“為消費者提供一輛合格的車。”若檢測中出現任何問題,授權經銷商將依據汽車供應商的要求酌情進行技術處理,如采取校正故障、更換配件、必要時更換車輛等不同措施,從而使交付的新車達到汽車生產廠家的新車出廠標準。與通常的汽車維修并不相同,該指引規定,乘用車新車交付消費者時,應向消費者提供乘用車新車 PDI 檢查表(8.2.1),并詳細規定,乘用車新車交付消費者時,存在經銷商應主動向消費者告知的各種情形(8.2.2)。對于汽車經銷商在PDI檢測和修復汽車之后并未積極向消費者告知的行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若PDI檢測的問題及相應的“整理行為”(如經銷商交車前對油漆的拋光打蠟)顯著輕微,既不影響消費者的人身安全,亦幾乎不涉及消費者的實質性財產利益。如果經銷商未將這類信息告知消費者,則其不違反法定告知義務,但是侵害消費者的知情權。
但是,“PDI”所規定的信息告知義務并非不受法律規制。法院對于PDI的援引應當受兩個方面的限制:(1)PDI屬于指引性規范,對于經銷商的信息告知義務采取兩種方式:一是修復率低于乘用車新車整車市場指導價格5%的,指引進行了詳細的列舉;二是不屬于上述應當告知的項目,但是修復率超過乘用車新車整車市場指導價格5%的情形(8.2.2)亦應當告知。法院應當從消費者的締約目的、對汽車基本現狀的影響、經銷商獲取信息的成本以及消費者的可期待性,通過利益衡量判斷修復率低于乘用車新車整車市場指導價格5%的、PDI未列明的事項是否屬于經銷商應當告知的情形。(2)經銷商應當提請消費者對PDI檢測和修復項目的格式條款注意并予以說明,否則視為未履行告知義務。經銷商向消費者交付汽車時,通常以格式條款的方式向消費者告知PDI檢測情況及修復項目。依據《合同法》第39條第1款的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負有必要的提請注意和說明義務。作為格式條款的制作人和專家,經營者應當以合理的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并予以說明,否則該格式條款不構成合同的一部分。
二、汽車經銷商的締約欺詐及其構成
(一)締約欺詐的制度競合
欺詐須與事實有關,唯有對可客觀檢驗的事實作虛假陳述始可構成。因此,不僅主觀評價難以構成欺詐,對于將來事實的表述亦因無法判定真假而不成其為欺詐的基礎。從邏輯上看,欺詐的表現形態“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均以行為人負有“真實的信息告知義務”為前提。汽車經銷商的信息告知義務通常發生在締約階段,如何協調締約自由與信賴保護之間的緊張關系,是立法者規定締約欺詐時應當考慮的主要問題。《合同法》基于不同立場,對同一個締約欺詐行為分別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第42條)與合同欺詐(第54條)及行使撤銷權的法律后果(第58條)。前者不涉及合同的效力判斷,其所解決的是損害賠償問題,規范意旨既包括損失的填補,也包含著對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過失行為的抑制;后者系以維護締約意思形成自由為出發點,以采欺詐手段訂立的合同應否有效為核心而展開的。由于締約欺詐適用《合同法》第58條第3句規定的損害賠償時,限定為“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后因此所受到的損失”,因此在合同不成立、合同成立但不生效以及合同有效三種情形之下,《合同法》第58條不能適用,可以適用的是《合同法》第42條規定的締約過失責任。對于欺詐的文義與構成要件,除少數學者之外,主流觀點認為《民法通則》(第58條)、《民法總則》(第148條)、《合同法》(第54條)與“消法”(第55條)系采取相同的判斷,包括經營者的主觀要件、經營者的欺詐行為、消費者陷入錯誤而為意思表示以及欺詐行為與錯誤意思表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二)汽車經銷商欺詐的主觀要件
通常認為,欺詐必須是行為人故意或者惡意,過失不構成欺詐。如果經營者明確告知消費者汽車的瑕疵或者消費者知道該瑕疵(“消法”第23條),則可以排除經營者的故意。有學者認為,為保護“信息上的弱者”,應當緩和欺詐須為故意這一要件,從正面肯定以過失性誤導或說明義務違反為理由的合同撤銷權。還有學者認為,由于欺詐構成中的主觀故意要件與《合同法》第42條規定的締約過失中的過失要件的對立,合同法中的締約過失與欺詐制度對于“締約時隱匿信息或告知虛假信息”的情形作出了矛盾評價,形成了典型的制度競合。承認“過失欺詐”不僅可以使現有民法體系保持邏輯的順暢,避免《合同法》第54條第2款的規定淪為具文,而且能夠通過信息提供義務的實現,以保障消費者在合同領域的實質意思決定自由。
筆者認為,為了保持合同法體系內部的邏輯一致,“消法”第55條規定的經營者欺詐的構成應當以故意為要件,不應承認“過失欺詐”。主要理由在于:(1)德國法上,對于一方當事人陳述虛偽事實或者沒有告知真實情況只是出于過失,1962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認為,受誤導的合同當事人可以通過恢復原狀的方式行使廢除合同請求權,使締約過失責任的觸角延伸至對表意自由的保障(BGB NJW 1962,1198f)。由此產生體系矛盾:欺詐撤銷權僅適用于故意違反信息義務的情形,締約過失的合同廢除請求權適用于故意和過失兩種情形。該焦點實質上在于締約過失與欺詐在損害賠償問題上的評價矛盾。(2)我國《合同法》締約過失責任系移植于德國,相同之處在于:在類型上,締約過失責任不僅適用于合同未成立、合同有效,而且適用于被撤銷以及無效情形;在主觀構成上,締約過失責任不僅包括故意,而且涵蓋過失。然而,與德國學說不同的是,我國學說通常認為締約過失責任方式是賠償損失,并不賦予受欺詐方廢止合同的請求權。在理論上,通說認為締約過失責任并非獨立的責任,而是一種違反法定義務(締約人之間特殊注意義務)的侵權責任,原則上應當以一般過失為歸責原則和標準。既然締約過失責任屬于侵權責任,其法律后果很難涵蓋合同廢止請求權。(3)從比較法上看,所謂“過失欺詐”缺乏廣泛的支撐。日本民法對于欺詐要求故意,不承認過失欺詐。若信息對受欺詐方很重要,而欺詐方違反信息提供義務時,惡意推定為欺詐故意。在英美法上,不實陳述分為欺詐性的不實陳述、過失性的不實陳述和無過失的不實陳述。其中,欺詐性的不實陳述要求陳述人明知陳述內容虛假并希望以其誤導相對人,即存在誤導的故意。依據《國際商事合同通則(2010)》第3.2.5條的評論,欺詐行為是指有意使對方陷入錯誤,并從對方的損害中獲得利益。《歐洲合同法原則(2002)》第4:107條也規定, 欺詐可以通過陳述或不披露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是有意地欺騙,則這種陳述或者不披露就是欺詐性的。我國臺灣地區“最高法院”1998年度臺上字第1195號判決亦認為,“民法上之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于錯誤之故意。”(4)德國民法學界關于締約上過失責任的合同廢除請求權之爭論仍在繼續。如梅迪庫斯教授認為,由于締約過失責任有使《德國民法典》第123條規定的欺詐故意要件空洞化的危險,在相對人為不實表示時,通常應否認其享有締約上過失的合同廢除請求權。只有在當事人一方具有特殊的提供信息義務時,肯定締約過失合同廢止請求權的司法判例才是可以接受的。卡納里斯教授指出,僅以買受人受到對方有過失的誤導為由而承認前者享有合同廢除請求權,會破壞第123條的欺詐故意要件,從而導致合同撤銷的門檻從故意降至過失的危險。為避免此種局面,可選擇金錢損害賠償而非恢復原狀的方法。(5)若立法上肯定所謂“過失欺詐”理論,在體系上與懲罰性賠償制度難以銜接。懲罰性賠償制度旨在制裁和遏制經營者的惡意或故意違法行為,無論如何理解“故意”與“過失”要素,兩者的核心領域不可能發生交集。如果經營者的“過失”就可構成欺詐,意味著經營者在締約過程中只要有不實陳述或未盡告知義務的行為即可推定為欺詐,并向消費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除非經營者證明自己的不實陳述或未盡告知義務的行為系無過失。這勢必導致經營者與消費者的利益關系失衡。
對于汽車締約中的欺詐爭議,由消費者提供初步證據證明汽車存在與經營者承諾不一致或未盡告知義務的瑕疵。而后,由經銷商舉證證明(擬)交付的汽車不存在瑕疵或欺詐故意。對消費者提出的瑕疵要求盡到高度蓋然性標準,使法官形成完全確信后才會形成舉證負擔的轉移。如果汽車經銷商虛構或者隱瞞事實的理由并不具有正當性,即不能達到理性人的標準,則可以推定經營者具有欺詐的故意。
如果經銷商并未故意隱瞞約定汽車(尤其是進口平行車)的重要信息瑕疵,但是過失地給予錯誤陳述或者違反披露義務而不作陳述, 而這些信息對消費者購買汽車的決定又具有意義,有三種路徑可以救濟消費者的權益,以實現對所謂“過失欺詐”理論的功能替代:第一,依據《合同法》第42條第3項作為“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令經營者承擔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該條關于“違反誠信”的規定是締約責任的一般歸責標準,“違反誠信”與“過錯”在歸責標準方面具有一致性,都表現為對毋害他人的正當行為要求的違反,過錯本身即屬“違反誠信”。第二,若經營者過失違反法定信息告知義務,依據《侵權責任法》第2條并結合第6條,經營者過失侵害消費者的“知情權”,應當承擔恢復原狀、賠償損失的責任。例如經營者進行“PDI”操作更換配件后,雖然依據行業慣例經營者并不構成故意欺詐,但綜合各種情形,經營者可能過失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第三,依據《民法總則》第147條、第157條規定的“重大誤解”(錯誤)的規定撤銷合同,并賠償損失。欺詐和錯誤的相同之處在于受害人均是基于錯誤而簽訂合同的;不同之處在于欺詐中的錯誤是由對方有意造成的。比較三種救濟方式:締約過失與過失侵權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但是責任方式不包括廢除已經締結的有效合同;“重大誤解”雖可以發生撤銷合同的法律后果,但是以損失較為重大為必要。
(三)經營者的欺詐行為與消費者陷入錯誤而為意思表示具有因果關系
消費者因欺詐行為陷入錯誤之后而為意思表示,即經營者的欺詐行為與消費者陷于錯誤和訂立買賣合同具有因果關系。此處存在雙重因果關系,具體而言:(1)經營者的欺詐行為須導致或者維持消費者的錯誤。究竟是哪種錯誤并不重要。但是對于輕微瑕疵信息的隱瞞是否構成欺詐,司法實務認識不一。大多數情況下,經營者的欺詐使消費者對汽車的重要特征產生錯誤,或者是可以影響汽車價值的某種情形,或者涉及到其他對消費者購買汽車的決定具有實際影響的情形。即使經營者的欺詐行為并未對車輛質量和基本性能產生實質性影響,只要經營者違背信息告知義務并致使消費者陷入錯誤,同樣可以構成欺詐。(2)消費者的錯誤是其與經營者訂立合同的誘因。消費者沒有必要證明欺詐行為所導致的錯誤是其訂立買賣合同的唯一原因,只要證明錯誤對合同的簽訂產生一定影響即可。重要的是,消費者對經營者的虛假陳述或沉默行為具有信賴,在無該錯誤的情況下消費者根本不會或者不會在該時間或者不會以其他內容作出意思表示。若消費者知道事實情況,則不存在該因果關系。因為“知假買假者”并未因欺詐而“作出錯誤意思表示”,更何況經銷商的瑕疵擔保責任因消費者“已知瑕疵”而免除。
三、汽車經銷商懲罰性賠償的正當性及其適用
(一)汽車經銷商締約欺詐懲罰性賠償的爭議
如果汽車經銷商在締約過程中欺詐消費者,依據“消法”第55條第1句前者向后者承擔“退一賠三”的消費合同欺詐的懲罰性賠償。該條第2句屬于產品責任的懲罰性賠償,是《侵權責任法》第47條的特別規范。在汽車經銷商締約欺詐或同時引起產品責任競合的懲罰性賠償案件中,面臨著以下爭議:
第一,汽車尤其是高檔汽車的價值較高,若經銷商締約欺詐時,以汽車價值的三倍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對于經銷商而言過于嚴厲而有失利益的平衡。例如前述“賓利”案、“法拉利”案等,消費者索賠金額動輒數百萬甚至數千萬元,甚至超過商品房的價值。如此高額的懲罰性賠償,不僅會加重企業的負擔并可能導致企業不堪重負而破產,還會導致經銷商通過商品定價機制或其他辦法將賠償代價轉移給消費者承擔。有學者主張,價值高昂的商品房交易案件不能適用舊“消法”第49條,因為“雙倍”賠償將致使買賣雙方的利益關系顯著失衡,既不符合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經驗,也很難說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結果。鑒于商品房交易完全適用懲罰性賠償會顯失公平,2003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與“消法”第55條在賠償比例和基數上均不相同。上述限制規則對汽車尤其是豪華汽車交易的懲罰性賠償無疑具有借鑒作用。
第二,過高的懲罰性賠償或過寬的適用范圍不符合比例原則,可能會導致該制度的濫用,引發消費者過度的、缺乏效率的訴訟。懲罰性賠償不符合比例原則表現在兩個方面:(1)經營者賠償數額與消費者所受損失相比。如果經銷商明知汽車存在缺陷而出售給消費者,同時引起產品責任的競合,由于合同領域的懲罰性賠償與產品責任的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礎和倍數均不相同,若汽車標的價值達到百萬元以上,盡管合同締約欺詐的危害性要遠低于產品責任的危害性,但是很可能前者會超過后者。近年來,由于消費者運動的勃興,我國理論界有一股片面強調消費者的權利、忽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的激進主義傾向,并將消費者過度維權現象歸結于經營者缺乏誠信、市場機制不健全等原因。然而,“消法”對弱者進行傾斜性保護的權利配置,旨在追求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實質平等,而非鼓勵消費者濫用法律賦予的權利獲得不義之財并可能助長不勞而獲的惡習,從而產生新的不平等現象,對于大件商品如房屋、汽車尤其如此。這種收益的正當性值得反思。
第三,在合同法體系內,由于懲罰性賠償以汽車的價款為基數,可能致使因締約欺詐引起的合同撤銷與合同解除的救濟之間相互抵牾。一旦經銷商具有欺詐行為,無論是根本性的欺詐抑或是局部性的欺詐甚至輕微的違背信息告知義務(例如出售的汽車為展車),均可以導致三倍懲罰性賠償。然而,就合同的法定解除而言,《合同法》第94條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根本違約”或“重大違約”,但是卻使用了“合同目的不能實現”、“不履行主要義務”等表述,實際上相當于根本違約。根本違約的形式價值在于限制合同解除權,實質意義在于平衡違約方與非違約方的利益及社會利益。經銷商構成根本違約時,消費者解除合同后獲得的是期待利益的賠償。然而,由于締約欺詐不考慮根本違約,可能導致這樣的局面:經銷商的締約欺詐遠未達到根本違約的程度,但是消費者可以通過“消法”第55條獲得遠遠超過經銷商構成根本違約時其依據《合同法》第97條所能獲得的賠償。于此情形,締約欺詐引起的合同撤銷+三倍于標的價款懲罰性賠償遠大于根本違約導致的合同解除+違約損害賠償,這顯然構成法律體系內的評價矛盾。究其原因,懲罰性賠償著眼于違法行為的震懾和嚇阻,而非常規的權利救濟。
概言之,懲罰性賠償制度可能陷入雙重的尷尬困境:當商品價格過于低廉時(例如食品),十倍的懲罰性賠償也難以懲罰和遏制違法行為;當針對價款較高的汽車尤其是豪華汽車,適用“消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不僅侵襲民法上損害賠償責任的形式正義理念,產生“顯失公平”或“威懾過度”的后果,而且在法律體系內部產生價值評價矛盾。對上述問題加以檢討并提出相應對策,顯得尤為必要。
(二)汽車經銷商締約欺詐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分析
考察近十多年來“消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適用汽車經銷商締約欺詐的情形,我國司法審判實踐主要有以下兩種裁判方式:(1)懲罰性賠償以締約欺詐涉及的部分為基數。當經銷商的欺詐行為針對的是汽車的表面瑕疵欺詐或局部欺詐時,懲罰性賠償基數并非是汽車的整車價款,而只是相關部分的損失或整車價款的一定比例。(2)懲罰性賠償以新車的價款為基數。第17號指導性案例與前述案例基本相同,但是法院并未考慮所謂的表面瑕疵與局部欺詐問題,而是直接依據舊“消法”第49條判決以全車價款為基數的一倍賠償。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兩種不同的裁判思路與結論中選擇了后者。
顯然,只要汽車經銷商構成締約欺詐,無論是根本性的欺詐(如縮減汽車里程數、以劣舊發動機裝配汽車)、抑或表面瑕疵欺詐(如車門油漆損傷重新烤漆)或局部性的欺詐(如導航損害修理),還是輕微瑕疵信息的隱瞞(如有輕微劃痕車身的修復)所構成的欺詐,均應統一依整車價款的三倍進行賠償。這意味著,經營者的欺詐情節與主觀惡性程度與懲罰性賠償金額幾無關聯。這難以為懲罰性賠償提供正當化的解釋,與我國的損害賠償法理明顯相悖。考察美國的BMW v.Gore判決可以發現,經銷商不法行為的非難程度、獲利的可能性、受害的性質與程度等都被用來作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量定因素。在立法所允許的職權范圍內(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或目的性限縮), 法官應通過選擇特定的形式化解釋方案彰顯特定類型的社會行為選擇,以更好地維護社會生活秩序并增進社會公共福祉。在“消法”第55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存在多元化解釋可能的情況下,適用汽車這類價值較大的商品締約欺詐案件時,既要發揮懲罰性賠償的懲戒和獎勵功能,同時也為避免經銷商“退一賠三”所帶來的“罰不當罪”而使雙方利益關系的嚴重失衡的問題,應該以不同的標準計算經營者承擔懲罰性賠償的數額。
四、結 論
消費者權益保護是現代民法的重要表征。在汽車交易中,經銷商獲取和控制信息的條件顯著優于消費者,為追求兩者的實質正義,經銷商負有一定范圍內的信息告知義務:一是經營者不得故意或過失告知消費者錯誤或瑕疵行為;二是經營者不得故意或過失隱瞞可能影響消費者選擇權的重要信息。汽車經銷商信息告知義務產生于當事人約定、法律明確規定或交易習慣,除此之外,應當在經銷商的誠實信用原則與消費者的信賴保護原則的框架之下,從消費者的締約目的、對汽車基本現狀的影響、經銷商獲得消息的成本以及消費者合理期待四個方面,判斷經銷商是否負有信息告知義務。為保持合同法體系內部及其與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邏輯一致,“消法”第55條規定的經營者欺詐的構成應當以故意為要件,不應承認所謂的“過失欺詐”。如果經營者對消費者過失錯誤陳述或者違反信息告知義務,消費者可以分別通過締約過失責任、過失侵權以及重大誤解獲得救濟。
現代市場所構建的是經營者與消費者互利共贏的市場秩序。“消法”在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同時,也保護經營者的合法權益,而絕非僅僅偏重保護消費者或只保護消費者。否則容易產生消費者濫用法律地位以及索賠權營利化的趨向。汽車屬于典型的大宗商品,汽車交易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法院可以援引“PDI”,但是應當在誠實信用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的框架予以考量,并審查汽車經銷商在締約時是否提請消費者對PDI檢測和修復項目的格式條款注意并予以說明,否則視為未履行告知義務。為避免經銷商“退一賠三”致使雙方利益關系的嚴重失衡,應該以不同的標準計算經營者承擔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具體而言:(1)若經銷商在締約過程中實施的欺詐所涉及的是汽車的表面瑕疵或局部瑕疵,該瑕疵部分屬于汽車的非重要成分,并不足以構成根本違約的,應當以所涉表面瑕疵或局部瑕疵部分的價值或價格為基數計算3倍懲罰性賠償;(2)若經銷商在締約過程中實施的欺詐所涉及的是汽車的重要部分并構成根本違約,或者故意對消費者隱瞞汽車的制造缺陷、設計缺陷,或者故意不告知汽車的警示缺陷,應當以整體汽車的價款為基數予以三倍懲罰性賠償。
①典型案例如《360萬買到的法拉利是事故車,終審判決:退一賠一》,重慶:《重慶晨報》,2016年12月15日。
④[德]馮·巴爾等主編:《歐洲私法的原則、定義和示范規則: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高圣平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02頁。
⑤李適時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釋義》,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84頁。
⑥在“游淑容與重慶愛尚汽車銷售有限公司買賣合同案”中,法院認為,愛尚公司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應當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重慶愛尚汽車銷售有限公司代理購車合同》中約定的車輛原產地為意大利,而交付車輛原產地為美國,即最終制造地為美國……愛尚公司作為專業車輛銷售企業,在銷售車輛的過程中,應當對車輛的實際情況進行明確的說明和告知,其未能交付符合合同約定的車輛,并對交付車輛的實際情況進行了隱瞞,應認定構成欺詐。參見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終5636號民事判決書。這是全國首例平行進口車產地欺詐被“退一罰三”的判決。
⑦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第17號指導案例的裁判要點指出:“汽車銷售者承諾向消費者出售沒有使用或維修過的新車,消費者購買后發現系使用或維修過的汽車,銷售者不能證明已履行告知義務且得到消費者認可的,構成銷售欺詐。”
⑧[德]本德·呂斯特、阿斯特麗德·施塔德勒:《德國民法總論》,于馨淼、張姝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414~415頁。
⑨[德]維爾納·弗盧梅:《法律行為論》,遲穎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6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