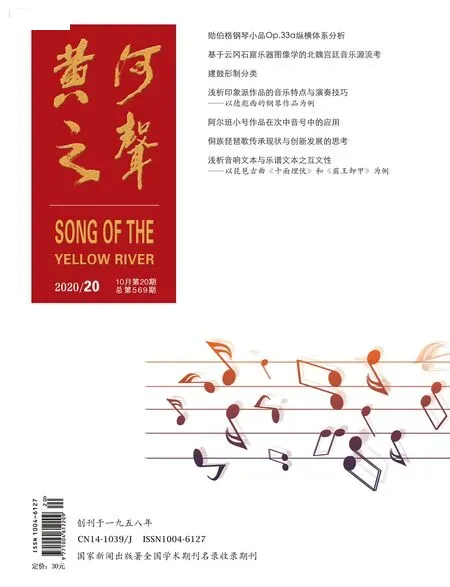勛伯格鋼琴小品Op.33a縱橫體系分析
◎ 孫斐然 (上海音樂學院)
勛伯格的鋼琴作品Op.33創作于1928-1929年間,是其為數不多的鋼琴獨奏曲之一,也是時間順序上最后一部獨奏作品,其中包含兩首鋼琴小品,Op.33a和Op.33b,皆為純粹的十二音序列作品。這部作品創作之時,勛伯格已寫作十二音序列音樂達十年之久,技法上的成熟在此顯露無疑。尤其是Op.33a,除序列方面頗具特色外,縱橫體系方面也有獨特之處,因此,本文將從“序列分析”、“結構分析”和“縱橫體系分析”這三方面分別進行論述。
與前人研究相比,本文的創新點在于詳盡的序列羅列、序列布局分析、奏鳴曲式思維與序列動機化思維分析、多方面縱橫體系分析以及多重對極布局分析。
一、序列分析
本曲共使用了46個序列,所有序列羅列如下(表1),原型序列為“P-?B”①(圖1):

圖1:

表1:

小節數 11 12-13 14-18 19-20 21-23?A③ 23-25④ 25-26⑤P-?B左手 R-E I-C I-?E RI-A⑦ I-?E右手 RI-A I-?E P-?B R-E⑥I-C P-?B

小節數27-27.5⑧ 27.5-小節末⑨ 27左手最后和弦-29.5 29.5-30.5 m.28-29.5 I-?B P-C左手 m.27-28.5⑩m.28.5-29.5 P-F I-F/P-F? I-F?右手P-?B R-E

小節數 30.5-31.5 31.5-32休止符前32休止符后-33E音 33A音-34 35-36右手 P-?A RI-B P-?B RI-A R-E左手 P-F RI-E I-?E R-E RI-A?

小節數 37-37.5 37.5-小節末 38-38.5 38.5-最后和弦前 38最后和弦-40右手 P-?B RI-A I-?E R-E P-?B左手 I-?E
通過分上述析可以看出Op.33a的序列使用極具特色,尤其體現在布局方面:
1、第一小節的三個和弦雖已使用序列原型,但并非按序出現,按照從前至后、從上至下的順序,這些和弦音所對應的序列號分別為:123468759121110。而按序出現、清晰易辨的序列原型直到第32小節才初次呈示,十分獨特。
2、本曲所用的46個序列中,大多數都未按原序出現,另外還有少量序列僅使用了部分序列音(如第28小節左手第二個和弦開始的“P-F”,僅用了第1-6號音)。
3、在使用頻率方面,序列P-?B(11次)、RI-A(8次)、I-?E(8次)出現次數最多,同一序列的多次出現具有動機式貫穿全曲的作用,是本作品的重要結構力。
4、本曲常采用不同形式配對使用的手法,如原型和倒影移位、逆行和倒影逆行移位相結合等,同時兩種形式的前一部分可結合產生組合性的派生序列。
總之,以上方面均體現出本曲“有序與無序”的對比與交織,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控制與隨意”的兩極布局。另外,不少段落的開頭和結尾都落于純音程,加之三個序列頭音“?B、A、?E”的反復出現(形成四度布局),從而具有一定調性感,“加強了無調性音樂與調性音樂的潛在聯系”?。
二、結構分析——結合傳統與現代
現代音樂的曲式結構已與傳統曲式大相徑庭,保留最多的當屬三部性結構。主題不再是判定曲式的主要因素,共同參與結構作用的因素大大增多,如節奏、音色、速度等。本曲也不例外,在以序列結構為主導的背景上形成了具備呈示、展開、再現的完整奏鳴曲式三部性結構布局。
呈示部為1-26小節,具有主副部對比的奏鳴特質。第1-9小節可視作主部主題,以柱式和弦接替進行,主要使用P-?B(3次)和RI-A(3次)序列,多次重復相同序列能夠增加穩定性。第10-13小節為連接部,織體、材料均來源于主部主題,以P-?B和I-?E兩個序列的縱向結合開始,每小節左右手聲部同時更換序列,共計出現6種不同的序列形式,相比主部主題更為動蕩不安,十分符合連接部特質。第14-24小節織體發生較大變動,同時使用術語“cantabile”,可視為副部主題,同連接部主題一樣開始于P-?B和I-?E兩序列的縱向結合。此處的序列使用重復音極多,序列變化頻率較低,每個序列持續時間不少于兩個小節,最長可達5個小節,體現了傳統副部般規整、穩定和典雅的特質。第25-27小節前半為結束部,同樣以P-?B、I-?E兩序列的縱向結合開始,結束于序列原型P-?B,較為穩定。
展開部從第27小節后半開始,結束于第32小節第一和弦。這部分序列變化頻率增加、多次使用不完整序列(如第27-28小節的I-F和P-F序列)、較少使用穩定序列(如前所述的P-?B、RI-A和I-?E),且序列順序較為混亂(如第30小節的P-?A),具有傳統展開部動力性強、穩定性弱、不斷分裂的發展特質。值得注意,呈示部中的序列變化通常為左右手聲部同時進行,而展開部的序列使用則更多為不同步改變,更具復調思維。
再現部為第32-40小節,其中第37-40小節也可視作尾聲。主部于第32小節再現,同樣使用P-?B和I-?E的縱向結合,隨后立刻再現呈示部主部中的RI-A。雖然主題旋律、織體不同于呈示部,但穩定序列的使用、原型序列的按序出現以及譜例中僅此一處的延長休止符都毫無疑問地指向再現。略過連接部,副部主題再現于第35小節,所用序列為R-E和RI-A的縱向結合,持續長達兩小節。其中,R和RI是對P和I的補充,同時1號音E和A與呈示部副部所用的?B和?E形成四度關系,具有傳統副部的回歸意味。
第37小節接替出現序列原型P-?B、RI-A與I-?E,第39小節使用全曲多處出現的P-?B與I-?E地縱向結合,具有總結全曲的尾聲作用。
通過上述分析,本曲的主要部分開始處都使用了原型序列“P-?B”與“RI-A”或“P-?B”“I-?E”的結合,具有極強結構意義,這是序列行使結構力的有力例證。同時,本曲在現代技法支配下仍與傳統奏鳴曲式結構產生了緊密關聯,體現出“現代”與“傳統”、“無調性”與“有調性”的緊密交織和兩極性布局。
三、縱橫體系分析
現代作品的縱橫體系分析包括音體系、節奏、連接邏輯、聲部進行等許多方面,其中音體系的橫向方面(序列部分)已于第一部分詳細論述,在此僅著眼于縱向和聲方面。
1、縱向和聲方面。現代作品中的縱向和聲根據是否含全音、大三、小三度、三全音及所含半音數量可分為五種類別?,本曲對此五類和弦均有涉及,其中1類最少僅1次,5類最多61次,其次為4類35次,3類21次,2類18次。5類和弦含有2個及以上半音,其大量運用具有明顯現代化特點,決定了連續不協和進行的音響效果。
2、節拍方面變化較多,包括4/4拍、2/4拍、5/4拍、9/8拍、6/8拍、3/4拍。其中呈示部與再現部節拍變化更為頻繁,展開部統一使用4/4拍,對比意味明顯。全曲的節拍變化與更替皆為左右手同步進行,無不同步現象。
3、橫向連接方面屬于完全的序列思維,不同序列形式的接替進行構成了本曲的橫向延展。
4、聲部進行方面。本曲的聲部數量不定,以三聲部為主,二、四聲部皆有出現,除呈示部副部主題開始處外,其余多為不平穩進行。副部主題基本建立于三聲部織體,值得注意第14-15小節中聲部形成了一條旋律帶,使用平穩進行。
結 語
Op.33a是勛伯格極具代表性的鋼琴作品之一,其序列性思維和寫作技法十分完善,雖然創作于二十世紀上半葉,但其中仍可見到不少傳統因素,從而形成“現代”-“傳統”、“有調性”-“無調性”、“控制”-“隨意”、“有序”-“無序”、“復雜”-“簡單”的多重對極布局。這部作品既是序列技術的里程碑式作品,亦是西方藝術音樂中的“高級藝術品”。
注釋:
① “P”為序列原型,“I”為其倒影形式,“R”為逆行形式,“RI”為倒影逆行形式。“P-?B”意為“從?B音開始的原型序列,下同。此種標記方式學自上海音樂學院學院彭程老師,比起半音標記法更為直觀便捷。
② “6E”意為第6小節的E音,下同。
③ 此序列延續至第23小節的右手E音和左手?A音。
④ 從第23小節左手?E音至第25小節第一和弦。
⑤ 該兩音列都自第25小節第一和弦以后開始。
⑥ 只有1-10號音。
⑦ 只有1-10號音。
⑧ “27.5”意為第27小節的前半小節左右,此處序列停留于小節中間的左手A音,下同。
⑨ 該序列開始于第27小節中間部分,結束于最后一個和弦之前。
⑩ 序列“I-F”開始于第27小節左手最后一個和弦,結束于第28小節左手第1和弦;序列“P-F”開始于第28小節左手第2和弦,結束于同小節左手第4和弦。
? 這兩序列均只使用了1-6號音。
? 序列“I-F”開始于第28小節中間位置,結束于第29小節第2和弦。
? 該序列缺少第5號音。
? 彭志敏《新音樂作品分析教程》,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 此分類系上海音樂學院彭程老師的研究成果,包含于2019-2020年度上海音樂學院碩博課程《現代和聲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