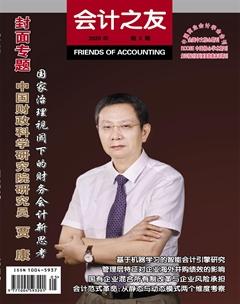可轉(zhuǎn)可贖優(yōu)先股的確認(rèn)與計(jì)量
王艷林 包瑞芝



【摘 要】 可轉(zhuǎn)可贖優(yōu)先股作為一種新興的融資方式受到許多上市公司的追捧,但是國際財(cái)務(wù)報(bào)告準(zhǔn)則與我國企業(yè)會(huì)計(jì)準(zhǔn)則對(duì)可轉(zhuǎn)可贖優(yōu)先股的確認(rèn)與計(jì)量未做嚴(yán)格區(qū)分,從而導(dǎo)致上市公司的“會(huì)計(jì)業(yè)績”和“真實(shí)業(yè)績”發(fā)生錯(cuò)配,直接影響到投資者對(duì)上市公司市值的正確判斷。小米集團(tuán)在營業(yè)收入和營業(yè)利潤均處于持續(xù)增長的狀態(tài)下,卻因可轉(zhuǎn)可贖優(yōu)先股公允價(jià)值變動(dòng)確認(rèn)為金融負(fù)債而產(chǎn)生巨額“虧損”。基于此,文章提出可轉(zhuǎn)可贖優(yōu)先股會(huì)計(jì)確認(rèn)與計(jì)量的三種改進(jìn)方法:其一,視為復(fù)合金融工具,分別確認(rèn)負(fù)債與權(quán)益;其二,確認(rèn)為金融負(fù)債,但其公允價(jià)值變動(dòng)計(jì)入其他綜合收益;其三,確認(rèn)為金融負(fù)債,披露非國際財(cái)務(wù)報(bào)告準(zhǔn)則(Non-IFRS)業(yè)績指標(biāo)。
【關(guān)鍵詞】 可轉(zhuǎn)可贖優(yōu)先股; 小米集團(tuán); IFRS; 企業(yè)會(huì)計(jì)準(zhǔn)則
【中圖分類號(hào)】 F27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1004-5937(2020)05-0133-05
一、引言
優(yōu)先股兼具股權(quán)和債權(quán)的雙重屬性,是“像股的債”,也是“像債的股”[1]。對(duì)于優(yōu)先股股東而言,可以將優(yōu)先股視為金融資產(chǎn),而對(duì)于發(fā)行企業(yè)而言,優(yōu)先股到底要確認(rèn)為權(quán)益還是負(fù)債,國際財(cái)務(wù)報(bào)告準(zhǔn)則(IFRS)和美國公認(rèn)會(huì)計(jì)原則(US GAAP)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并不相同。IFRS 32規(guī)定,如果金融工具的發(fā)行人具備在潛在不利條件下將現(xiàn)金或其他金融資產(chǎn)交付于持有人的義務(wù),那么這種金融工具就應(yīng)該作為金融負(fù)債列報(bào),后續(xù)公允價(jià)值變動(dòng)計(jì)入當(dāng)期損益,而US GAAP則根據(jù)破產(chǎn)風(fēng)險(xiǎn)和權(quán)益價(jià)值來界定債務(wù)與權(quán)益,只有公司強(qiáng)制破產(chǎn)清算的索取權(quán)才能歸類為債務(w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