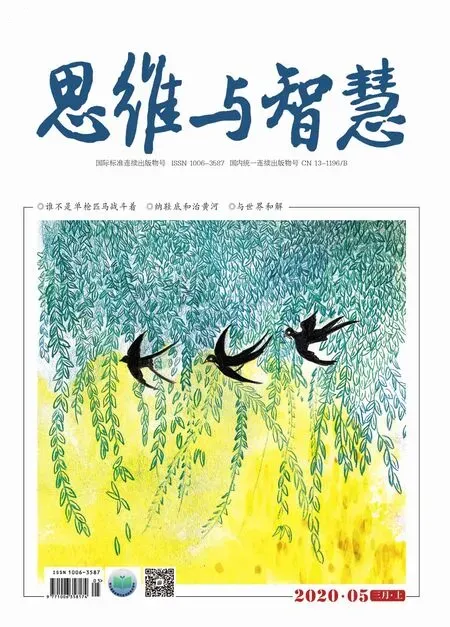清與濁
●葉春雷

儒家人格,涇渭分明。一個人,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清,就是濁,其間容不得一絲兒茍且。說白了,“喻于義”的君子,就是清;“喻于利”的小人,就是濁。當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的時候,也就在昭告天下:我是“喻于義”,你們都“喻于利”。
道家人格與此不同。老子言:“大白若辱。”這明顯表明,道家不是“非清即濁”的二元論。在道家看來,純粹的清是不存在的,清中自然含藏著濁。且只有含藏著濁的清,才可保持長久。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老子言:“察見淵魚者不祥。”老子不是叫人萬事睜只眼閉只眼,老子只是強調,不是每一件事,都必須爭出個子丑寅卯的。含藏,包容,才是人生正義。
讀《紅樓夢》,發現寶玉的高明之處,是論人論史講究實際,跳出了單純道德論的框架。寶玉說:“那些個須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者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庚辰本有綺園的眉批曰:“玉兄此論大覺痛快人心。”可見寶玉說出了大家的心聲。不顧實際,只想圖個清名,這是純粹的道德至上。對于實際,其實無補費精神。
所以儒家只顧清名的政治觀,在曹雪芹的筆下,遭到撻伐,是歷史的巨大進步。歷史是復雜的,人性也是復雜的,不是簡單的“清濁”二字所能概括。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談及海瑞,曾說:“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縱使海瑞清正廉明,官至二品,死后僅留下白銀十余兩,不夠殮葬之資,但他的所作所為,無法被接受為全體文官們辦事的準則。說白了,他就是個另類。
綜觀歷史,我們發現,在一個法治不健全的時代,單純憑借自己的清廉,想成就事功,實在于事無補,所以明代大學士張居正,也有他不得已的地方。標榜清廉不如標榜法治,這是歷史的深刻教訓。而從做人的角度,以清高自許,也容易將自己引入孤立的境地。《紅樓夢》中黛玉“孤標傲世”,不比寶釵“隨分從時”,結果非常被動,人生之悲,無過于此。
《菜根譚》言:“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歸己,可以韜光養德。”這段文字,與老子“大白若辱”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清節戾名,過分高揚,會引來眾人嫉恨,謠諑紛紜,身在是非窩中,容易成為眾矢之的。而引些辱行污名,歸到自己名下,反而能如沙漠中的動物,給自己涂上一層保護色,從而避免被天敵獵殺。道家的智慧,就是“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自然,我們肯定道家生存的智慧,肯定做事要符合實際,不能一味膠柱鼓瑟,標榜清高,也不能將儒家的道德論完全推倒。儒家清濁分明的人格,也有至大至剛的一面,充滿一種灑落的浩然之氣,儒家“舍生取義”的人格風標,令人高山仰止。
至清很難做到。人性的復雜,決定了人見得陽光的一面,也有不大見得陽光的一面。商鞅不就是利用人們對軍功的欲望,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嗎?所以“濁”也有可資利用的價值,不可一概而論。人類歷史的進步,很多時候,就是政治家順應歷史潮流,因勢利導,將百姓紛繁的欲望引導到一個正確的方向。中國當代改革開放的成功,不也源于對百姓物質和精神上欲望的滿足嗎?
所以對待清濁,應該有一個辯證的動態觀。清可以變成濁,濁也可以澄清。清中自有濁,濁中也有清。清濁涇渭分明的人生,事實上是不存在的。至清有其弊害,至濁自然更該鄙棄。只有在保持清的底色基礎上,靈活處理清濁關系,才能既保全自己,又實現既定的人生目標。
唐人杜甫《佳人》詩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如果離開“山”,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清”,這樣的“清”,實在太脆弱,不要也罷。真正意義上的“清”,應該如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