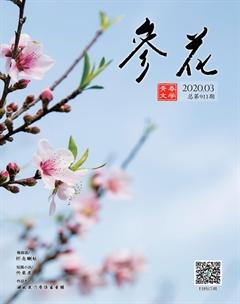那年的正月
郭朝軍
一
娘是一九九一年的正月十九去世的,如果活到現(xiàn)在,算起來應(yīng)該是七十九歲。
我清楚地記得,那年的正月十六,我堂妹結(jié)婚,作為娘家人,我們送她出嫁。清早,爹卻喊我們,說娘的半身沒有知覺,讓我們送娘到縣醫(yī)院。
我和哥哥及三弟趕到爹娘住的屋里。娘躺在床上,兩個(gè)妹子已經(jīng)幫娘穿好衣服。我們喊了幾聲“娘”,娘嗚啦嗚啦地低聲應(yīng)著。
爹說,娘半夜起來解手,是一頭暈倒在地面上的,由于是半夜,我們又在煤礦上班,怕我們累,就一直堅(jiān)持到天明。
我們連忙在架子車上鋪好被褥,將瘦弱的娘抱了出來放在鋪好的被褥上,哥哥前邊駕著車把,我們用力地推著兩邊的車轅,向十六里開外的位于縣城西關(guān)的人民醫(yī)院趕去。
到了縣醫(yī)院,給娘做了X光片,醫(yī)生開了住院手續(xù)。這時(shí),我們才知道娘得的是腦血栓。
二
娘是性格要強(qiáng)的人。
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條件,爹從外婆家背回來二十多斤大豆,用了生產(chǎn)隊(duì)的一孔土窯洞,安了一盤石磨,磨起了豆腐,推磨時(shí),是爹、娘和哥哥與姐姐。我和弟妹年齡小,只能打打下手。現(xiàn)在想想,那時(shí)的父母頂多也就三十來歲。豆腐磨好后,或是爹,或是娘,用獨(dú)輪車推著豆腐,踏著晨曦,聽著狗叫聲,沿著荒野小徑趕到鄰村,以物換物的方式將豆腐換成大豆、玉米或紅薯干。我曾和娘一塊兒去東嶺的趙村和王村、以及嶺上南邊的龍尾溝換過豆腐,我年紀(jì)小,推獨(dú)輪車肯定不行,都是娘推著,遇到上坡的時(shí)候,我用一根繩子吃力地拉著,給娘減輕推車時(shí)的力氣。到了鄰村,娘的一聲“割——豆——腐——”,穿過村子的農(nóng)舍、樹木,傳出老遠(yuǎn)老遠(yuǎn)。
有拿著豆子換豆腐的女人會(huì)問娘,這個(gè)孩子是誰?
娘會(huì)中氣十足地說:“俺的老二,上高中呢。”
那女人會(huì)說:“長(zhǎng)得真好,說媳婦了沒有?”
娘會(huì)接過話頭,問:“你給他說一個(gè)?”
接著是倆人和其他來換豆腐或看熱鬧的人們哈哈大笑。
我呢,滿臉通紅,心里埋怨娘怎么那么多話。
三
娘昏迷不醒,問主治醫(yī)生,主治醫(yī)生說如果天氣暖和了會(huì)有希望。可過了春節(jié)才立春,寒冷的天氣還會(huì)好到哪里去?醫(yī)院條件也差,沒有空調(diào),沒有暖氣,我的心里一緊。
正月十九,六舅來醫(yī)院看望我娘。見到我娘在病床上躺著,他喊著娘的小名“妞”,一連叫了幾聲。六舅看妹子沒有應(yīng)聲,淚水從眼眶里不斷線地涌了出來,一看六舅落淚,我們的淚水不聽話地都涌了出來,兩個(gè)妹子更是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
六舅把我和哥哥喚出病房外,對(duì)我們說:“把你娘接回家吧。”哥哥沒說話,我說:“舅,讓俺娘在這里治病吧。”六舅說:“你們真不聽話哩,醫(yī)生說了這病很難治,咱有多少錢得往里填還?”爹本來就站在不遠(yuǎn)處,聽到六舅這樣說,竟蹲在地上,“嗚嗚”地哭了起來。
六舅勸歸勸,我們沒有讓娘出院,我們都在盼那一線的希望。可就在那天晚上的九點(diǎn)多,娘真的咽了氣。三弟在漆黑的夜里騎著自行車回家報(bào)信,大姐、嫂子及兩個(gè)妹子幾個(gè)人到街上的估衣鋪買娘過世后的鋪金蓋銀和壽衣。
娘終于回到了家里,不過是以這樣的方式,可就是這樣的家啊,娘也只是匆匆過客,再過幾天,埋入黃土,與我們?cè)匐y相見。
回到家后,娘還是被我們護(hù)送到她住院前躺過的床上。我們要趁著她身子還有余溫時(shí),趕緊把她去世時(shí)要穿的衣服穿上。
換衣服時(shí),她的最親近的兒子、閨女和媳婦圍在身旁給她脫衣、用溫水擦拭,讓她干干凈凈地走,在擦拭的當(dāng)間,我看到娘為了這個(gè)家已累得骨瘦如柴的身體和干癟的乳房,我的淚水好像不斷線的珠子一個(gè)勁地往地上炸。
四
我們小的時(shí)候,爹和娘總是想辦法“扒擦”。春上,河里的楊樹剛有了鵝黃,或坡上的洋槐樹潔白的洋槐花開得一咕嘟、一串串,滿樹正濃的時(shí)候,他們會(huì)拿上鐮桿(一根長(zhǎng)木桿,把鐮刀安裝在桿的稍部),喊上我們,去捋樹上的嫩楊葉和洋槐花,反正什么葉子能吃就弄什么,什么花能吃就“掰”什么。夏天,麥子剛收罷,我們就頂著烈日去麥地里拾麥穗,一直到了玉米苗從麥茬壟里露頭。揉揉搓搓,也能拾上三四十斤麥子。秋天,隊(duì)里的各種莊稼前腳收罷,娘就帶上我們兄弟姊妹的一兩個(gè),反正是看見誰帶誰,到已經(jīng)收獲后的地里遛紅薯,遛棉花桃,遛煙桿頂部的煙葉,甚至?xí)谏a(chǎn)隊(duì)挖紅薯前,到地里拽紅薯葉。棉花桃拽回來后曬干,如果桃嘴還沒有咧開,就用錘砸開,把沒有綻放的花疙瘩拽出來,拿到軋花機(jī)鋪彈彈軋軋給我們做棉襖棉褲。煙葉弄回來曬干后捆成“把”,拿到煙站賣“末級(jí)煙”。紅薯葉曬干后儲(chǔ)備起來當(dāng)作冬天的菜肴。
聽同村的雙進(jìn)母說,娘在修瓦窯溝水庫時(shí)非常賣力氣,一個(gè)人能挑四塊土坯,一塊土坯就有三四十斤重。當(dāng)時(shí)她說時(shí)我也不在意,現(xiàn)在想想,娘才一米五五左右的個(gè)子,瘦弱的她挑了一百六十斤還多的重量,要不是為了能多掙些“工分”,說什么她也挑不動(dòng)那么多的東西。娘就是因?yàn)樽优嗟耐侠鄱钢Я藲q月。有時(shí)候想想在娘的生前我們還會(huì)和她頂嘴,真想扇上自己幾個(gè)耳刮子。
五
抬草鋪、裝殮、上供,娘去世后的一切禮儀都要做,特別是上供時(shí),爹到娘的棺材前磕了三個(gè)響頭,以表示對(duì)娘為這個(gè)家庭所做的功勞無以為報(bào),只有靈前磕頭以表感謝之意。如今想起來,爹給娘磕的幾個(gè)頭也應(yīng)該。娘不僅為我們,也為爹遮擋了不少風(fēng)雨。
在出殯的前一天,是大祭。
當(dāng)主事的讓我們也找人寫一篇祭文時(shí),我想,我應(yīng)該親自為娘寫一篇祭文了。寫的當(dāng)間,我和大哥邊回憶娘的生前往事,邊在紙上斷斷續(xù)續(xù)地下筆。娘對(duì)我們的養(yǎng)育之恩,使我們終生難忘。寫的當(dāng)間,我和大哥是泣不成聲。有人說,父母在有來路,父母不在,只有歸途。我卻有自己的一番見解,有娘在,我們永遠(yuǎn)是孩子;沒有娘了,我們就成了大人。
靈前大祭時(shí),靈棚前的人很多。有同村的人,親戚,還有娘的娘家哥、嫂子和侄子及侄媳婦們幾十口子人。念到祭文時(shí),我淚眼蒙眬地掃了一下周圍,觀看的人中,有的暗自神傷地抹淚,有的竟抽抽噎噎地哭了開來。也許是這篇祭文真正地激活了他們內(nèi)心的柔弱之處。
母親的靈柩在一片哀泣和嗩吶聲中,急匆匆地穿過村東的二○七國(guó)道,向坡崗上的祖墳所在地蜿蜒而去。老天也想湊這場(chǎng)熱鬧,竟然一片一片地飄起了雪花。
- 參花·青春文學(xué)的其它文章
- 家鄉(xiāng)松
- 此地一為別
- 一縷陽光
- 曾經(jīng)滄海
- 當(dāng)時(shí)明月在
- 苦曲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