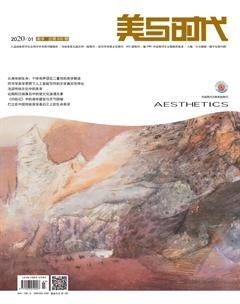柏拉圖與尼采的“嬗變”
摘 ?要:在丹托《尋常物的嬗變》關于藝術定義的思考中,“再現”與“解釋”一經一緯,共同組成了藝術的新定義。而構成藝術定義的這二維,都各自有其思想淵源:“再現”根植于“可感-可知”世界的二分,“解釋”則發生在不可見的“可知世界”中。為解決自柏拉圖以來世界二分所導致的困境,丹托提出“藝術終結于哲學”,用哲學收編藝術,從而整合成一個“可知世界”。然而,丹托修正后的“可知世界”并不像柏拉圖或黑格爾所理解的那樣,由一個單數的超然實體所宰治,而是像尼采理解的那樣,由各種流變爭勝的現世理論相互生成。
關鍵詞:丹托;尋常物的嬗變;藝術定義;柏拉圖;尼采
一、丹托對尼采的“誤讀”
在《尋常物的嬗變》中,丹托借尼采之口表述了“再現”概念的發展史,從“再次-出場”(re-presentation)到“代表”(represent)。再現的早期含義“再次-出場”適用于狄奧尼索斯的秘儀中,此時信徒們相信“神真的是在‘出場(present)的字面意義上現身在場”[1]24,秘儀中狄奧尼索斯的外觀和實在是同一(identity)關系。再現的后期含義出現在由狄奧尼索斯秘儀所發展出的悲劇中,狄奧尼索斯神已經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表著(represent)狄奧尼索斯的人。此時所謂的“再現”,“就是一物在另一物的位置上,就像議會中的代表們(representatives)代表著我們一樣”[1]21,外觀和實在是指稱(designation)關系,猶如語言與實在一樣。
丹托在這里對尼采進行了至關重要的傾向性誤讀。在尼采的《悲劇的誕生》中,悲劇是極具張力的二元綜合體,由阿波羅(理性,能識破假象的個體化原理)和狄奧尼索斯(迷狂,在忘我中復歸為一的沖動)各執一端,在費力拉扯中塑造成型[2]19。而丹托在再現的“代表”含義上所談論的悲劇,取的更多的是《悲劇的誕生》中由歐里庇德斯和蘇格拉底所代表的那種世俗、理性、冷靜而又樂觀的類型。這在尼采看來,恰好是殺死悲劇的元兇,絕非形成悲劇的機理[2]90-107。進言之,尼采所言的悲劇,大約對應丹托所言的“再現”的早期含義,即秘儀中“再次-出場”的狄奧尼索斯,不區分外觀和實在[2]58-59;而在丹托對尼采的轉述中,悲劇所對應的就變成了再現的后期含義“代表”,區分外觀和實在,這與《悲劇的誕生》的原意恰恰相反。
此番對應的偏差自然也導致了對“再現”概念發展史認識的巨大差異。在《悲劇的誕生》里,從“再現”的早期含義墜向晚期含義意味著西方文明沒落的開始:蘇格拉底這個“新生惡魔”的出現將狄奧尼索斯的迷狂鎮壓在了冷靜的理性之下。丹托雖認可這一思想史的重大轉變,不過他是站在哲人蘇格拉底的立場來積極言說的。丹托以為,“再現”從早期含義到晚期含義,意味著藝術的誕生:人們從此“不再對再現一詞做巫術的理解,而是對再現一詞做語義的理解”[1]95,“再現品從巫術式的道成肉身轉變為單純的符號”[1]94。于是,藝術作為和現實對立的東西,和哲學一同出現了。丹托絕不像尼采那樣唱衰,他樂觀地指出,一旦人們可以區分現實和其他事物(如外觀、幻覺、再現、藝術),覺察到藝術與世界、語言與世界、外觀和現實存在對立,藝術和哲學便由此誕生了。此外,既然藝術區別于現實,猶如語言區別于現實,那么藝術的本體論和語言的本體論便位列同一類,這就為在藝術領域運用語言分析的規則和邏輯打開了方便之門。
尼采痛斥這種將世界劃分為二的觀念:“我擔心我們擺脫不了上帝,因為我們還相信語法”,“把世界分為一個‘真實的世界和一個‘虛假的世界……都是僅僅是頹廢的一種暗示——是衰敗的生命的一個征兆。”[3]這樣看來,信奉世界二分的丹托似乎站到了尼采的對立面。但丹托和尼采,或者說和具有“尼采”特質的諸多觀念,又是那樣親和。譬如當他將人作為一種再現系統來理解時,便與尼采的視角主義酷肖之至,都旨在呈現一種視角化的觀看之道;并且在丹托的早期專著《作為哲學家的尼采》中便設有專章“透視主義”(Perspectivism)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又譬如,丹托在《在藝術終結之后》中所謂的“后歷史時期”“藩籬的移除”幾乎可以看作是尼采在永恒輪回下移除“大地界石”以達到“無限肯定”效果的翻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視角主義”和“無限肯定”都是尼采“一個世界”的表征,丹托想要站在“一個世界”的全然對立面去與其表征相親緣,勢必也要對他自己“世界二分”的觀念進行改造。
二、丹托對柏拉圖的“改造”
丹托將藝術和哲學的誕生奠基在“世界二分”的基礎之上,并將之歸功于古典理論的榮耀:
古典理論的極大榮耀,就在于它擺正了藝術與現實的關系,其唯一的錯誤之處或者說狹隘之處在于,它把再現局限在摹仿的范圍之內,這使得藝術的再現論無法容納那樣一種藝術品,它可被理解為是再現性的,卻明顯不是摹仿性的。[1]100
從柏拉圖的“理念論”中能夠清晰地看到古典理論的榮耀:它清晰地區分出了兩個世界,一張用來睡的床無論如何都不同于一張理念的床。丹托所理解的古典理論的兩個世界,是藝術和現實二分的世界,然而用這種二元的范疇去理解古典理論,無疑也是簡化的。在《理想國》第六卷中,柏拉圖給出了著名的“線喻”:首先將世界按比例分為可見世界和可知世界,然后再以同樣的比例從低到高在這兩個世界中分出影像、實物、數理對象、理念四個部分[4]509D-511E。而丹托所言的其“錯誤或狹隘之處”主要發生在“可感世界”中“影像”和“實物”的階段。在蘇格拉底的鏡喻“藝術是現實的一面鏡子”[1]10中可見,他將摹仿理解為藝術的全部,并且這種摹仿建立在和對象的相似性基礎上。顯然,在“影像”與“實物”這兩個對立范疇內不能解決無對象的摹仿品的問題。為應對挑戰,丹托以藝術品和對象的“關于性”(aboutness)替代了“相似性”(resemblance),并輔以對三種“再現方式”的系統分析,以“再現”替代了“摹仿”,由可見性到可知性,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古典理論的缺陷問題。要之,在丹托看來,古典理論因其摹仿概念,而停留在“可感世界”中“影像”和“實物”二分的基礎上;而他更新后的“再現”觀念,則重啟了“可知世界”的不可見向度,真正在原初柏拉圖的意義上達到了“可知世界”與“可感世界”的二分。
由此觀之,丹托和柏拉圖,或者說和具有“柏拉圖”特質的諸多觀念也是那樣親和,在上述“世界二分”之外,其“藝術界”概念、對于“解釋”的依賴,都和崇尚“可知世界”的柏拉圖相當親近。而一旦丹托進入了具有“柏拉圖”特質的問題域,那么柏拉圖理論的便利和問題都會接踵而至。凡此種種,再綜合上一節丹托對尼采的青睞,他便好像置身于哲學史兩極的風暴之中。筆者以為,丹托在其早期著作《作為哲學家的尼采》中對尼采的理解,可以作為其糅合尼采元素和柏拉圖元素的先聲:
如果說尼采堅持了某種理念論(idealism),那就是一種動態的(dynamic)理念論。 [5]
這里的dynamic idealism之于藝術哲學,可以做這樣的理解:一個柏拉圖的“可知世界”是必要的,理念論(idealism)不能偏廢。但這個可知世界需要由各式各樣相互矛盾、斗爭且存在在歷史之中的、流變的(dynamic)理論構成。接下來我們試圖從丹托津津樂道的哈姆雷特為刺探叔叔而導演的假戲《貢扎古之死》入手,進一步闡釋丹托對于柏拉圖“可知世界”的“改造”。
三、藝術作為一場理論的戰斗
如果將哈姆雷特的假戲理解為再現性的,它“關于”或者說“指稱”了僭主殺父娶母這一現實。那么,這出戲就不再是一出尋常的戲了,它悄無聲息地完成了變形(transfiguration),但這種變形并非肉眼所能覺察:
哈姆雷特:“你什么都沒有看到嗎?”
皇后:“什么都沒有,但這就是我所看到的。”[6]
哈姆雷特通過亡靈得知了是叔叔殺害了父王這一真相,克勞狄斯本人則是由于親身實踐了殺害國王而知道這一真相,而皇后由于把握不到《貢扎古之死》所指稱的事實,所以她“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并不擁有這份認識,除了演的戲以外什么也沒看到。于是,哈姆雷特和克勞狄斯共同處于一種不可見的場域之中,正是在這一場域之中,這出假戲的變形才能被識別,從而激起主體的反應。
以上是丹托講述《哈姆雷特》這段故事的版本。哈姆雷特和皇后在第三幕第四場的這場對話雙雙出現在其《藝術界》的文首和《尋常物的嬗變》的卷首。如果讀者只是對《哈姆雷特》有一個簡單的印象,再受了丹托上下文的影響,就會輕易地認同上邊哈姆雷特問皇后“你看到什么”的潛在對象正是那出哈姆雷特用來試探僭主的假戲。然而實際上,此時哈姆雷特問皇后的語境是,你有沒有看到我父王的鬼魂。在莎士比亞的原版中,沒能看到自己丈夫的鬼魂正是皇后不能得知信息,從而看不懂《貢扎古之死》的原因。丹托版本的講述仿佛是在嘲弄看不懂《貢扎古之死》的皇后,是對于最終結果的現象描述。而在原本的故事中,皇后看不見幽靈,所以她喪失了進入與哈姆雷特和克勞狄斯共處同一種認識場域的機會。至此,如何才能“看見”不可見的幽靈,成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莎士比亞沒有給出答案,還沒等丹托說出他的“藝術界”,蘇格拉底便搶先兩千年回答了:因為皇后沒有完成“靈魂轉向”。所謂“靈魂轉向”就是一項讓靈魂從變化的可感世界中轉離,從而觀看可知世界的學問。這一學問發生于事物讓靈魂迷惑不解的時候,尤其是一物和其相反者一樣顯得是一個的時候[4]518D-524E。到這里似乎有點似曾相識,因為丹托標志性的命題“兩件東西一模一樣,為什么一件為藝術品而另一件不是”便是觸發靈魂轉向的標準問題。從這個角度同樣可以理解為什么丹托說布里洛盒子的出現,標志著“藝術終結于哲學”,因為靈魂此時已經不再關注可感世界,朝向可知世界了。
蘇格拉底轉向的可知世界,最終朝向“善”。“善”屬于可知世界中理念的最高級。《理想國》中關于“善”有著名的“日喻”:在可感世界中,太陽被視覺看見,同時使得可見事物被看見;同樣,在可知世界中,善被理知,同時使得可理知物被理知[4]509C。由于丹托處于“上帝死了”之后,這使得他不能夠像蘇格拉底一樣再造一個形而上域。于是他只能管轉向的地方叫“藝術界”,在其中,藝術史和存在在歷史之中的藝術理論——或者統稱為“解釋”——起著“善”的作用。由此,這個“善”不再是超驗之物,而是一個全然經驗的化身。能夠完成靈魂轉向的人在《理想國》中僅為少數一出生就被遴選的哲人,同樣,在丹托這里,嬗變(transfiguration)也僅向那些符合再現條件、符合藝術歷史、符合藝術理論的少數物什敞開。
由此可見,丹托牢固地將其藝術哲學建立在“可感-可知”的二元分離、可知世界主宰可感世界的觀念之上,這可以說是他理論中的柏拉圖面向。但另一個方面,丹托的二元分離又是嚴格“在歷史之中”的,他只能在后形而上學時期的“一個世界”里展開論述。所以,丹托在其之后的論述中,部分出于規避“兩個世界”的原因,他參照黑格爾提出了“藝術終結于哲學”這一觀點,將“可感世界”整合進了“可知世界”之中。
但丹托畢竟不是黑格爾,黑格爾的“實體”也好“絕對精神”也罷,背后都是其為糅合“知識-信仰”這一斷裂所精心營造的設計,然而丹托并沒有黑格爾的宗教抱負。再者,丹托是多元主義的,并不像黑格爾由一個單數的“精神”展開而化成萬物。所以筆者以為,在“一個世界”問題上,丹托之于黑格爾大抵只是習其形而沒有習其神,丹托在這一問題上真正的思想老師,應該是尼采。當然,尼采有很多面向,如果以后現代為進路,則會得到一個否定性和解構性的尼采,而一旦讓丹托認這個尼采做老師,就自然會得到一部分人攻訐丹托時所言的虛無主義結論。不過還有另一個肯定性和建構性的尼采,他旨在通過對流變世界的無限肯定以求達到對虛無主義的克服。當查拉圖斯特拉擁抱永恒輪回時,他便挪開了大地所有的界石(Grenzsteine),將萬物從目的論的枷鎖中釋放,由是,一切曾在與現在都得到了肯定[7]。與此相應,丹托在其后期的《在藝術終結之后》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后歷史時期告別了排他性的歷史“大敘述”,讓一切藝術風格都得到了平等的肯定:今日不再有任何歷史的藩籬,再也沒有什么事物會被排除在外,任何事情都是容許的。但“這不表示藝術作品沒有高下優劣之分,而是好與壞的判準,與它們是否屬于某種正確的風格或是否符應某個正確的宣言無關”[8]。
那么正確的判準是什么呢?此番“一個世界”運行的原理是什么呢?丹托在其藝術哲學的論述中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但筆者以為,在他對尼采的闡釋中已經暗含了解答。在《作為哲學家的尼采》一書中,丹托這樣理解尼采:世界不存在形而上學的真理,意志斗爭(Will-to-Power)所激發的諸解釋(interpretations)為其賦予了形制。正是在意志與意志、解釋與解釋、哲學與哲學的廝殺較量中,世界得以在生成中持存,而不至于墮入虛無[5]79-81,210-214。在丹托這里,既然藝術已經被哲學接手,哲學化的藝術就必須進入這場解釋的競賽之中,在理論的戰斗中爭勝。這樣,在丹托的“一個世界”即“藝術界”中,“諸解釋”雖然扮演著柏拉圖“善”的功能性角色,但它卻是完完全全動態、開放和生成的。
丹托堅持“可感-可知”世界的二分,并以為不可見的“可知世界”在藝術定義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解決兩個世界的矛盾,丹托提出“藝術終結于哲學”,用哲學收編藝術,整合成一個“可知世界”。但這個“可知世界”并不像柏拉圖和黑格爾所理解的那樣由一個單數的實體所宰治,而是像尼采理解的那樣,由各種流變爭勝的理論“生成”。
晚年丹托曾在《美的濫用》中說:“哲學是場戰斗,它用我們所能找到的最基本常見的語言文字表達我們人類究竟是什么。”[9]藝術又何嘗不是一場戰斗呢,它們爭相為我們自己再現自己,像鏡子一樣映照出關于人形形色色的真相。
參考文獻:
[1]丹托.尋常物的嬗變:一種關于藝術的哲學[M].陳岸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2]尼采.悲劇的誕生[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3]尼采.尼采著作全集 第6卷[M].孫周興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94-96.
[4]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5]Danto. Nietzsche as philosopher[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214.
[6]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 第5卷[M].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54.
[7]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247、296、351.
[8]丹托.在藝術終結之后:當代藝術與歷史的界限[M].王春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41.
[9]丹托.美的濫用[M].王春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103.
作者簡介:黎耀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哲學、藝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