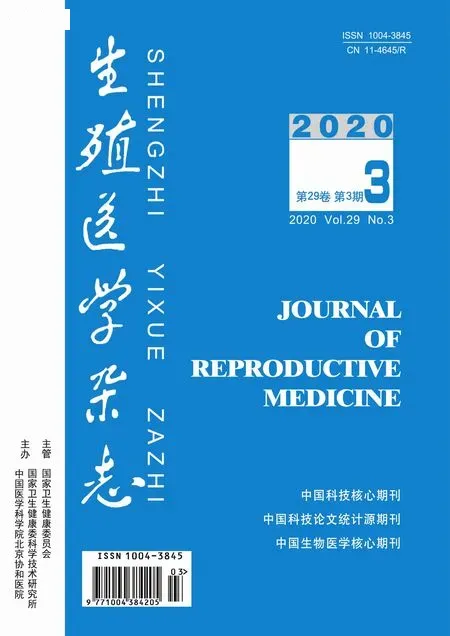卵巢睪丸性性發育異常中性腺優勢與內生殖器生育潛能
——22例病例報告及文獻復習
鄧姍,於利剛,孫愛軍,陳蓉,郁琦,田秦杰*
(1.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 北京協和醫院婦科內分泌與生殖中心,北京 100730;2.浙江蕭山醫院婦科,杭州 311200)
卵巢睪丸性性發育異常(Ovotesticular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OT-DSD)是指同一個體內存在卵巢(含卵泡)和睪丸(含有曲細精管)兩種性腺組織,而且兩種性腺均有功能,以往也稱為真兩性畸形[1],其發病率估計為1/10萬[2],約占所有DSD的3%~10%[3]。絕大多數患者在出生時即表現為外生殖器模糊,少數青春期后出現變化。“女孩”可有陰蒂長大似陰莖,而“男孩”可有“周期性尿血”。青春期后患者乳房通常會有發育,腹股溝包塊或“疝”亦不少見。內生殖器的特點和發育潛能是性別認定中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在OT-DSD的患者中,50%的患者按男性或女性撫養并不取決于染色體核型,而在成年后出現性別不安或要求改變最初性別的情況并不少見[4]。內生殖器的發育與性腺密切相關,睪丸一側因抗苗勒管激素(AMH)作用,不會有輸卵管和子宮發育,而卵巢側則必然出現單側苗勒管發育而來的輸卵管和單角子宮及陰道。
既然OT-DSD的患者能來月經(或周期性血尿),提示其可以有功能性子宮的發育,而子宮的發育有賴于AMH的缺失。單側性腺為睪丸則同側無子宮,而對側仍可以有子宮。根據經典文獻的資料,OT-DSD的性腺以卵睪最為常見,約半數的患者不具有單側純睪丸的性腺[5]。那么卵睪側的內生殖器發育是怎樣的特點?不同性腺組合情況下內生殖器的發育又有何特點?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對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收治的22例OT-DSD患者病例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并查閱中外文獻,對國內的相關個案報道和病例系列報道進行匯總數據分析,希望對性腺與內外生殖器表型的關聯有進一步理解,為日后的臨床實踐提供參考。
資料和方法
一、病例資料收集
收集1977年3月至2019年8月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收治的22例卵巢睪丸性DSD患者,對其臨床資料進行記錄和匯總。
二、文獻搜索
從中國知網(www.cnki.net)以“真兩性畸形”為主題詞,不限制年代進行檢索,共檢索到94篇相關病例報告或病例系列報告。篩除同一家單位的重復病例,或文章內容存在互相矛盾、不嚴謹現象,或從病例資料中無法確認有兩種性腺存在等文獻,共去除24篇文獻(含我院前期發表的14例)。最終納入70篇文獻(發表年代為1964~2017年)中的242例患者。
三、數據分析
對所有納入病例的臨床資料進行觀察性描述和分析。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變量多為分類變量,各組間的百分率(%)比較采用獨立樣本的卡方檢驗進行。
結 果
一、病例資料分析
北京協和醫院1977年3月至2019年8月共收治22例OT-DSD患者,具體臨床資料詳見表1。其中性腺組合的定義為:卵巢、睪丸各在一側稱為分側型;卵睪在一側、卵巢或睪丸在另一側的稱為單側型;雙側均是卵睪稱為雙側型。子宮大小評估中“無法評估”包括以下3例:(1)13歲無初潮,術中見幼稚子宮,但后期失訪;(2)8歲術中見“杏仁大小”子宮,同時予以切除;(3)3歲術中見“杏仁大小”子宮,后期失訪。月經情況中閉經病例(共14例)包括:幼年已切除子宮3例;繼發閉經2例;生殖道梗阻導致周期性腹痛并切除子宮6例;原發閉經3例:(1)20歲原發閉經,Gn升高診斷卵巢早衰(POF),術后人工周期1年子宮無明顯變化,最大徑仍為2 cm,亦無月經來潮;(2)17歲Gn正常,無初潮,術中見子宮2 cm×1 cm,拒絕人工周期治療;(3)30歲原發閉經,根據激素水平診斷POF,未行人工周期,術中見子宮如條索予以切除。
22例患者均有子宮,除睪丸側無子宮外,卵巢側均有子宮,卵睪側也均有子宮發育,其中2例分側型性腺患者的子宮異位至卵巢側腹股溝管,1例后期失訪,1例原發閉經,20歲診斷時子宮僅2 cm大小,經人工周期治療1年后無明顯變化,診斷為“始基子宮”。

表1 北京協和醫院22例OT-DSD患者的臨床特征一覽表 (n)
針對子宮功能狀態的評估和隨訪顯示,5例在幼年診斷術后失訪,除1例僅3歲無法評估外;其余4例患者的年齡為13~16歲,均無自然月經或周期性腹痛,其中3例為分側型性腺,子宮均位于盆腔一側,最大徑3~5 cm,且均有陰道,另1例性腺為卵巢-卵睪,子宮偏于卵巢側,6 cm×4 cm×2 cm,陰道下段狹小,可疑尿生殖竇。其余17例患者中,幼年時切除子宮的3例,其中2例有陰道(其一選擇男性生活,另一19歲子宮發育不良),1例“無陰道”,在25歲接受了人工陰道成形術。5例因周期性腹痛切除子宮,均合并無陰道,子宮發育不良2例,類似育齡期單角子宮3例,其中1例合并腺肌癥。1例患者有發育良好的單角子宮及陰道,但因多年按男性生活,且外陰已行男性化整形,要求切除子宮。3例原發閉經(性腺分別為分側型2例和雙側型1例),子宮均小,最大徑2 cm,其中2例分別于20歲和30歲時診斷POF,1例17歲雖性激素水平正常但拒絕人工周期治療,不能排除子宮發育不良導致的子宮性閉經情況。2例初潮后數年繼發閉經(性腺分別為卵睪-睪丸和卵巢-睪丸),1例查有陰道但未婚,1例曾有婚史,但因陰道外口狹小性交不成功而離異。1例患者(雙側型性腺)15歲初潮,隨診至今34歲,月經規律無腹痛,但嗓音低沉如男性,未婚。2例性腺為卵巢-卵睪的患者在切除卵睪側附件術后自然妊娠且足月,均以骨盆狹窄為指征行剖宮產術,后期1例再次妊娠行人工流產1次。
二、文獻資料分析
去除我院前期發表的資料后,對國內文獻報道的相關病例進行匯總分析。242例患者中,就診時社會性別為男性者128例,女性107例,未注明性別或因引產胎兒或新生兒性別不明者7例。年齡(14.1±8.4)歲(1~50歲)。
1.染色體類型:排除25例未提供染色體結果的患者,染色體類型的頻次排序依次為:46,XX 132例(60.8%),46,XY 40例(18.4%),46,XX/46,XY 30例(13.8%),其他不超過5例的少見核型包括:47,XXY,45,X0,45,X0/46,XY,46,XX/47,XXY,45,X0/46,XX,45,X0/46,XX/46,XY。
2.性腺類型:去除未提供性腺信息的患者。在不區分側別的情況下,除繼發腫瘤無法分辨原始性腺類型的1例外,其余包括單側型性腺的患者均納入統計,總計434側性腺,其中卵睪177例(40.8%),卵巢134例(30.9%),睪丸123例(28.3%)(表3);就側別而言,卵巢位于盆腔左側居多,睪丸位于右側居多(表2)。

表2 單側性腺的類別及側別分布[N=434,n(%)]
注:*原文獻中僅表述為“一側/另一側”,無法區分左右側別
國內文獻資料中,就雙側性腺的組合情況而言,分側型(即卵巢+睪丸)為83例(45.1%);雙側型(即卵睪+卵睪)45例(24.5%);單側型中卵巢+卵睪為32例(17.4%),睪丸+卵睪為24例(13.0%)。國內文獻資料及我院患者中各組合類型及比例情況詳見表3。

表3 OT-DSD的性腺組合類型及比例[n(%)]
3.性腺位置:文獻中有115例患者資料提供了性腺側別、類別和位置等完善信息,其中5例為單側性腺。匯總卵巢、睪丸和卵睪的位置分布見表4。74.6%(50/67)的卵巢位于盆腔左側,69.5%(41/59)的睪丸位于盆腔右側,此側別優勢經卡方檢驗證實具有統計學差異(P<0.001)。卵睪位于盆腔、腹股溝或陰囊(唇)的比例分別為59.6%、28.3%和12.1%。8例(11.9%,8/67)患者的卵巢不在盆腔內,而且其中6例合并子宮異位于腹股溝或陰囊內。我院22例患者中亦有2例卵巢和子宮一起異位于腹股溝管內。

表4 不同性腺的解剖位置分布(n)
4.子宮情況:118例病例報告中對子宮有所描述,但僅限于“有”或“無”的表述,其中11例“無子宮”,6例可疑,其余101例(85.6%,101/118)均有子宮,但缺乏針對側別、大小和功能性的區分。
討 論
根據此次對本院22例病例的回顧性分析以及國內文獻中242例相關病例的匯總分析,OT-DSD最常見的染色體核型是46,XX,性腺多少的占比排序為:卵睪>卵巢>睪丸(約4:3:3);性腺組合按多少排序為:分側型(卵巢-睪丸)、單側型(卵睪-卵巢和卵睪-睪丸)、雙側型(卵睪-卵睪)。本院的全部病例均有子宮,國內文獻中的絕大多數病例也有子宮,少數“沒有子宮”可能與年齡過小、子宮尚未發育有關。睪丸側無子宮發育,卵巢和卵睪側均有子宮發育,但常伴發育不良,且約半數(11/22例)合并無陰道或尿生殖竇異常。在社會性別女性的19例患者中,5例因生殖道梗阻行子宮切除,9例陰道發育不良,3例發生POF,雖有妊娠分娩的病例,但總體生殖預后并不樂觀。因我單位為婦科內分泌專科,故所涉及病例是截至目前國內針對成年女性OT-DSD患者的最大宗報道,除失訪的5例患者外,其他患者均已成年,關于生殖潛能的隨診信息均比較完整,結論新穎,臨床意義較大。
有關OT-DSD患者染色體核型以及性腺類型,本研究的結論與1981年van Niekerk等[5]發表的409例真兩性畸形的經典文獻相符。不管在亞洲還是南非種族的患者中,46,XX都是最常見的核型,我國和日本患者中的占比分別為60.8%和61.6%[6],而南非的患者中該核型占比更高,達89.1%[7]。就性腺性質而言,大宗病例匯總分析均顯示卵睪是最常見的性腺,占比40.8%~56.0%[5-7],我院的22例患者中,卵巢、睪丸和卵睪分別是18(40.9%)、14(31.8%)、12(27.3%)(側)例,卵睪并非最多見的性腺類型,可能跟本組病例數較少有關。而在性腺組合上,前述van Niekerk等[5]的經典文獻中,單側型(40.1%)>分側型(29.6%)>雙側型(20.8%);日本的165例病例回顧中單側型(50.3%)>分側型(24.2%)>雙側型(20.6%)[6];而我國病例的此次回顧顯示分側型最常見(45.1%),其次為單側性(30.4%)和雙側型(24.5%)。針對性腺類型的差異,不能除外國內病例病理診斷的準確性偏差。應強調病理診斷的嚴格標準,尤其是卵巢組織,必須以鏡下可見始基卵泡為診斷標準,不能僅以卵巢樣組織(卵巢樣間質)就診斷卵巢。我院22例患者的性腺組合中也是以分側型最多(54.5%,12/22),單側型次之(36.4%,8/22),可能也跟病例數有限有關。但無論性腺組合的具體類型如何,最終其功能都將體現在內外生殖器的分化和發育上。
我院2013年曾回顧性分析14例OT-DSD病例,其中對于子宮的描述未具體涉及其盆腔的位置(即中線區域或側盆腔),也沒有將性腺情況與子宮的發育對應描述[8]。即使國內242例病例報告的匯總分析中,針對子宮發育的信息也非常有限,在118例對子宮有描述的原始文獻中,17例(14.4%)描述“無子宮”或“可疑子宮”的后續情況無法考證。所報道患者的年齡也差別很大,幼童占較大比例,因此有限的匯總信息僅能對“OT-DSD患者絕大多數都有子宮”提供粗略的支持,但關于子宮的功能狀態和生育潛能都無從借鑒。本文復習前期病例加上新收治的總計22例OT-DSD患者的臨床資料,著重對其性腺及內生殖器的發育進行比較,證實OT-DSD是體現性腺決定內生殖器單側發育的典型模型,睪丸側一致性無輸卵管和子宮發育,而卵巢側有苗勒管發育,卵睪側也都有輸卵管和子宮發育。分側型性腺的子宮均位于盆腔偏側(卵巢側),大多位于側盆壁,而雙側型性腺以及單側型中的卵睪-卵巢型的子宮可位于盆腔中線,部分幼年時手術中顯示“未見”或“杏仁大小的”子宮,成年后也可有月經來潮。提示在青春期前不宜輕易切除未發育患者的子宮。至于卵巢和卵睪側的子宮發育是否有差異,限于本研究的病例數有限,且部分病例失訪,似乎看不到明顯差異,如:兩例完成生育的患者均為卵巢-卵睪型,卵巢側的子宮符合育齡期外觀的和發育不良的例數大致相當,雙側卵睪型患者也可持續月經正常。
由OT-DSD中不同性腺占比、性腺組合的比例特點,以及子宮的存在比例來看,女性特征的內生殖器占優。更重要的是,van Niekerk等[5]關于OT-DSD性腺的組織學研究表明,77%的卵巢是正常的,23%表現為始基卵泡減少,50%顯示有排卵。我院病理科曾經對9例OT-DSD患者進行性腺病理分析的結果也類似,卵巢與卵睪體的卵巢組織均可見各級卵泡,2例可見黃體,而睪丸與卵睪體的睪丸組織則有不同程度的發育不良[9]。這些組織病理學證據也支持性腺功能中卵巢占優的推論。我院曾報道的2例完成生育的卵巢-卵睪型性腺的成年女性患者,睪丸組織的功能僅體現在外陰輕微男性化和血睪酮升高上,術前即月經正常[10]。另據文獻報道,雙側為卵睪的個體也可以有生育潛能,盡管技術上可能很困難,但應該爭取盡早予以手術分離[11]。盡管如此,我院19例社會性別為女性的患者隨診結果顯示,合并生殖道梗阻而無法正常性生活或切除子宮的患者并不少見,而因POF喪失生育潛能者也不止1例,提示此類患者的生殖預后并不樂觀。
鑒于OT-DSD中大多數睪丸的組織學檢查是異常的,僅2/24的患者有接近正常的組織學特點[5],對選擇性別有很重要的提示意義。根據此次我院22例病例的回顧性分析,睪丸功能的影響似乎更多體現在外陰模糊不清或陰蒂增大上。本院22例病例中,外陰的Prader分級由Ⅰ~Ⅳ級不等,陰莖最長者可達5 cm,但關鍵點在于其尿道開口都是在陰莖下方的會陰區(即會陰型尿道下裂),而非陰莖頭部或陰莖沿線旁側,這一特征將嚴重影響選擇男性生活的患者的遠期生活質量。針對外生殖器模糊不清的DSD病例而言,尿道開口的定位對于性別認定至關重要[4,12]。如我院1例成年男性患者,6歲時接受“尿道下裂”矯形術,但青春期后出現乳房發育和周期性血尿,我院手術證實患者單角子宮和同側卵巢均發育良好,陰道遮蔽于陰囊后,尿道開口也位于會陰區,而對側睪丸明顯萎小。但因該患者已23歲,要求繼續按男性生活,于是行卵巢、子宮切除術和乳房切除術。該例患者的代表性在于性別認定錯誤的結局,切除優勢的性腺和生殖器官,而保留殘缺的性腺和生殖器官是非常遺憾的。根據國際共識的相關意見,OT-DSD的性別選擇應結合性腺分化和外生殖器發育的具體情況,考慮生育潛能,以及外生殖器整形后與所選性別能否一致的可行性[1-2,4,13-15],這是一個復雜、審慎,需要多學科專家參與的重要決策過程。早期診斷固然更理想,但性腺和生殖器的功能通常要到青春期后才能充分評估,所以本領域內對手術時機的選擇存在爭議[12],一方面主張延遲認定和手術,有利于患者有能力自主參與到“性別選擇”的決策中,而日本等國家的專家認為患兒的父母很難接受孩子“性別不確定”的狀態長時間存在,應對患兒心理反應的難度也很高,所以主張早期診斷和治療[6]。針對嬰幼兒性腺功能的評估可以通過檢測AMH和或HCG刺激試驗輔助判斷,但內生殖器如子宮的潛能恐怕只能等到青春期后才能充分評估[4]。
總之,OT-DSD是一種罕見且復雜的性分化異常疾病,從性腺類型到內外生殖器的表型均有多種可能性,如何及早診斷,在合適的年齡指導患者及其家庭選擇合理的社會性別,并進行恰當的矯治性手術涉及多學科的理論和技術,強烈建議轉診至該領域內有經驗的機構進行診治。另一方面,性腺與內外生殖器的發育在胚胎發育和臨床解剖學的理論基礎上也是有規律可循的,OT-DSD的性腺功能中,卵巢通常占有優勢,進而保留女性生育潛能是可行的,了解這一規律對于性別認定等重大臨床決策會有很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