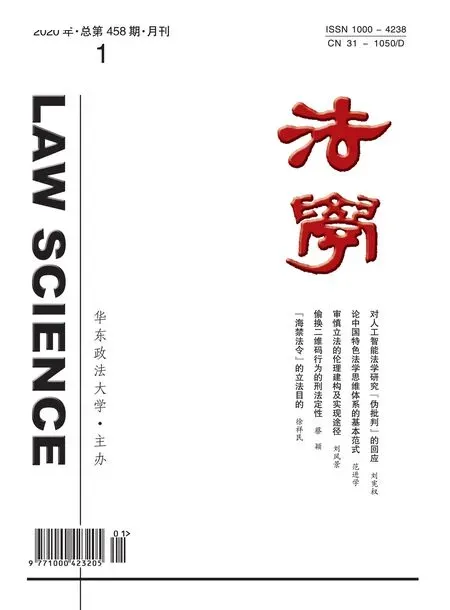算法共謀的反壟斷法規制
●周 圍
一、算法共謀的競爭隱憂
經濟學家熊彼特曾預言:“新商品、新技術、新供應源以及新型組織的競爭將比完全競爭更為重要,它沖擊的不是現有企業的利潤額,而是他們的根基、他們的生命。”〔1〕[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48-149頁。數字經濟的繁榮印證了熊彼特的預言,它不僅顛覆了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且還創造出無數新的交易機會,極大地激發了全球經濟增長的活力。為了維護數字經濟的有效運行,經營者們開始利用以現代計算機為載體的算法來實現交易機會的快速搜索和有效匹配,〔2〕See Joseph Kennedy, Why Internet Platforms Don’t Need Special Regulation, http://www2.itif.org/2015-internet-platforms.pdf.以及建立廣泛的信任機制。〔3〕See FTC, The Sharing Economy: Issues Facing Platforms, Participants & Regulator,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reports/sharing-economy-issues-facing-platforms-participants-regulators-federal-trade-commission-staff/p151200_ftc_staff_report_on_the_sharing_economy.pdf.算法是一種機械、精準、系統地應用于特定標記(tokens)或對象(objects)的操作流程。隨著算力的大幅提升和運算數據的海量供給,經營者一方面可以利用算法分析歷史數據,以便對產品需求、價格變化、客戶行為和偏好、市場風險和可能影響市場環境的內外因素迅速快捷地做出反應,另一方面還可以優化業務流程,通過降低經營者的生產和交易成本,設置有效響應市場環境的最優價格來獲得競爭優勢。根據歐盟委員會2017年針對電子商務行業的調查報告,58%的受訪經營者表示會跟蹤競爭對手的在線價格,其中約三分之二已開始使用自行創建的算法程序或借助第三方提供的算法軟件來搜索、跟蹤、抓取競爭對手的產品價格或其他商業信息。〔4〕See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 Brussel, 10.5.2017, SWD (2017)154 final, para.149,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sector_inquiry_swd_en.pdf.在亞馬遜公司的電商平臺上,已有超過85%的供應商使用Buy Box算法來自動定價。〔5〕See Le Chen et 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lgorithmic Pricing on Amazon Marketplac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s Steering Committee, 2016, p.1339-1340.
經營者使用計算機算法雖可改進定價模型、定制特色服務和預測市場趨勢,進而提高競爭效率,但算法的廣泛使用也可能產生反競爭效應。因為使用算法讓經營者更容易在無任何正式協議或人際互動的情況下實現或維持共謀。早在2015年就有學者撰文指出:“無論是明示或默示的共謀,通過對收集的海量數據進行算法處理的自動定價可能會導致價格高于競爭水平。”〔6〕Salil K. Mehra, Antitrust and the Robo-Seller: Competition in the Time of Algorithms, 100 Minnesota Law Review, 2016, p.1350.隨后,在2017年經合組織(OECD)的“算法與共謀”圓桌會議上,美國、歐盟、英國、意大利、俄羅斯、新加坡等反壟斷執法機關也開始對算法可能引發的共謀問題表示出擔憂。〔7〕See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 Summaries of Contributions, https://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 df/?cote=DAF/COMP/WD(2017)2&docLanguage=En.由是可見,算法與大數據以及機器學習等先進技術工具的結合正在日益改變數字市場的競爭格局,算法的使用不再只是經營者的個體行為,其對經濟活動的深度介入還可能產生廣泛的公共性問題。
首先,算法提升了供給側的市場透明度。〔8〕市場透明程度是指在市場競爭中,經營者完整、全面、真實和可靠地獲取經營信息通常需要基于對商品供求、交易價格、市場監管以及財政、經濟和金融等各項指標和信息的獲取程度。理論上,市場透明度越低,具有信息優勢的經營者達成共謀的可能性就越高,處于信息劣勢的經營者將為此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導致市場的運行效率降低;反之,市場透明度較高,經營者雖能充分收集競爭對手及市場信息,但具有強大數據挖掘能力的復雜算法可更好地區分有意圖的共謀偏差,從而更容易實現共謀者對彼此履行壟斷協議情況的監控和懲罰。實踐中,算法能夠有效收集可自動分析并轉化為行動的詳細實時數據,從而使經營者從強大的預測能力和高效的算法決策規則中受益。故此,只要部分市場參與者從算法競爭優勢中受益,行業的其他公司就會有強烈的參與動機,以避免被趕出市場。如此的結果便是所有市場參與者不斷地收集和實時觀察競爭對手的行為、消費者的選擇和市場環境的變化,從而創造出一個容易產生共謀的行業。歐盟委員會就認為,通過價格監測軟件提高價格透明度可通過更容易和更直接地檢測與共謀協議的偏差來促進或加強零售商之間的勾結。反之,這可以通過限制這種偏離的預期收益來減少零售商偏離共謀價格的動機。〔9〕Supra note 〔6〕, para.608.
其次,算法顯著提升了經營者之間交互的頻次(Frequency of Interaction)。在傳統的市場環境中,經營者調整價格的成本高且耗時,極易引起反壟斷執法機關的關注。例如,占據德國年度汽油零售額64.6%的埃克森美孚、殼牌等5家公司為了監控競爭對手的定價,會安排人手多次駛過指定競爭對手的加油站并記下價格,并將監測到的價格輸入到相應的石油公司電子系統。通常情況下,一個經營者提高汽油價格時,其競爭對手需要在3-6個小時后才能做出回應。〔10〕See Fuel Sector Inquiry Final Report,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Sector%20Inquiries/Fuel%20Sector%20Inquiry%20-%20Final%20Report.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14.但引入算法后,經營者們即可便捷地監控競爭對手的價格,而無需冗長的價格公示來觀察并形成競爭反應,僅需通過自動化決策即可及時更新自身的價格水平。在澳大利亞珀斯市的汽油零售市場盡管也存在類似的價格監控,但零售商們普遍采用算法來監控每個加油站的實時定價,從而避免每天多次開車經過鄰近的加油站。信息的互聯使得經營者在獲取即時價格后不必再向總部報告定價信息后再做出反應,也不必持續觀察其他經營者的價格變動,通過將價格信息饋入算法即可迅速產生實時的價格反應。〔11〕同前注〔6〕,Salil K. Mehra文,第 1338頁。鑒于定價算法的反應速度,其他零售商不太可能再臨時提供折扣以吸引其客戶。鑒于此,這種高頻次的交互不僅可顯著降低經營者之間的溝通成本,減少價格信號暴露的風險,而且能有效避免給予消費者充足的時間對價格變化做出反應,防止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因價格變動而造成客戶流失。
最后,算法有效地拓展了經營者達成共謀的市場范圍。一方面,算法降低了達成共謀所需的市場條件,從而使得經營者在集中度較低的市場中也可以有效實施價格的搜索、匹配、監督和報復,從而間接地拓展了共謀的發生場域。在傳統市場中,若競爭對手數量有限,則共謀更易實現。申言之,若市場內存在大量的經營者,則經營者難以尋找共謀者以及協同目標,即使僥幸締結了壟斷協議,每個參與共謀的經營者也只能獲得較低的壟斷利潤,這會抑制市場經營者實施共謀的動機。而快速精準完成搜尋與匹配的計算機算法可以實現在不太集中的市場中進行協調、監督和懲罰,可從理論上弱化競爭對手數量與達成共謀之間的相關性。〔12〕傳統反壟斷法理論在分析共謀時最常采用古諾的雙寡頭模型,而實踐中因受制于市場性質、信息傳遞的便利性以及市場監管的強度,共謀通常產生于產品同質化程度高、市場結構相對集中的市場。See A. Ezrachi and M. E. Stucke, Algorithmic Collusion: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 Note, Roundtable on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2017, p.21-23.另一方面,算法不存在人類經營者的心理變化和偏見,不受執法機關和社會輿論的影響,而且還能增強對共謀者價格維持狀況的監督,防止偏離共謀的背叛行為,有效地提升共謀的穩定性。法國和德國競爭管理機構在一份聯合報告中也指出:“通過處理所有可用信息,從而監控和分析或預測其競爭對手對當前和未來價格的反應,競爭者可以更容易地實現持續性的超競爭價格均衡。”〔13〕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and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DE/Berichte/Big%20Data%20Papier.pdf.
可見,盡管算法本身并不會產生法律意義上的價值判斷,但這并不表明引入算法對競爭的影響始終是中性的。與算法對整個數字市場的公共性影響不同,其競爭屬性還應取決于經營者在競爭中如何使用。一旦算法被用于達成、實施共謀,就可能破壞市場競爭秩序,從而受到反壟斷法的規制。在2016年歐盟“Eturas案”中,經營者提供的折扣算法為下游經銷商之間達成“有意識的平行行為”提供了幫助,被法院認定構成共謀。〔14〕See Eturas, C-74/14, ECLI:EU:C:2016:42.在實踐中,反壟斷執法機關對于是否應規制算法共謀都持有十分明確的意見,“任何人都不應該想象他們可以通過允許軟件為他們達成協議而逃脫價格壟斷”,〔15〕Vestager, M.,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The Remarks at the Bundeskartellamt 18th Conference on Competition, Berlin, 16 March 2017.“如果行為之前就是非法的,使用算法來實施這種行為并不會神奇地將其轉化為合法行為。同樣,以不違反傳統反壟斷規范的方式使用算法不太可能產生新的責任場景。”〔16〕Maureen K. Ohlhausen, Should We Fear the Things That Go Beep in the Night? Some Initial Thought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nd Algorithmic Pricing: The Speech at the Concurrences Antitrust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Conference, New York, 23 May 2017.作為全球重要的數字市場,中國同樣面臨因算法普遍適用而產生的系統性監管風險。面對違法行為隱蔽且多樣的算法共謀,如何理解其形成機理,解析其違法性,進而對規制算法共謀的分析框架作出更為明確的指引,目前尚未形成共識,還需進一步著力探討。
二、算法輔助共謀的反壟斷法規制實踐
在實踐中,算法作為促進共謀最為直接的作用是為了確保共謀協議的實施而監督競爭對手的行為。價格等市場數據雖可公開獲得,但也并不必然意味市場就是透明的。經營者參與共謀通常需要通過一種定期更新且易于使用的方式從特定競爭對手那里收集數據,而算法則可用于收集競爭對手商業決策的信息、觀察篩選潛在的共謀參與者和協商壟斷價格。同時,參與共謀的經營者還可通過復雜的算法來提升它們監督相互行為的能力。通過自動收集方法收集到的數據可以被監督,并可以與對背離行為進行自動報復的定價算法相配合。例如,經營者可能設計定價算法有效實施的觸發策略(trigger strategies),通過該策略設置一個協議價格以便所有競爭對手都能適用該價格,但只要任何經營者背離則立刻啟動價格懲罰機制。由于算法發現與懲罰背離行為的速度快,所以經營者通常缺乏足夠的動機實施背離行為。
算法作為一項輔助經營者監督競爭信息的工具,早在1994年“美國聯邦政府訴ATP案”中就引起了反壟斷執法部門的關注。〔17〕See United States v. ATP., 58 Fed. Reg. 3971 (1993).在該案中,美國多家航空公司共同出資成立了一家公司,旨在收集各航空公司每日的航班價格信息并通過電腦預訂系統(CRS)發送給航空公司和旅行社,航空公司可使用此系統快速觀察和響應競爭對手的票價。囿于高昂的協調成本,航空公司通常難以同時參與數十個或數百個航線市場的具體談判,而基于算法的交流監督平臺則能克服航空公司之間的數據交流壁壘和談判能力缺陷,有效協調各條航線上的價格策略,使機票價格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從而提高聯合利潤,這比任何一家公司只用自己的規則或算法獲取的利潤更高。因任何顯著的價格變動都可以被競爭對手快速匹配,故航空公司背叛共謀價格所獲得的潛在收益遠小于保持高售價的收益,從而進一步增強了共謀的穩定性。〔18〕See William Gillespie, Cheap Talk, Price Announcement, and Collusive Coordination, EAG 95-3, Discussion Paper, Economic Analysis Group,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9/25/95).在此情形下,反競爭協議仍是由航空公司的經營者們協商、達成和實施的,算法只是促成和實施協議的一種監督機制。
對于這類輔助共謀的算法,其違法行為的認定與傳統共謀案件并無明顯差異,但在算法的輔助之下,一方面大幅降低了經營者達成和實施共謀的難度,另一方面則進一步提升了執法機關發現共謀的難度。例如,在高度動態化的市場中,供給與需求的持續變化要求參與共謀的經營者頻繁調整價格、產出及其他交易條件,經營者必須通過會議、電話、郵件或通過第三方進行頻繁協商,以實現非競爭均衡(non-competitive equilibrium),這些溝通行為都存在被反壟斷執法機關發現的風險。引入算法后,協商行為被自動化決策所替代,使得價格等市場信息可自動反饋市場變化而無需進一步溝通,甚至價格可自動反饋市場條件的任何變化,從而達成“有意識的平行行為”(conscious parallelism)。〔19〕See OECD,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 2017, p.27-29.例如,某行業中大部分經營者利用算法實時跟隨某個市場領導者的價格,即實施“針鋒相對策略”(tit-for-tat strategy),若領導者負責設置將價格固定在競爭水平之上的動態定價算法,那么其他經營者就會即時跟進并且達成共謀。
在前述“Eturas案”中,立陶宛的一家名為Eturas的公司使用折扣算法為下游旅行社之間達成“有意識的平行行為”提供了幫助。〔20〕同前注〔14〕。E-TURAS軟件是Eturas公司研發的一個在線旅程預訂系統,通過與Eturas公司訂立許可合同,下游旅行社則可通過該系統向顧客提供旅行預訂折扣。2010年間,立陶宛競爭委員會根據使用E-TURAS系統的其中一個旅行社所提供的信息展開了調查,根據這些信息,使用該系統的旅行社似乎通過該系統在所給出的旅行預訂折扣上相互協調。調查顯示,2009年8月25日,Eturas公司的經理向數個旅行社發送了一封標題為“投票”的電子郵件,以詢問收件人是否愿意調整網站上的折扣,將原為4%的折扣下調為1%-3%的差幅折扣。2009年8月27日,8家旅行社的網站陸續對3%的旅程折扣作了廣告宣傳。在旅程預訂過程中,網站會彈出一個窗口以告知預訂人其選中的行程將享受3%的折扣。競爭委員會在2012年6月7日的裁決中認為,2009年8月27日至2010年3月間,Eturas及30家旅行社通過E-TURAS軟件給出預訂折扣的行為是一種反競爭行為。而所有在涉案期間使用該預訂系統而未提出異議的旅行社均違反了競爭條款,因為他們理應聯想到該系統的其他使用者可能也將他們的折扣率控制在3%以內。據此,競爭委員會推斷這些旅行社之間已相互告知其在未來將實施的折扣率,并通過暗示或默認的方式間接表達了在相關市場上對其行為的共同意志。故此,競爭委員會認為,上述旅行社在相關市場上的行為應被解讀為達成一項協同行為。盡管Eturas并未參與相關市場的競爭,但該公司及其E-TURAS算法為這一行為提供了便利。最終競爭委員會宣布Eturas及所涉旅行社違反了《歐盟運行條約》第101條第1款之規定。
為了避免明示性溝通,經營者會通過披露共謀的意圖、特定的信號或單邊價格宣傳行為來實施更為復雜的共謀策略。在傳統的市場競爭環境中,發布共謀信號可能給經營者帶來極高的成本,若大部分競爭對手并不接受該信號或故意不予回應,發出共謀信號的經營者便因率先提高價格而面臨消費者的流失和利潤的減損。〔21〕參見韓偉:《算法合謀反壟斷初探——OECD 〈算法與合謀〉報告介評(上)》,載《競爭政策研究》2017年第5期。這一潛在的風險抑制了經營者主動發出共謀信號的動力,使其只能被動等待少數經營者的冒險嘗試,從而導致共謀的遲延甚至失敗。與之相較,算法能讓經營者自動設置執法機關和消費者無法發覺但參與共謀經營者的算法可以察覺的快速議價行為,從而降低甚至完全消除信號成本。例如,在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訴托普金斯案”〔22〕See Plea Agreement, United States v. Topkins, No. 15-201 (N.D. Cal. Apr. 30, 2015) [ECF No. 7].中,被告就利用了算法頻繁地釋放價格信號和調整價格,達成并實施了共謀。該案被告托普金斯與其他亞馬遜網站賣家協商一致,對同類海報設定同樣的價格,該共謀行為利用特定的定價算法來實現,此種定價軟件通過收集亞馬遜網站上各商家關于特定商品的價格信息,為商家提供定價規則。托普金斯及其共謀者同意使用特定算法為特定海報產品進行定價,促使共謀者的商品價格及其變動能夠保持一致,從而實現固定和提升商品價格之目的。此種共謀行為使得托普金斯和共謀者在一個共謀的、沒有價格競爭的亞馬遜市場銷售、傳播和交易商品。本案中算法對該共謀行為的影響表現在:若無定價算法,托普金斯及其他參與共謀的經營者則需通過一系列協商以及后續溝通調整,才能保持價格的一致,但在引入算法后,算法可按事先設定的定價規則進行定價,并根據市場變化進行統一的價格調整,從而徹底隱藏了經營者的明示共謀行為。
共謀是競爭對手之間實施的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共同利潤最大化策略行為,算法的引入則進一步放大了共謀的產生場域和社會危害。現有涉及共謀的算法在案件中主要是作為輔助經營者達成和實施共謀的一種工具,在其輔助下,經營者間的協商、交流和實施更加難以被察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執法機關發現線索、搜集證據和確認違法行為的難度。值得注意的是,此類案件無論是在以經營者的目的和行為作為判定其違法性的標準,抑或是以行為的反競爭效果作為其承擔法律責任的裁量依據上,均未突破反壟斷法“人類中心主義”的規制框架,其核心始終聚焦于經營者的壟斷行為。也就是說,雖然使用算法進行共謀串通的經營者能夠通過該系統隱匿地接收和確認參與共謀的意圖和方式,但是共謀之達成和實施仍依賴于經營者有意識的客觀行為。不可否認,算法對共謀行為的影響遠非止于此,技術的引入還可能產生更具挑戰性的共謀場景。
三、自主學習算法共謀的特殊性及應對
除了作為輔助共謀的工具,算法還能夠與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技術相結合,在無需經營者人為干預算法運算過程的情況下就自主實現共謀之結果。換言之,這種算法通過持續學習以及與市場主體行為的反復協調,在無需人類干涉的情況下便可能形成共謀。這種算法被稱為自主學習算法(Selflearning algorithms),〔23〕同前注〔19〕,OECD文,第 31- 32頁。相較于輔助共謀算法,其更容易確定共謀者之間的共同利潤最大化價格,從而最大程度地損害消費者利益。更令人憂慮的是,與人工智能技術相結合的算法所形成的共謀結果只能通過競爭效果去觀察,無法通過形式去認定和判斷,故而執法機關很難察覺自主學習算法是否已在數字市場中形成了“虛擬共謀”(virtual collusion)或產生了相應的共謀結果。而且,人工智能算法的具體工作過程是個“黑箱”,其處理原始數據的方式復雜、快速及精準,目前執法機關尚無從知曉算法決策背后的相關細節。如果經營者通過人工智能算法自動設置價格及其他商業決策,那么共謀的結果將更難通過傳統的反壟斷工具予以阻止。
(一)自主學習算法共謀的特殊性
與算法輔助型共謀相比,自主學習算法形成的共謀具有如下特征。
1.由算法主導形成。多年來,定價算法已經在諸多行業中得到應用,人工智能領域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一旦定價和協調決策完全委托給具有自主學習能力的算法則可能引發對算法共謀的系統性監管風險。〔24〕同前注〔6〕,Salil K. Mehra文,第 1335頁。目前雖尚未出現由自主學習算法主導實現共謀的案例,但已有學者通過構建利潤最大化函數模型,成功模擬了兩個利用算法設定價格的經營者實施共謀的情形。〔25〕See Bruno Salcedo, Pricing Algorithms and Tacit Collusion, Manuscrip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15).在該模型中,假設這兩個寡頭壟斷經營者在局部時間點上均能夠快速、及時地“解碼”對方的算法及價格,并相應地調整自己的價格,經營者α采用一種對競爭對手的任何提價均進行匹配的定價算法,在此情況下,經營者β的最佳反應就是將其視為某種“提議”,同時并行地提升價格。只要經營者α不能迅速修改其價格,經營者β就會將其視為提高價格的堅定承諾,從而擺脫競爭均衡價格。該模型中的算法人為地抑制了價格調整的及時性,導致算法之間的共謀“不可避免”,這也同時證實了在寡頭市場中當具有可信承諾時算法達成共謀的可能性。這種能夠自主觀察、接收、饋入市場信號,并據預設邏輯得出反饋結果的算法與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相結合,通過使用不同的編程原理來設計智能體(agent)處理復雜的市場競爭問題,完全規避了經營者在市場競爭過程中的主導作用。
2.共謀實現的方式更為隱蔽。算法改變了數字市場的特征,一則提升了市場透明度,二則提高了經營者快速回應對手行為的能力。在這種環境下,算法可讓企業無需明確溝通或互動的前提下相互依賴,提升了產生默示共謀的風險。在這種高度集中、穩定與透明的市場環境中,經營者行為對其競爭對手有著更為顯著的影響。因此,通過反復協調和觀察,經營者所使用的算法慢慢可以覺察到他們各自的策略選擇是相互依賴的,通過配合各自的行為,他們可以將價格的設置高于競爭水平,而無需實際的溝通。換言之,通過相互依賴以及相互的自我意識,算法可協調將價格推向壟斷水平,這與經典的“寡占問題”(oligopoly problem)頗為相似。〔26〕See R. Posner, Oligopoly and the Antitrust Laws: A Suggested Approach, Stanford Law Review, (21), 1968 , p. 1562-1606.而且,自主學習算法還使得默示共謀在更多樣化的環境下變得可持續,從而在非寡占市場結構中拓寬了寡占問題的適用范圍。學界普遍認為,傳統的默示共謀只能在相對集中的市場中持續存在,當經營者反復且無限次地溝通時,默示共謀在某些限制條件下是能夠實現均衡的。〔27〕See S. Feuerstein, Collusion in Industr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3), 2005, p.163-198.但是,算法的出現和廣泛應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算法共謀形成所依賴的市場結構。如有學者所言:“行業向定價算法的轉變可以將超級雙方的默契勾結拓展到擁有五六家大公司的市場。”〔28〕數字市場的性質、數據的可用性、類似算法的發展以及它們所促進的穩定性和透明度很可能將一些原本處于暗中勾結之外的市場推向相互依存。See A. Ezrachi and M.E. Stucke, Algorithmic Collus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 Note, Roundtable on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2017, p. 21- 23.有學者同樣認為:“通過對收集的海量數據進行算法處理的自動定價可能會導致價格高于競爭水平,無論是通過默示共謀還是更強大的卡特爾形成。”〔29〕同前注〔6〕,Salil K. Mehra文,第 1363頁。OECD也指出:“算法可能會影響數字市場的某些特征,以至于默示共謀可能在更廣泛的情況下變得可持續,可能將寡頭壟斷問題擴大到非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30〕同前注〔19〕,OECD文,第 21-23頁。
3.自主學習算法對反壟斷“人類中心主義”規制框架的潛在突破。作為一種工具,算法消除了競爭對手之間的明確溝通或交流的需要,可以便利非競爭均衡的達成。實際上,算法可以發揮經營者之間媒介的功能,通過收集與處理市場數據,快速應對競爭對手的行為。算法在控制共謀的結構方面可能比人類做得更好,因為它們在發現價格變化方面更為精確,消除了人類偏見等非理性因素,降低了共謀策略被錯誤行為所削弱的可能性。〔31〕同前注〔6〕,Salil K. Mehra文,第 1346頁。傳統反壟斷法對壟斷協議的規制是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首先,在禁止經營者實施反壟斷法所規定的壟斷協議時,反壟斷執法機關經常會利用競爭對手相互之間的不信任,放大涉案經營者對執法行為的恐懼,以實現案件的突破。其次,在判定經營者是否違反反壟斷法實施共謀時,通常需要衡量壟斷經營者或企圖壟斷經營者的行為意圖以及判斷經營者之間是否存在“一致性意見”(meeting of the minds)或“合意”(mutual assent)。〔32〕See Alon Y. Kapen, Duty to Cooperate Under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Aspen Skiing’s Slippery Slope, 72 Cornell Law Review, 1987, p.1047.行為的意圖、一致性意見或對違法的恐懼都是針對假定的人類心理狀態,但在自主學習算法主導共謀時通常很難奏效。算法的設計和運行雖在一定程度上模擬著人類的思維方式,但很難模擬人類的潛在情感和心理狀態,而這些在執法機關查處壟斷協議案件時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雖然自主學習算法共謀的上述特點給反壟斷法規制帶來了諸多困難,但仍應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對自主學習算法實現共謀的原理進行剖析,以求找尋可能的應對策略。
(二)自主學習算法實現共謀的現實障礙
在算法博弈論和人工智能經濟學領域,學者們不斷探索算法在實現自主共謀上的可能性。例如,有學者使用基于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技術的Q-learning算法根據零和博弈(Zero-Sum Games)、一般和隨機博弈(General-Sum Games)等策略嘗試模擬默示共謀。〔33〕See A. Ittoo, N. Petit, Algorithmic Pricing Agents and Tacit Collusion: 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https://ssrn.com/abstract=3046405.還有學者發現基于強化學習算法的智能體在古諾雙寡頭壟斷中可實現默示共謀。〔34〕See Waltman et al., Q-learning Agents in a Cournot Oligopoly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32.10, 2008,p.3275-3293.我國學者也從雙寡頭競爭模型中成功建構了一種線性勒索算法(Linear Extortion to Collusion Algorithm),并成功模擬了與人類實現共謀的情形,〔35〕See Nan Zhou et al., Algorithmic Collusion in Cournot Duopoly Market: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18.根據該研究,在共謀的動態演化過程中,無謂損失不斷增加而社會福利則持續下降,而且在勒索算法—人類共謀中,隨著共謀程度的不斷上升,勒索算法的利潤比人類經營者更多,這充分說明算法共謀產生的威脅是真實的、可預期的。當然,目前自主學習算法多智能體之間的共謀面對成本、價格或其他參數的微小擾動時并不穩定,〔36〕See Segismundo S. Izquierdo and Luis R. Izquierdo, The Win-Continue, Lose-Reverse Rule in Cournot Oligopolies: Robustness of Collusive Outcomes, Advances in Artificial Economics, (18), 2015, p. 33-44.因此,在真實的市場環境下,要實現依賴復雜的自主學習算法共謀仍存在諸多難題。〔37〕假設市場中存在n個智能體,而每個智能體又分別存在A個可能的策略和反應以及m個狀態的環境變量,那么需要計算的可能性就是nmAn,其計算的復雜性是難以估量的。See L. Bus?oniu, R. Babuska, and B. De Schutter,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Part C: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2), 2008,p.156-172.
首先,算法函數的偏好存在差異。在多個自主學習算法試圖進行共謀的場景中,算法所代表的不同經營者收益彼此相關,且無法獨立優化。要想達到均衡,則需考慮聯合行動與各算法之間的連鎖反應。原則上,這需要算法程序之間互相信任并且訪問內部信息,但每個自主學習算法的設定是無法博弈和互相試探設定此類聯合行動與反應函數的,故而這無法在經營者或算法制定者不知情或不允許的情況下實現。鑒于此,自主學習算法必須面對價格不斷波動及算法之間對價格的信任認定問題,所以還需要預先引入寡頭壟斷者之間交換信息等輔助機制來確保共謀均衡的穩定性,但這又背離了自主學習算法引發市場系統性共謀風險的前提。
其次,交易信息和市場數據的非平穩性。每個算法智能體的最佳策略會由于其他智能體的反應而改變,這種交易信息和市場數據的非平穩性可能使算法之間的趨同屬性失效。如果將定價算法的博弈抽象為一個個獨立的階段,那么則需要進一步確定一個階段的確切構成以及階段內的時間長度。每個寡頭壟斷者可能對此有不同的認識和預測,從而導致對其他算法預期的均衡狀態判斷失誤,降低算法之間共謀的可能性和效率。同時,在計算各自收益時算法可能還需考慮其他經濟變量,包括需求預測、垂直整合策略、投入價格等。這些不斷變動的數據增加了自主學習算法達成共謀的不確定性。
最后,自主學習算法的“探索—利用”困境(exploration-exploitation dilemma)。算法的可拓展性是自主學習算法的主要特點,其中包括“探索”與“利用”兩種傾向。前者用于分析當前數據并對未來可能的更高收益作出預測,但過于關注“探索”的算法可能會錯失實現均衡的條件,不利于共謀的達成;后者則更關注已知的能產生最大Q值的狀態和策略,但也存在披露價格不充分、導致無法使價格處于競爭水平之上的風險。兩者的權衡是自主學習算法在開發現有知識與探索以改進現有知識之間的權衡,這也是多智能體環境下實現共謀均衡的一個障礙。
鑒于此,基于當下產業的實際狀況,自主學習算法尚不足以顛覆當前反壟斷法的制度框架。盡管有大量的新技術涌入,但市場競爭及其規制仍將以“人類為中心”。
(三)自主學習算法實現共謀的判定標準與理論內核
雖然自主學習算法目前在經營活動中仍需借助大量的輔助機制或限定性的市場條件才能夠完成共謀,但算法共謀潛在的系統性風險仍然引發了各國反壟斷執法機關的廣泛關注。自主學習算法所形成的共謀一般僅由算法基于預先設定的變量控制規則和函數運算結果與其他經營者的算法結成相互依賴的關系或實施一致行為,而無需達成公開或正式的協議即可實現排除、限制競爭的目的,這與默示共謀的特征十分契合。參與默示共謀的經營者通過經營者之間的依賴行為實現協調,而算法的快速發展使得競爭對手之間可以快速及微妙地進行互動,競爭對手可能以復雜的編碼為媒介去達成共同的目標。根據各國反壟斷法的制度安排,競爭者之間達成特定的“協議”(agreement)是反壟斷執法機關規制共謀的前置條件。例如,專門針對限制貿易的合同、聯合及共謀的美國《謝爾曼法》第1條在適用時即要求原告或執法機關必須證明在兩個或多個經營者之間存在固定價格或限制產出的協議。然而,自主學習算法引發的默示共謀在未進行客觀協商的基礎上,僅通過算法運算函數的設置即可達成一致,導致價格位于競爭水平之上。這種行為因缺乏客觀協商行為及明示合作的前提,故難以被納入協議的范疇,受到傳統反壟斷法的規制。鑒于此,我們還需進一步分析共謀形成的理論內核,以明確自主學習算法導致的共謀的判定標準。
1.拓展“協議”范疇的必要性
由于共謀是反壟斷法的“終極罪惡”,因而壟斷協議中的“協議”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法上的合同,也不具有普通民事合同所具有的法律約束力和強制執行力。根據法律解釋的相關理論,對“協議”概念的解釋應秉持法律目的和普通意義的雙重原則。雖然法律規則中概念的模糊性為法院尋找符合基本法律目的的解釋提供了自由空間,但是其所作的解釋必須符合概念的普通含義。也就是說,法院可適用法律目的來解釋概念,但不得突破普通含義的范疇。〔38〕See O. Black, Agreement: Concurrence of Wills, or Offer and Acceptance? 4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2008, p.108-112.
相對于反壟斷法,合同法中的“協議”概念更接近于普通意義,該語境下的協議通常包括“要約”和“承諾”兩個要件,且兩者應具備一定的客觀性,即要約和承諾都應是基于文字或行為等形式的客觀行為,并能夠被受要約人所客觀理解。同時,協議中的要約與承諾必須相互對應,即要約人和受要約人采取某種協調行為的共同意圖。除此之外,為了使相對人之間形成特定的法律約束,要約與承諾還應具備一定的精確性。在這種解釋中,客觀性和對應性要求是固有的定義特征,而精確性是合同法下要約和承諾的非固有定義特征。也就是說,固有的定義特征是作為協議構成概念的要約和承諾的普通含義固有或部分包含的那些特征;非固有的定義特征并非源于要約和承諾的普通含義,而是專門基于合同法的法律目的。未達到合同法規定的精確性要求的協議表明要約人和受要約人缺乏認真承諾,因此缺乏法律約束力。若要將合同法概念下的要約和承諾適用于反壟斷法時,需將固有定義特征和非固有定義特征進行區分。
2.判定反壟斷法“協議”的標準
當證據不足以充分證明存在協議時,該如何適用反壟斷法來規制那些具有明顯反競爭效應的“有意識的平行行為”呢?對屬于固有定義特征的客觀性和對應性而言,反競爭性要約和承諾必須根據雙方的客觀互動進行確定,并且必須涉及同一個聯合限制競爭行為,以便產生從事這種行為的共同客觀意圖;對屬于非固有定義特征的精確性而言,雖然共同客觀意圖對于締結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協議”是必要的,〔39〕See O. Odudu, The Boundaries of EC Competition Law: The Scope of Article 8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59-61.但是并不意味這種意圖必須與當事各方對某項具體的聯合限制競爭行為作出的準確承諾相關。鑒于合同法意義上的精確性要求并非要約和承諾的固有定義特征,其能否適用于反壟斷法還須考慮其一般目的,即是否阻止了反競爭活動。假設“要約”向競爭對手提出的建議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價格,盡管這是一個未包含精確性內容的提議,但仍可能引起競爭對手以反競爭的形式提價。同樣地,對于競爭對手的“承諾”行為而言,重要的是它們是否足以使要約人繼續實施限制競爭行為,而不是立即放棄。換言之,反壟斷法中的“協議”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抽象,只要它反映了共同的客觀意圖,即采取了一些具有反競爭意義的協同行動。例如,串通價格的一般共同意圖已經表明了反競爭的損害,此際要約和承諾沒有必要再詳細說明價格共謀的細節。雖然高度的精確性對于確保合同協議是自愿的并且對要約人和受要約人互利是必不可少的,但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協議只需要共同損害市場競爭的主觀意圖即可。由于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協議既不是其普通含義所固有的,也不適用于合同法的目的,所以無需遵守合同要約和承諾的精確要求。故此,上述分析支持客觀性和對應性要求作為固有的定義特征的持續相關性和重點,以及對要約和承諾精確性要求的適當放寬。當事人的共同意圖必須客觀而非主觀的確定,這種共同意圖可以由“實際的,語言化的交流”構成。
例如,在“Interstate Circuit v. United States案”〔40〕See Interstate Circuit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1939).中,有8家電影銷售商和電影放映商在與劇院訂立的放映合同中要求劇院對首輪放映的電影門票至少要收40美分,非首輪放映的電影門票則至少收25美分,同時,還禁止劇院將首輪電影與其他電影一起“雙片連映”,然而除了有包含變更條款的信件外,并無證據能證明銷售商們達成了協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地區法院認定銷售商們之間存在協議這是得到證據支持的,但我們認為在本案情況下,這種協議并不是認定存在非法共謀的前提條件。既然銷售商們之間的一致行為是策劃好的,銷售商們收到邀請后遵守這個方案,參與這個一致行為,知曉這些就足以認定非法共謀存在了。”〔41〕Interstate Circuit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226 (1939).這一觀點表明聯邦最高法院試圖根據表現出協議某些特征的行為來推斷存在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共謀。在“American Tobacco v. United States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再次提出了這種觀點,“要構成非法的共謀,并不是必須有正式的協議。犯罪的認定往往是從嫌疑人所為的、具有犯罪意圖的行為來推斷的。如果當事人的一致行為證明存在共謀——就像本案這樣,則更能有力地證明它們具有運用這種(通過共謀獲得的)排除力量的意圖。可以根據交易的過程或其他環境,或根據語言的交流來證明發生了《謝爾曼法》所要求的‘聯合’或‘共謀’。如果環境足以使陪審團認定共謀者們有從事某個非法安排的統一的意圖,或共同的設計與理解,或在某個非法安排上存在意思一致,則認定共謀存在就是合理的。”〔42〕American Tobacco Co. v. United States, 328 U.S. 781, 809-810, 66 S. Ct. 1125 (1946).
歐盟委員會在認定默示共謀時也不要求經營者之間必須達成具有普通民事合同特征的協議。例如,歐洲的幾個染料經營者在一段時間內多次以相同的幅度同時提高價格,對此德國聯邦法院認為,《反限制競爭法》第1條所指的合同與一般合同一樣是訂約人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礎上達成的一致意見。由于該案的卡特爾局無法證明經營者之間存在明確的協議,也不能證明存在要約和承諾,因而法院就認定當事人之間不存在合同關系,并進而推翻了聯邦卡特爾局的裁決。但是,歐洲法院卻將其視為違反《歐盟運行條約》第101條規定的協同行為。雖然經營者之間的協議沒有在立法上得到明確界定,但一般認為這里的協議所涵蓋的范圍比較寬。〔43〕See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ases, 48-57/69 [1992]ECR619: CMLR 557.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對協議概念的寬泛理解并不是毫無限制的。歐盟委員會曾明確指出,一項協議不需要以書面形式訂立,也不需要合同的批準或執行措施,協議存在的事實可以清晰地或含蓄地體現在成員的行為中。〔44〕See Robert Lane, EC Competition La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p. 51-52. 轉引自游鈺:《卡特爾規制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頁。
在此情況下,自主學習算法形成的共謀即有可能被納入反壟斷法的規制范圍。例如,其他經營者的算法可以客觀地觀察或爬取到價格領導者算法的共同提高價格“要約”的信號,并因此可能促使他們參與默示共謀。同時,價格領導者算法同樣可以客觀地觀察市場中其他算法對該提案的同意和跟隨,以促使其繼續參與共謀。這種共同提高價格“要約”通常會提高其價格作為一個客觀的信號,競爭對手也會基于“追隨策略”(follow-the-leader strategy)選擇是否跟進。如果被要約人的算法效仿并據此默示同意該提議,那么價格領導者的算法將被誘導以維持其高價;如果競爭對手的算法不跟進,那么價格領導者的算法就會放棄并將其價格調整回原來的水平。盡管要約和承諾都是通過行為和默許,但仍足以滿足客觀性要求,就像合同要約和行為接受一樣;盡管各方承諾的承諾程度較低,但模糊的默契仍可成為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協議。如上所述,合同法中的精確性要求應在競爭法的范圍內適當放寬,從而使其具有反競爭效果但內容模糊的默示共謀落入規制范疇。
當然,僅憑行為意圖來判定默示共謀仍存在極大的風險。例如,在古諾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中,每個經營者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入相等。一旦達到均衡,在其他競爭者產量不變時,自身價格即是自身利潤最大化的水平,任何個體的降價均會減少降價者自己的利潤。在實現這種均衡的過程中,經營者們的行為表現為不斷試探和提價,這與默示共謀的行為外觀十分相似,但其結果并不具有反競爭效果。在歐盟競爭法實踐中,這種例外也同樣獲得了關注。例如,在1975年的“Suiker Unie案”中,歐盟法院就認為:“不應一概剝奪經營者明智地適應其競爭對手的現有和預期行為的權利。”〔45〕Case 40/73 Suiker Unie, ECLI:EU:C:1975:174, paras. 174.
3.充分利用間接證據和環境證據
一般而言,若實踐中未能掌握經營者進行明示性共謀的直接證據,法院還可利用某些間接性證據推定共謀的存在。例如,在前述“Interstate Circuit v. United States案”〔46〕Interstate Circuit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1939).中,訂立價格維持條款和限制雙片連映條款可有效防止從這些銷售商那里得到電影的劇院之間進行價格競爭,并且使得劇院在所維持的價格上無法通過多放映一部電影來進行競爭。如果銷售商之間達成一致,迫使每個放映許可協議中都加上這兩個條款,則行為顯然是非法的。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對于這兩個限制,如果沒有一致性的同意,則會使自身的經營和商譽受到巨大的損失;但如果大家一致同意,則可以增加利潤。”〔47〕Interstate Circuit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222 (1939).換言之,單方施加價格維持條款和限制雙片連映條款不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據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環境證據來推斷存在明示的通謀。盡管這里只存在明示的“要約”,而無明示的“承諾”,但可從證據中推斷出存在承諾。
由于共謀的隱蔽性特點,許多案件無法以書面協議、口頭要約與承諾的證詞等直接證據來證實共謀的達成或實施,所以需要借助間接證據和環境證據來進行推定,此一方法在算法共謀中依然有效。例如,在前述“Eturas案”中,雖然使用E-TURAS軟件的旅行社均擁有直接與E-TURAS預訂系統對接的特殊郵箱來進行信息傳遞和接收,但該信息的閱讀方式與一般電子郵件相同,仍需以收件人打開郵件為前提。因而,該案佐審官(General Advocate)認為:“任何一個審慎負責的普通經營者均應(且必然)注意到涉案系統消息及其所參與的限制競爭行為,除非有證據能證明涉案旅行社未曾收到上述信息或未曾瀏覽相關版塊,否則涉案各旅行社均應被視為已知悉上述信息內容,并且在作出市場決策時已將其與競爭者互通過的信息納入了考量,從而被推定為參與了相關的協同行為。”〔48〕Eturas, C-74/14, ECLI:EU:C:2016:42.
但需注意的是,僅證明經營者有機會進行共謀或實施共謀在經濟上具有顯著的合理性尚不足以證明共謀的存在。在1954年的“Theatre Enterprises v. Paramount案”中,法院認為,電影發行商拒絕給予作為原告的電影院首映資格的做法反映了每個發行商的個體判斷,即原告電影院的位置使它不適合作為進行首映的電影院。于此情形,一致性的拒絕并不意味存在默示的協議,無論其他的競爭發行商如何選擇,每一個發行商都會拒絕給予原告首映資格,這些發行商的一致行為甚至不是有意識的。〔49〕See Theatre Enterprises v. Paramount Distributing, 346 U.S. 537 (1954).鑒于此,若要依靠間接證據或環境證據證明經營者之間存在協議,則還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只有在與其他經營者達成諒解,后者也對其行為進行同樣的調整的情況下仍具有經濟上的理性。尤其是隨著新業態商業模式的不斷涌現,算法已經與經營者的日常業務高度融合,若經營者的算法之間需要頻繁交互時,并不能據此證明經營者之間正在進行共謀。比如,當事人在行業協會的業務交流中時常會面,而討論議程之一正是要就正在惡化的市場條件進行討論,則不能僅僅根據這樣的事實就推斷他們在進行固定價格。只有當有證據證明會議上的確討論了固定價格問題,或討論了排除某個競爭者的計劃,則這些證據一般是可以接受的,可據此認定存在一項適格的協議。
四、應對算法共謀的法律路徑
來自于產業實踐的數據以及學界的研究表明,基于算法的自主和智能系統與現實社會的融合趨勢不可逆轉。雖然囿于算法運算能力、算法函數設計等客觀的技術發展瓶頸,算法共謀可能帶來的反競爭損害目前還未真正涌現,但算法共謀的系統性風險是潛在但可置信的。鑒于此,我們還需從算法內容、法律實施以及社會實踐等多個面向探究規制算法共謀的合理框架。
(一)算法內容面向的規制策略
作為一種存在明顯反競爭效果且無特殊行業監管背景的壟斷行為,算法共謀的規制通常應依賴反壟斷法律制度。但是,隨著算法對經濟社會影響的不斷擴大,在適用反壟斷法規制算法共謀問題時,還應充分考量算法在共謀活動中的作用和特性。
1.數據的收集和利用
算法共謀的實現有賴于海量數據計算所得出的預測性結論。而作為市場信息的重要載體,數據的使用和分享并不當然地違反法律。相反,數據的使用和分享能夠賦予潛在競爭者獲得進入特定市場的競爭力,因為“數據的規模是成為有效競爭者的重要因素”。〔50〕Comp/M.5727, Microsoft/Yahoo! Search business, 10 February 2010, §153.特別是作為實現算法共謀所必需投入品的成本價格、生產計劃等市場信息,在市場中并不能為公眾所直接獲得,而算法的介入,則大幅提升了信息交互的頻率、信息溝通的及時性。換言之,數據的收集和利用可能通過提高市場透明度和實現高頻交互來增加明示或默示共謀的可能性。若經營者之間可以毫無障礙地互相抓取關鍵的市場數據,并足以降低經營者作出市場策略的不確定性,即可認定存在協同。例如,《關于歐盟運行條例第101條適用于橫向合作協議的指南》就將經營者之間交換與未來的價格或產量等有關的個體性信息的行為可被直接認定為具有限制競爭的目的。此外,收集和利用數據可能會增加市場進入壁壘并成為市場力量的來源。經營者在算法中還以可利用用戶協議、“白名單”“ 黑名單”等方式設置特殊的數據抓取壁壘,則能夠為參與共謀的經營者提供獲得市場關鍵信息的途徑,從而實現算法共謀或者其他排除、限制競爭的結果。例如,在“Google收購ITA案”中,法院認為,除非擁有其他數據來源或者克服了數據的非對抗性(non-rivalrous),涉及獨特數據來源的排他性合同能夠通過投入品封鎖的方式形成市場進入障礙。〔51〕See U.S. v. Google Inc. and ITA Software Inc., Civil Case No. 1:11-cv-00688.鑒于此,在判定經營者之間是否利用算法實施共謀時,可進一步審查經營者是否對其非公開的關鍵市場信息設置了必要的保護措施,以及經營者之間是否存在頻繁數據抓取和信息交換。若經營者在基于數據抓取和信息交換等輔助行為進一步實施了某些平行行為或跟隨行為,且行為限制或者消除了合法競爭,則這種數據抓取和信息交換即可證明經營者之間存在共謀的意圖。
2.算法的內容設置
除了在數據獲取環節可能存在的執法契機外,對算法共謀的規制還可從涉嫌共謀經營者所使用的算法入手,對算法運行的機制進行審查。雖然目前算法的運行過程普遍處于“黑箱”狀態,但實際上人工智能算法的輸出仍是由數據和代碼決定的,并不會比自然現象更難以分析和解釋。〔52〕參見[美]萊斯格:《代碼2.0:網絡空間中的法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頁。反壟斷法并不禁止經營者之間獨立地采用相同或者類似的算法,尤其是在沒有產生一致性行為時。例如,如果多個存在競爭關系的公司在互不知情的情況下購買了相同的軟件來設定價格,并且該軟件使用相同的算法,這可能有效地調整了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定價策略,但他們并未達成共謀。不可否認的是,存在競爭關系的經營者采用相同或類似的算法來決定市場價格時,就可能導致中心輻射型共謀(huband-spoke conspiracy),因為算法接受市場信號后會基于特定的運算機制預測競爭對手的應對策略和市場變化趨勢。不同的函數設計和反應觸發設定會導致算法預測的結果及反應的時間存在差異,進而增加算法之間博弈的運算量和交互次數,而憑借相同算法產生的中心輻射作用可能引發行業性的共謀,進而導致產品價格的上漲。經營者是否愿意使用同一算法去提高價格等有關共謀意圖的證據便能幫助反壟斷執法機關去評估協議的目的以及可能產生的競爭效果。〔53〕參見[英]Ariel Ezrachi、[美]Maurice E. Stucke:《人工智能與合謀:當計算機抑制了競爭》,焦海濤譯,載韓偉主編:《數字市場競爭政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364 頁。
除了內容相同或近似的算法,特定的算法運行機制也可能對共謀的實現起到促進作用。例如,在線性勒索共謀算法實驗中,實驗人員通過該算法與人類進行多迭代博弈的市場實驗中發現,該算法能夠根據市場變化自動限制產量,進而迫使人類經營者執行超競爭策略并與之進行共謀,最終實現提高價格和提高利潤的不法目的。而根據實驗結論,當該算法與人類的迭代博弈達到300次時,雙方因未實現商品或服務均衡而導致的無謂損失激增12倍;當博弈次數達到600次時,共謀是不可避免的。〔54〕同前注〔35〕,Nan Zhou等文。鑒于此,反壟斷執法機關還應關注涉案算法的運行機制對實現共謀是否存在特殊的促進作用。若發現證據表明算法的選擇或開發過程是出于減少競爭之目的,則可能存在嚴重且明顯的違法風險。
3.算法的信任問題
無論是發生在參與共謀經營者之間,還是存在于經營者內部,信任始終是達成、實施共謀的重要條件。于參與共謀經營者而言,信任的建立和延續是做出并維持價格跟隨等一系列協同行為和平行行為的前提;在經營者內部,與其他競爭對手進行共謀的決定必須建立在公司管理層與股東之間互相信任的基礎之上。算法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共謀的實現。一方面,算法能夠更為全面地收集、獲取信息,并進而作出理性的博弈決策,提高經營者對參與共謀者的行為預期,增強經營者之間的信任,提升共謀實施的穩定;另一方面,算法能夠減少公司中參與共謀決策的人員數量,利用公司規模和管理架構所形成的信息不對稱來解決經營者內部決策的代理成本問題。
然需注意的是,無論作為基于單一的運算程式抑或是獨立的人工智能體,實現算法技術層面上的信任仍需要人為地公開或隱匿地操作。因為算法對數據的挖掘、獲取、分析并不能消除決策過程中對市場競爭狀況的定性需要。換言之,算法不能基于未經驗證的數據自動建立信任并形成知識或結果。〔55〕See C. Rygielski et al., Data Mining Techniques for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echnology in Society, (24), 2002,p.483-502.而驗證的過程即反映了人類經營者在競爭活動中的傾向與偏好。一方面,算法之間進行博弈和協同需要對競爭對手的特有數據進行接觸、獲取和匹配,以便相應地調整自己的價格,但計算機軟件無法自主驗證和信任另一個軟件,這個過程需要人類預先授予數據訪問和讀取權限,以解決算法之間互相信任的問題;另一方面,算法的自動化決策是基于預先設置的觸發變量在饋入數據之后作出的,這種對競爭狀況的判斷實際上是以定量的方式實現定性的任務。目前自主學習算法多智能體之間的共謀面對成本、價格或其他參數的微小擾動時并不穩定,表明算法在建立信任方面依然需要依賴于人為操作。〔56〕同前注〔36〕,Segismundo S. Izquierdo、Luis R. Izquierdo文,第 33-44頁。在不人為調整決策觸發變量時,算法只能通過市場價格的不斷變動與其他市場競爭者進行多迭代的博弈,而無法像人類經營者那樣利用關系型激勵輔助建立與共謀參與者之間的信任,進而直接進行價格的跟隨或其他協同。鑒于此,反壟斷執法機關還應關注是否存在人為修改算法的運行機制或觸發變量以實現對特定經營者或算法的信任。
(二)法律實施面向的規則設計
1.明確算法共謀的責任規則
在規制算法共謀時,還必須解決參與共謀經營者的責任問題。首先,在合理懷疑階段,需要在經營者與反壟斷執法機關之間配置解釋算法內容的責任。若要求采用定價算法的經營者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反壟斷執法機關或法院解釋其算法的功能,則可能潛在地限制可以使用的算法種類。例如,基于深層神經網絡的算法就很難向第三方以易于理解的方式解釋其功能。但若由反壟斷執法機關自行承擔算法的解釋責任,則他們必須證明經營者使用的算法確實導致了市場的共謀。雖然這會增加執法成本,導致反壟斷執法機關需要有足夠的內部或第三方計算機科學專業知識,特別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專業知識,但是這種解釋能力是反壟斷執法機關應對數字市場競爭挑戰和增強自身執法能力的必由之路。例如,意大利競爭與市場管理局(Autorità Garante della Concorrenza e del Mercato, AGCM)于2017年就已開始在IT和人工智能領域擴展其技能和專業知識。〔57〕See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Summaries of Contributions, https://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 df/?cote=DAF/COMP/WD(2017)2&docLanguage=En.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則于2019年2月組建了一個專門監督美國技術市場競爭的工作組(Technology Task Force),用于監督、調查和規制這些市場中任何潛在的反競爭行為。〔58〕See FTC’s Bureau of Competition Launches Task Force to Monitor Technology Markets: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9/02/ftcs-bureau-competition-launches-task-force-monitor-technology.
其次,如果經過解釋發現行為已經超出合理懷疑的范圍,即算法確實已經達到共謀均衡,那么會產生相應的違法責任問題。目前,若將責任配置給算法可能會嚴重阻礙技術的進步和推廣,而且一旦賦予人工智能技術相應的法律責任,則會使得問題從技術層面轉向了法律制度的建構基礎,進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59〕See ACM US Public Policy Council and ACM Europe Policy Council, Statement on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2017.此外,從競爭損害的角度來觀察,使用算法進行共謀與經營者之間的共謀對市場產生的反競爭效果是相同的,計算機算法只是實施或輔助實施了經營者的意圖,其仍在經營者的控制之下運行,因此經營者應對其行為負責。〔60〕See A. Ezrachi and M. Stuc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llusion: When Computers Inhibit Competi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5), 2017, p.1775-1809.例如,歐盟競爭法就認為,參與非法定價行為的公司無法避免因其價格由算法確定的責任,因為這種情形與員工或外部顧問在公司的指導或控制下完成特定工作相類似,〔61〕根據歐盟競爭法,公司應對其員工以及在其指導或控制下工作的外部顧問的行為負責。Case C-542/14 VM Remonts,ECLI:EU:C:2016:578, para. 27.所以自主學習算法是否被歸類為個人或是其實際操控者的行為延伸并不會影響責任的配置。
最后,除了積極的行為責任,經營者即使未從事違法行為,也不能采取被動的態度。因算法會隱匿經營者與算法之間的溝通痕跡,故經營者應與算法獲取或可接觸的商業敏感信息保持距離,否則經營者將因參與協同行為而承擔相應之責任。換言之,反壟斷法律責任不僅可由經營者的主動行為產生,而且也可由其不作為產生。在規制算法共謀行為時,因反壟斷執法機關在證據收集和獲取時處于被動地位,故應賦予經營者在與競爭對手交易時或從競爭對手那里獲得敏感信息時一定的“特殊責任”。〔62〕這類似于歐盟競爭法下對擁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所施加的特殊責任,以確保其行為不會限制競爭。Case C-322/81,Nederlandsche Banden Industrie Michelin v. Commission, ECLI:EU:C:1983:313, para. 57.例如,當競爭者設立合法的合資企業時,他們必須確保合作不會在其他市場產生溢出效應。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企業可能有義務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同樣地,參與合并的經營者需要交換某些商業敏感信息進行交易評估時,還需要采取保障措施,以確保信息交換不會觸犯反壟斷法,〔63〕歐洲委員會在并購交易之前沒有關于信息交換的決定,但在法國競爭管理局于2016年11月8日決定對Altice在收購之前對SFR施加影響進行罰款時表示,盡管準備集中通常會導致收購方與賣方或目標之間交換大量信息,然而無論公司可能需要交換信息的原因如何,他們都有責任采取措施消除獨立企業之間的任何戰略信息交流。Décision 16-D-24 du 8 novembre 2016 relative à la situation du groupe Altice au regard du II de l’article L. 430-8 du code de commerce, paras. 259-260.否則,即使在業務結束時并未產生違法行為,但協議仍可能是非法的。
2. 引入市場研究機制
成功的技術進步與商業創新所帶來的利益通常都遠超成本,〔64〕See Paul A. Johnson, Should We Be Concerned That Data and Algorithms will Soften Competition?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2),2017, p.5.然而,經營者利用數據與算法等創新方式所帶來的影響尚不明晰,現階段反壟斷執法機關對之很難給予充分、全面的理解和認識。鑒于此,需要進一步強化數字經濟下的執法能力,這不僅有助于執法機關在算法廣泛適用的新市場環境中科學、理性地調查和判定數字市場中的競爭行為,而且還能準確區分基于算法的科學預測行為和算法共謀行為。
反壟斷法規制由算法主導或輔助共謀的前提條件是存在算法與算法以及算法與競爭者之間達成、實施共謀,產生排除、限制競爭的負面效果或損害消費者利益的特定證據。雖然有諸多跡象顯示數字市場的運行存在一定的障礙,但是目前算法共謀對市場的損害尚未被證成。故此,反壟斷執法機關可引入“市場研究”(market studies)等創新執法機制,以強化數字經濟下的執法能力。例如,俄羅斯聯邦反壟斷局(FAS)考慮到定價算法適用范圍和規模的增加可幫助創建長期壟斷協議,而這些壟斷協議對執法機關使用傳統證明違規行為的方法不那么明顯,于是在2016年啟動了對電子商務零售市場的調研活動。FAS要求多家電子和家用電器經銷商向其提供算法的推薦價格、對競爭對手價格的考量因素等有關定價算法的信息。在分析這些信息后,FAS發現經銷商們在確定產品零售價時會使用Competera、Revionics等幾個特定的定價算法。同時,經銷商們對算法的使用方式并不相同,大致可分為四種:(1)收集或分析有關競爭者價格以確定產品范圍和其他信息的信息;(2)根據用戶上傳的數據自動計算價格并自動定價;(3)通過算法收集或分析競爭者價格信息以確定自動定價;(4)收集和分析針對特定品牌產品設置的經銷商價格信息以確定零售價格或建議/最低價格。〔65〕See Annu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ment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AR(2019)51/en/pdf.通過對所有可用信息的充分評估,FAS加深了對算法共謀的理解,進而認定此類軟件產品可用作識別價格偏差的程序,這與歐盟對電子商務領域市場調查報告的結果相類似。根據該報告,提高價格透明度可使公司更容易監控其價格。大多數零售商會追蹤競爭對手的在線價格,而其中三分之二使用自動軟件程序,并根據觀察到的競爭對手價格調整自己的定價。制造商越來越能夠使用定價軟件來即時監控和影響零售商的價格設定,而且實時定價信息也可能觸發自動價格協調。這種軟件的大規模使用會引起競爭問題。〔66〕See Final Repor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sector_inquiry_final_report_en.pdf.隨后,FAS于2018年2月認定LG公司在2014年11月28日至2017年2月15日期間協調其智能手機經銷商的經濟活動違反了《聯邦保護競爭法》第5部分第11條之規定。經查,經銷商的經濟活動由LG公司使用第三方機構研發的特殊價格算法進行協調,包括在網站上公布并通知經銷商LG智能手機的建議零售價格,迫使經銷商采取符合建議的零售價格,以及對不符合建議零售價格的經銷商實施制裁。〔67〕See Russian Subsidiary of LG Unlawfully Coordinated Prices for Smartphones, http://en.fas.gov.ru/press-center/news/detail.html?id=52813.而AGCM也于2018年2月成立了算法工作組,嘗試從平臺內和平臺間兩方面考察在線競爭中定價算法的市場影響。一方面,工作組嘗試從效率和潛在的反競爭效果出發,研究電子供應商廣泛使用算法來改進定價模式、定制服務和預測市場趨勢;另一方面,工作組還關注在線賣家使用的算法與在線平臺所采用的算法之間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經營者采用某些定價策略對在線平臺和市場所使用算法的影響。〔68〕See Implications of E-commerc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 Note by Italy,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WD(2018)32/en/pdf.2019年6月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政府也正在籌建一個新的數字市場部門,并計劃對由兩家公司主導且極度缺乏透明度的數字廣告市場展開正式的市場研究。〔69〕See UK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 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5547/unlocking_digital_competition_furman_review_web.pdf.
綜上,市場研究可幫助反壟斷執法機關“了解算法驅動型市場的最新動態以及任何競爭問題的嚴重程度”,〔70〕A. Ezrachi and M. E. Stucke, Two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Meet in an Online Hub and Change the Future (of Competition,Market Dynamics and Society), Oxford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s, 2017.甚至推動相關的立法活動。〔71〕例如,FAS就于2018年10月提交了《關于修改〈聯邦保護競爭法〉的修正案》,其中涉及定價算法、分析市場和調整價格。該修正案建議將“定價算法”的概念定義為旨在監控商品市場價格、計算商品價格、設定商品價格和監控商品價格或在投標時采取行動的軟件,并且在經營者使用類似算法來控制和規范與競爭對手關系的情況下開展壟斷協議的審查。See http://en.fas.gov.ru/documents/documentdetails.html?id=15345.同時,市場研究還可促進對產業界的倡導工作和建議,目的在于促進更強有力地遵守競爭原則。例如,根據市場調查的結果形成自我監管的行為準則,并在行業內使用定價算法時自行遵守。此外,反壟斷執法機關還可通過市場研究評估其政策或法規是否在數字市場中對競爭產生了不必要的限制,或者對數字競爭者與非數字競爭者之間的競爭產生了不必要的限制,并且還應考慮可能的促進競爭的替代方案。〔72〕Se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G7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n “Competi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http://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doc/g7_common_understanding.pdf.
3. 制定算法應用的負面清單
隨著反壟斷執法機關對算法應用的理解逐漸清晰,算法的引入不僅能夠大幅度提高商業活動的效率,而且還能夠改善消費者決策,提升消費者福利和社會整體福利。鑒于此,反壟斷執法機關對算法的應用不應秉持行業監管的策略,而應放松對市場結構的管控,鼓勵和推動技術的適度進步,僅需對那些具有明顯反競爭效果的算法類型或行為進行干預或規制即可。雖然目前對算法內容以及運行結果的理解尚需進一步加強,但一旦經過實證確認其具有顯著的反競爭性,則能極大地降低反壟斷法的實施成本,并且給予經營者明確的算法適用指引及合規預期。例如,已有學者利用空間計量的方法來測試價格或行為可疑的經營者,并通過一種算法來篩查最可疑的經營者集群。〔73〕See Adriaan R. Soetevent et al., Screening for Collusion: A Spatial Statistics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5) ,2015, p. 417-448.當前,對算法應用的審查主要來自于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是否促進非法的信息交換。明示或默示的溝通和信息交換是實現共謀的必要手段。換言之,反壟斷法并不禁止無意識的平行行為,而僅對可導致算法之間非法信息交換或數據抓取的算法應用行為進行規制。這在算法程序中可能表現為將收費價格以可解碼的編碼形式互相傳輸和接收,也可能表現為接收或抓取競爭對手價格后呈現的特定反應。二是算法是否具有支持價格高于競爭水平的特征。實現超競爭性價格是進行共謀的目的,因此執法機關應審查經營者的算法中是否包含支持價格高于競爭水平的機制。例如,有學者認為“應禁止具有支持價格高于競爭水平特征的算法”,并提出了以是否產生超競爭水平價格為標準的三部檢測法。〔74〕首先,使用學習算法創建模擬市場環境,以產生共謀均衡的結果。其次,檢查產生預定結果的算法函數,以便識別超競爭價格時出現而競爭性價格時不存在的內容。最后,測試禁止某一組反競爭算法函數后的市場模擬效果。See J. E. Harrington,Developing Competition Law for Collusion by Autonomous Price-Setting Agents,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3), 2018,p.356-357.而法、德競爭管理機構的聯合報告指出:“由于算法的原因,人為地增加了市場透明度,從而導致了競爭風險。例如,通過處理所有可用的信息,從而監控和分析或預測其競爭對手對當前和未來價格的反應,競爭對手可能更容易找到他們可以同意的可持續的超競爭價格均衡。”〔75〕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and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DE/Berichte/Big%20Data%20Papier.pdf.因此,為了降低數字市場中經營者之間的高頻互動可能導致的共謀,執法機關可能要求降低算法對價格的調整反應時間或者要求經營者承諾在最低等待期后才能提出新的要約。〔76〕同前注〔19〕,OECD 文。三是可能便利共謀的數字市場的其他特征。開發有利于促進競爭的算法需要先進的數據挖掘系統、機器學習軟件及海量數據等基礎條件,這些會受到公司規模和市場壁壘的影響,尤其是沒有技術儲備和充分數據支持的中小公司或其他潛在競爭者可能面臨進入障礙,阻礙他們開發能有效施加競爭壓力的算法。鑒于此,反壟斷執法機關應審查涉案經營者的算法中是否就市場敏感信息的傳遞與交換進行限定性分享和傳輸或其他便利共謀的算法特征。
(三)公眾能力面向的行為引導
算法是結構化的決策過程,其使用一組規則或過程來基于數據輸入和決策參數自動提供結果。編碼算法通常使用預定的決策集,該決策集將權重分配給決策參數,以便在給定特定數據和環境的情況下建議最佳決策。決策參數及其權重由算法設計者設置,以優化用戶的決策。〔77〕See OECD, Data-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 Interim Synthesis Report 4 (2015).更高級的算法采用機器學習,即算法從其自己對先前數據的分析中學習如何優化和重新定義其決策參數的過程,從而使算法從預定義的偏好中解放出來。同樣地,算法也可幫助消費者在市場交易中作出決策。例如,算法可為消費者提供與其選擇相關的信息。這些算法用作通過聚合和收集相關數據來增強消費者選擇的工具,以幫助消費者作出明智的決定。〔78〕See Prashant R. Nair, E-Supply Chain Management Using Software Agents, CSI Communications, (6), 2013, p.14.這種通過分析數據,輔助消費者作出消費決定的算法被稱為算法消費者(Algorithmic Consumers)。近年來,國際競爭法理論界將算法消費者視為一種與算法問題相關的市場化解決機制。技術能力和消費者需求的綜合影響促進和加速了算法消費者的興起。海量數據的存儲和分析方面的技術進步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日趨成熟使得算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方便和強大。〔79〕See Ariel Ezrachi & M. E. Stucke, Virtual Competition: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 Algorithm-driven Economy, 2016, p.11-21.算法消費者理論的主要倡導者Michal S. Gal教授認為,算法消費者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供應商使用算法帶來的負面福利效應。〔80〕See Michal S. Gal, Algorithmic-facilitated Coordination: Market and Legal Solutions,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2), 2017.換言之,如果某類算法消費者數量足夠多,或者某類算法消費者可與其他算法消費者相互協調行為,那么算法消費者可獲得買方勢力,這轉而可能讓消費者抵消供應商的力量。算法消費者可因此改進市場動態,限制共謀,抵消算法導致的負面影響。
五、對中國的啟示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進化以及數據運算能力的日漸提升,算法在數據驅動型市場中的作用越發重要,甚至對市場競爭方式也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不僅引起了社會大眾對隱私權和消費自主權的關注,而且引發了各國反壟斷執法機關對潛在競爭問題的關注。雖然算法誘致的共謀問題在實踐中偶有暴露,但人工智能技術支持下的算法通過與海量數據的充分結合極大地增強了共謀行為的隱蔽性,尤其是日益復雜的算法在重復博弈中成為了促進共謀行為的關鍵要素,甚至還可能自主制定并實施定價策略,從而在沒有人類經營者提供任何明確指令的情況下學習共謀,由此導致算法共謀的查處難度極高。而作為全球數字經濟最活躍的市場之一,中國的反壟斷執法機關同樣需要審視算法共謀問題的應對問題。
(一)加強和深化執法機關對反壟斷制度和規則的理解與適用
首先,要明確《反壟斷法》對算法共謀的可規制性。算法共謀的復雜性不只在于算法引致共謀的識別更為隱蔽,還在于對反壟斷法下傳統概念的沖擊,尤其是對在無經營者人為干預的情況下算法通過重復博弈實現共謀是否能被傳統反壟斷法理論中“壟斷協議”概念所涵攝。我國《反壟斷法》僅在第13條中通過“原則規定+列舉”的方式界定了“壟斷協議”的范圍,并未界定“協議”的具體含義,這種原則性規定未能明確構成壟斷協議的具體要件,為利用算法輔助實現共謀的行為以及自主學習算法共謀的認定帶來了一定困擾。為了區別未經協商達成的一致行為,應加強和深化反壟斷執法機關在認定壟斷協議時適度擴張“協議”的固有概念,強化對共同損害市場競爭主觀意圖的考察,弱化“協議”的形式要件,從而為規制算法共謀行為提供充分的法律實施空間。
其次,明確間接證據的推定與抗辯規則。算法可被共謀者用作規避法律風險的工具,特別是在經營者形成默示共謀的情況下,共謀者之間沒有達成明確的協議,這更增加了算法共謀被查處的難度。此際,反壟斷執法機關往往是通過市場的異常變化來推定經營者之間是否達成了共謀。〔81〕推斷算法共謀的輔助證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個方面:(1)經營者同時或幾乎同時宣布提價;(2)經營者頻繁地交換信息;(3)經營者同時發生商業策略的重大變化;(4)經營者出現與個人利益不一致的統一行為;(5)經營者沒有明顯的經濟壓力而發生異常變化;(6)經營者保持長期的一致高價;(7)行業領導企業存在領導價格的歷史等。但需注意的是,適用這種輔助證據的推定時需要十分謹慎,只有在排除一切偶然因素的情況下才可作出推定。例如,市場中占據市場優勢地位的兩個經營者對某種商品長期保持相同且遠高于成本水平的價格,并隨時保持價格的同步變動,這種情況下可以推定相關經營者之間達成了共謀。這種根據輔助證據推定的方法只有在確實無其他方法可用時才可使用。正如歐盟法院在“Eturas案”給立陶宛最高法院的回復中援引了“T-Mobile 案”的觀點并認為:“任何經濟主體都應自主決定其在共同市場上所要遵循的政策。這一自主性要求嚴格排除前述經濟主體之間任何形式的接觸,當這些接觸的目的或效果是為了在相關市場上創造一些與正常競爭環境不相同的競爭環境時,無論它們是直接的或是間接的,只要從本質上看,這些接觸影響了市場上某一現有或潛在競爭者所采取的行為,或這種接觸向某一現有或潛在競爭者公開了自己已經或即將在市場上采取的行動。”〔82〕T-Mobile Netherlands and Others, C-8/08, EU:C:2009:343; Eturas, C-74/14, ECLI:EU:C:2016:42.若旅行社能舉證證明自案件所涉信息發送之日起已對其內容有所了解這一推定的可能,如證明自己未收到該信息或未查閱所涉板塊,抑或僅在收到該信息一段時間之后才對其進行查閱,則應能推翻法院對涉案旅行社的推定。
最后,重新配置算法共謀行為的責任承擔。算法的介入極大地拓展了可能參與共謀的主體類型和范圍,《反壟斷法》需要對在試探、博弈、達成及實施共謀等不同過程中以不同身份和角色參與共謀的經營者合理配置不同程度的法律責任,從而強化經營者的合規意識,規范其利用算法參與市場競爭的行為。有學者認為,在討論如何針對機器人賣家(Robo-Seller)實施的反競爭行為施加責任時,可以設置機器人賣家承擔責任、部署機器人的人類承擔責任或不設置責任承擔者。〔83〕See Mehra, S. K., Antitrust and the Robo-Seller: Competition in the Time of Algorithms,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100, 10 March 2015.目前,絕大部分的計算機程序與算法僅僅被視為工具,仍需基于人類設計的指令運作,因此這類案件中人類經營者仍需就算法決策承擔責任。誠如歐盟競爭委員Vestager所言:“自動化系統帶來的挑戰是非常現實的。如果它們幫助企業固定價格,這將讓我們的經濟變得糟糕。作為競爭執法部門,我們需要確保企業不能通過躲在計算機程序后面而逃脫共謀的法律責任。”〔84〕Vestager, M.,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Speech at the Bundeskartellamt 18th Conference on Competition, Berli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commissioners/2014-2019/vestager/ announcements/bundeskartellamt-18th-conference-competition-berlin-16-march-2017_en.而對于自主學習算法主導的共謀是否能豁免部署該算法的經營者的法律責任則還應進一步審核算法的內容,以判斷市場異常的出現是否屬于未經協商達成的一致行為。此外,我國《反壟斷法》對法律責任的承擔對象限定為經營者,并未考慮以自主學習算法為代表的異類主體的可責性。對此,可考慮在責任條款中強化違法行為與法律責任的對應關系,弱化違法行為與經營者的單一關聯關系。由違法行為配置責任的承擔主體,并根據人工智能倫理規則的演進狀況適時調整部署算法的經營者與自主學習算法之間在責任承擔上的界限。
(二)創新和完善反壟斷執法機關的執法手段
首先,應增強反壟斷執法機關對數字監管技術的運用能力。傳統反壟斷執法工作依賴于對實物證據的收集、固定、整理與梳理,但在規制算法共謀的過程中,反壟斷執法機關需要強化對數字技術的理解、識別及監管技術的應用能力,通過引入技術專家對各類算法運行的技術原理以及算法函數與變量進行研判。針對基于算法協調價格的違法行為,還可適時引入商品價格跟蹤與回溯技術,便于比較、分析涉案經營者之間價格的變化趨勢,提升電子取證和存證效率。
其次,通過引入市場研究等創新執法手段,對算法在特定細分市場中的應用情況進行調查,對明顯具有競爭損害的使用方式設置負面清單。規范算法等新技術的合理競爭范疇,引導市場主體參與和進行良性競爭。
最后,進一步引導涉案經營者適用寬大制度。寬大制度對發現算法共謀行為、節約監管執法資源、有效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但長期以來,我國《反壟斷法》第46條第2款對寬大制度的規定十分模糊,在責任減免、適用條件和程序規定上都缺乏對執法機關和經營者的指引。雖然2019年通過的《禁止壟斷協議暫行規定》對寬大制度作出了進一步細化規定,對如何認定重要證據、減輕或免除處罰的考量因素給予了明確規定,增強了涉嫌違法者適用寬大制度的行為指引,但監管機關仍應遵循“人類中心主義”的基本規制思路,針對算法的實施者及時進行制度宣傳和心理勸導,破壞參與共謀經營者之間的信任平衡,化解算法對共謀穩定性的積極影響,提升辦理相關案件的執法效率。
不可否認的是,算法共謀問題只是數字市場競爭中的冰山一角。新技術、新業態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會持續對傳統反壟斷法理論產生沖擊,并對反壟斷法的實施提出新的挑戰,這需要中國反壟斷法學界與實務部門的持續關注與精誠合作,共同探索應對數字市場反壟斷制度變革的中國方案,塑造中國數字經濟的競爭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