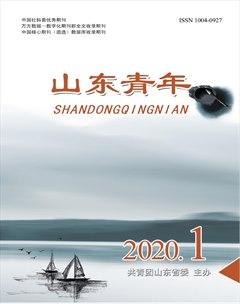從公民的網絡表達淺析當前我國公共精神
孫培鑫
摘要:
公共精神對于我國面臨的向“大政府、大社會”的轉型有著不可或缺的意義。網絡使用者的數量隨著近些年來的科技發展,不斷遞增,而與此同時,網絡表達也成了公民參與社會的一種重要途徑,然而由于公共精神的缺失,網絡表達不斷的呈現亂象。本文從公共精神的含義出發,探究我國目前公民所抱持的公共精神的現狀,并結合現狀分析其成因,最后探究得出如何通過教育實現對公共精神的培育并完成向“大社會的轉型”。
關鍵詞:公共精神;培育;公民社會;青少年教育
2019年韓國一位年僅25歲的女藝人雪莉因長期遭受抑郁癥困擾自殺離世的新聞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可否認的是,其所遭受的網絡暴力是其死亡背后的重要推手。與之相同的是近年來我國各行各業內飽受網絡暴力困擾者愈加繁多,這種現象的背后恰恰體現了當前我國公民的公共精神方面的欠缺。
一、公共精神的含義
“公共精神”一詞的具體定義,目前學界并無統一通說,但就其內涵而言,國內外學者卻已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公共精神是孕育于人類公共生活之中,位于人類心靈最深處的基本道德倫理和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一種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1]它包含對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責任等一系列價值命題的認可與追求。[2]從本質上說,公共精神要求公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表達自己的公共關懷,并從主觀意志到實際行動上都要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來。[3]
就個人理解而言,公共精神意味著要用一種更廣闊的視角去看待問題,處理問題,而不僅僅從自我、利己角度出發,是一種更積極、更主動的社會參與,是將“我”變成“我們”的一種思維方式。
以微博上曾發起過的一場“我不是完美受害者”運動為例,多達2000多萬人參與了這場反對強奸犯罪中常見的“受害者有罪”理論的線上運動,其中有數萬名女性分享了自身相關的極不愉快的過往經歷進行參與,意在用親身經歷證實在性犯罪中不存在“完美受害者”,而任何一個受害者都不應該再因為其并非“完美受害者”而承受網絡上或者生活中的任何道德指責甚至“蕩婦羞辱”。
這種發聲意味著她們每一個個體都意識到了“她們”群體的存在,她們在用個體的力量對抗對于社會“偏見”保護個體、鼓勵個體,也在用個體集結的力量對抗“偏見”保護群體,鼓勵群體,此即公共精神的體現。
二、我國公民公共精神的現狀
(一)抱持公共精神的人數不斷增多
近年來我國的互聯網普及率持續走高,直至2018年6月,我國網民數量已經突破八億,其中手機網民比例高達98.3%。隨著互聯網的高度普及化,針對社會問題提出觀點的途徑更加廣泛,提出觀點的成本更低,針對提出觀點主體身份的要求也幾近于無,同時幫助他人的成本也不斷降低,只需要“轉發”即可幫助形成輿論壓力,因而大多數人在網絡平臺上對于社會事件展現出了十足“熱心”,當今社會中甚至衍生出一種新的形式——“微博立案”,即如果當地政府或者有關部門拒不受理,可以將相關證明材料發至微博平臺上,通過吸引網民的注意力形成輿論壓力,進而督促政府或者有關部門受理并解決問題。
如上所述,如今在網絡平臺上已經逐漸開始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群體表達——造成輿論壓力——能夠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能夠維護權益——公眾樂于表達”,這種良性循環促進越來越多的人愿意進行公共參與,而在公共參與的過程中又能進一步培養公民的公共精神,故而我國越來越的的公民開始保持公共精神進行社會參與。
(二)公共精神的深化程度不足
然而由于傳統的文化和教育的缺失兩方面的原因,導致我國公共精神下的社會參與展現出參與廣泛、但深化程度不足、效力缺乏的現象。
1、傳統文化導致公民社會的缺失
這主要是由于我國長期以家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使家庭、家族成為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基礎,而傳統社會結構的特征是家—國—體使公共空間在傳統社會結構中發育不良。而我們常常講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由血緣人倫向外推及的慈善,其過渡不是社會倫理的運作而是家族倫理情感的擴展,這使得我們難以產生對素不相識的人和對社會的關懷和責任。正是這種“愛有等差”的觀念使得我們的慈善觀缺少博愛精神所具有的、普遍抽象的公共精神。[4]
這種影響體現在網民的參與中,致使目前網民的社會參與更多的只能流于表層,即不深入、不持續。目前大多網民的參與并非是因為他們真正的將視角從“個人”轉向了“群體”,真實的意識到他們是“群體”中 的一員。故而在參與成本提高時,就會有相當數量的人停止參與或者放棄參與。這導致我們目前許多社會事件呈現出虎頭蛇尾的狀況,在初期大批人進行表態,聲勢浩大,而事件后期卻無人問津。這種形式上泛濫的“公共精神”,導致許多問題的社會參與呈現出嚴重的后勁不足,難以真正發揮效力。
2、培育公共精神的教育缺失
“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不僅是一個凸顯公民價值與權利的民主社會,而且還應是一個倡導公民參與意識、責任意識的社會。”[5]而目前我國對于公共精神既缺乏倡導性的教育,也缺乏相應的責任意識培養,這也是當前我國頻頻出現網絡亂象的原因。
未經過相關教育的大多數人的網絡表達是情緒表達而不是理性表達,表達的目的在于宣泄情緒,這種隨意表達和任意參與帶來了兩個后果:一是在進行社會參與時,表達、參與很難成體系,各自有各自的立場,很難形成合力促進一個共同的目標達成;二是網絡信息的繁雜、真假混合,社會參與的網絡環境混亂,嚴重沖擊了未形成完整世界觀的青少年,會影響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進而對未來的網絡表達環境乃至社會參與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三、從教育角度談公共精神的矯治
公共精神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是一種意識,而意識是不能被強加的,想要培育或者提升某種意識,只能通過教育。具體針對公共精神的教育則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
一是加強公共精神的意識教育,從兒童時期就開始培養青少年的相關意識,潛移默化的從意識層面進行公共精神的培育;
二是加強青少年的參與與實踐,給予青少年更多的參與機會,鼓勵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觀察社會中種種需要改善的問題,允許以提案或者報告的形式提交給老師、學校或者某個校外組織機構,而接收者也要及時給予提交者反饋,除此之外也可以定期從中擇優改進后進行試點。
如此一來,即可將青少年培養出積極主動進行社會參與的習慣,而青少年的關注點也將僅僅從“個人”、“考試”、“前途”中移向更廣闊的社會、世界,而思考角度也將從個人的“我”逐漸轉向群體的“我”,逐漸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一種社會氛圍,當這部分具有出色的公共精神的年輕一代成長起來后,我們就將彌補被傳統文化影響進而缺失的“公民社會”,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將完成向“大社會”的轉型。
[參考文獻]
[1]劉鑫淼.試論公共精神的哲學意蘊——基于現代性的考量[J].廣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65-70.
[2]馬俊峰,袁祖社.中國“公民社會”的生成與民眾“公共精神”品質的培養與化育[J].人文雜志,2006(1):18-23.
[3]朱蕾.大學生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協同培育[J].揚州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19,23(05):33-37.
[4]譚莉莉.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J].探索,2002(04):52-55.
[5]甘紹平.論公民社會 [ A].對話中的政治哲學 [ C].北京:人民出版社.
(作者單位:北京理工大學,北京102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