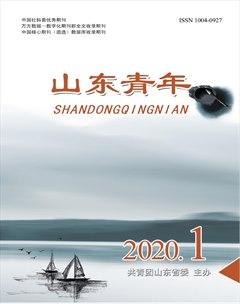簡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傳統法治文化發展
武群健
摘要:
法治文化作為社會治理文化的重要組成,不僅對以往國家與社會治理產生重要影響,對今天我們的社會生活仍然發揮重要作用。了解傳統法治文化,理解其中法治文化的本院于特質,從中汲取我國法治發展過程中的智慧與經驗,對今天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學說,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起著積極的引導與載體作用。通過對儒學發展的研究,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清傳統法治文化發展脈絡。
關鍵詞:法治文化;儒學;魏晉玄學
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法治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國家和民族長久以來社會治理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其產生與發展受傳統文化影響頗深,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也成為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法治文化的重要載體與對象。自西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實施以來,借助與政治結合以及官方力量的推廣,儒學在社會中傳播速度大大加快,西漢中期以后,儒學以兩個向度即從社會上層到社會底層、從若干個中心向更廣區域傳播,引起東漢社會儒學的同質化,在儒學廣布的地區,其價值逐漸成為共同的社會價值觀。[1]自此以后,儒學成為歷朝歷代所提倡、支持主流學說,也成為中國傳統法治文化沿襲與發展的主要載體。魏晉南北朝時期處于中國傳統法治文化發展定型階段的初期(發展期),對于后世傳統法治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與意義。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處于長期戰亂與分裂狀態,社會形勢動蕩復雜,儒學獨尊的地位雖然受到沖擊,但仍受到各朝代當權階層支持,其地位仍較為鞏固且有所提高,再者當時的社會環境也會儒學的傳播提供了契機,特別是南方地區儒學文化發達區域的形成,最終也為中華民族法治文化邊疆的擴展提供了堅實基礎。窺一斑而見全豹,以這一時期儒學發展為主線,對于幫助我們更加直觀的了解中國傳統法治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儒學自身的發展
對于這一時期儒學的發展,學術界主要存在強盛與衰弱兩種觀點,之所以產生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筆者以為, 這是因為這一時期的儒學是學術思想、官方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三位一體的復合體。[2]這幾乎說明這一時期的儒學已經不是單一且明確的個體了。從價值觀判斷的視角出發,天命論的動搖, 致使抑君申臣思潮和“時遇論”命運觀的興起, 導致儒學凝聚社會精神的作用崩塌, 其追求道德理想主義的的夢想破滅,儒學喪失了社會精神支柱的地位,這是學術界認為其衰落的主要原因。儒學自身學術思想追求與官方意識形態身份的相互糾結導致其衰落,但從法治文化傳統角度來看,儒學在社會、政治、生活的芳芳慢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還有愈演愈強之勢, 尤其表現為禮法合治的興起與發展[3]禮的興起,除了應對社會流弊的需要,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存在為其興起發展提供土壤養分的文化傳統,如建安年間, 曹操西征途中經過弘農王冢, 猶豫是否該謁, 董遇認為:“《春秋》之義, 國君即位未逾年而卒, 未成為君。弘農王即阼既淺, 又為暴臣所制, 降在藩國, 不應謁。”[4]曹操的猶疑和董遇的回答, 反映了當時的人生活在一種禮文化氛圍中, 禮制作為約束人們行為的一種規范而被人們所廣泛認可,除此以外,將禮作為治理國家的手段和法結合協調起來也足見人們對其的重視。這也體現了傳統法治文化具有強大的自在性,凡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無不受其影響,并為其所塑造。儒學發展受傳統文化影響,同時反過來,其對傳統文化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在典籍尤其是在經學方面,古文經學的繁興,經書注解集解體和義疏體也大大興起[5],為傳統法治文化的傳播提供了途徑;在價值觀方面,儒學的發展并對士人人格的建構產生了重大影響,強調士人在批判玄風流弊的同時, 增強了忠孝仁義意識, 固守家學傳承中的儒學內涵, 這有利地促進了東晉士人的家族觀念與儒學文化心態, 也在更深的層次上推動了儒學向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滲透, 呈現出生活化的特點[6],對人們的心理預期和價值判斷起著權衡和引導作用,為傳統法治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生存土壤;在法律方面,從“春秋決獄”到“納禮入律”,儒學思想漸漸融入法律,對后世法律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7],并未后來法治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方法;在文學方面,儒家政教觀對魏晉賦格建構起了重要作用, 儒家王權一統、“比德”的政治文藝觀念在時代的流變中不斷地滲透至魏晉辭賦中, 并逐漸造就了魏晉辭賦宏闊、淵雅、醇和的精神氣格[8]。
二、儒學與其他學說的交叉發展
1、儒學與玄學的關系
魏晉南北朝時期, 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態勢是相當蓬勃的,各種學術思想涌起, 玄學作為眾多學說中的一種, 在這一時期得到迅猛的發展, 后世哲學家在寫作哲學史時常常以“魏晉玄學”來概括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學說概況, 可見玄學在這一時期地位之高。關于玄學的性質, 一直以來備受學界的關注, 爭論的關鍵在于如何理解玄學與儒學的關系, 這些爭論中有的學者主張二者是相互對立的, 有的學者認為二者是相互影響滲透的, 也有學者提出玄學是儒學的一種表現形式。然而, 不管爭論最終的結果如何, 開展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研究, 必然不能將玄學拋之在外。[9]從儒玄關系的視角進行考察,首先,玄學的產生與儒學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玄學產生與漢代儒學的分裂以及儒道之間的融合,而且玄學產生以來,與儒學的關系也并非我們想象的那般排斥對立,反而對儒學的發展起到了有利的促進作用[10];其次,作為這一時期玄學產生與發展載體的玄學家們,本身也大多是儒學的傳承者,這使得儒學的功能作用實際涉及兩個不同領域, 即政治領域和知識分子的士風學風領域, 如此一來, 魏晉玄學興盛背景下的儒學式微, 實際只是儒學在后一個領域有嬗變的趨勢, 傳統儒學的深厚根基并未真正動搖[11];此外,在士人人格建設方面,一些士人既遵循儒學規定的道德倫理, 又對相關玄學思想表達欣賞與肯定 。
玄學產生于儒學又不拘泥于儒學,反而對儒學進行了一定的改造,并且藉此對傳統法治文化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在法律觀方面,玄學的本體論為法律觀的發展提供了直接的理論淵源,其中“貴無”“崇有”的主張打破了傳統儒學僵化的模式,形成了“執一統眾”“以簡馭繁”的思維模式,律學家們吸收借鑒了玄學中辯名析理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方式,使得律學研究進入了融通諸家學理、以學理統率律條的新時期;其次,在法律思想方面,隨著社會的動蕩與“君權神授”思想的動搖,玄學家們主張以自然為本,名教為末,提倡“崇本息末”,從哲學角度為后世法律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2、儒學與佛道關系
魏晉南北朝時期, 多種學說紛涌而起, 外來佛教在中土逐漸生根發芽, 本土之道教亦在蓬勃興起,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 儒學與佛道之間呈現出以既相融相攝又相拒相斥作為三教相處基本形式,以內容的廣泛性、主體的模糊性、義理的互補性作為三教關系基本特征的局面[12]。
首先是三教之間相斥相據的發展,隨著佛教勢力的增強, 佛與道、儒之間的斗爭逐漸展開并日益激烈, 其間較大的爭論有“沙門不敬王者之爭”“因果報應之爭”“夷夏之爭”和“神不滅之爭”, 四次爭論不僅促進了道教的發展, 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13]。另外,這一時期,三教的發展也呈現相融相攝的態勢,具體表現既包括梁武帝的援佛入儒,將佛學的佛性融入儒學的心性之中[14],佛學中的慈悲思想與寬恕理念更是對傳統法治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又包括道門中人多儒道雙修, 闡揚儒家禮教,將儒家倫理道德規范改造為道教的戒律規范成為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等[15],此外,道家還吸收儒家“重民”思想,主張“與民休息”“清凈無為”,在立法方面,道家還主張“大制不割”,對于法治文化中關愛百姓、輕刑薄賦的法治理念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諸如此類,既體現了儒學在此階段對佛道兩教的影響,又體現了儒學發展并未停歇的態勢, 主要以經學的方式存在并發展, 并攝取了佛、道的相關內容, 為后世傳統法治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后來傳統文化的多元活潑包容心態的發展提供了指引。
總的來講,這一時期傳統法治文化的發展,仍然是在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的大框架范圍內進行的,其發展并沒有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從另一方面講,這一時期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的發展也強化了傳統法治文化在整個社會層面的影響力,中國傳統法治文化的“文化疆域”也大大擴展了。
[注釋]
[1]夏增民. 儒學傳播與漢魏六朝文化變遷[D].復旦大學,2007.
[2]余英時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中談道:“漢社既屋, 經國之儒學乃失其社會文化之效用;而宋明理學以前, 儒家性命之學未弘, 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資, 老釋二家亦奪孔孟之席。唯獨齊家之儒學, 自兩漢下迄近世, 綱維吾國社會者越二千年, 固未嘗中斷也。而魏晉南北朝則尤為以家族為本位之儒學之光大時代, 蓋應門第社會之實際需要而然耳!” (《士與中國文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399頁) 又, 杜維明在《論儒學第三期》一文中談道:“學者通常也都以為, 隨著漢朝的覆亡, 儒術也黯然失色了。不過, 正如余英時以及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樣, 儒家的生活方式不僅在社會上繼續存在, 甚至還更加盛行。門閥世族在這個時期興起, 居于統治地位, 都帶有儒家色彩, 盡管儒家體制分裂了, 儒家規范卻在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美]杜維明著, 錢文忠、盛勤譯:《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第150頁。)
[3]郝虹.魏晉儒學盛衰之辨——以王肅之學為討論的中心[J].中國史研究,2011(03):45-59.
[4]《三國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魏略》, 第420頁。
[5]周培佩.《隋書·經籍志》與魏晉南北朝學術[J].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23(02):65-67.
[6]孫寶.東晉儒學文化型態與士風[J].理論月刊,2008(07):44-47.
[7]武劍青.從“春秋決獄”到“納禮入律”——淺析儒家思想融入魏晉北朝諸律的必然性[J].柳州師專學報,2005(02):127-129.
[8]孫寶.儒家政教觀與魏晉賦格建構[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8(05):1-6.
[9]吳艷.21世紀以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研究述論[J].唐都學刊,2017,33(06):92-98.
[10]薛勝元.儒學分裂與玄學產生——論漢魏社會思潮的變化[J].文史博覽(理論),2012(06):39-41.
[11]巴曉津.玄學代表人物的儒家素養與魏晉儒學之傳承[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2):32-36.
[12]李承貴.儒佛道三教關系探微——以兩晉南北朝為例[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04):12-18.
[13]湯其領.試論東晉南朝時期的佛儒道之爭[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06):86-89.
[14]樂勝奎.梁武帝的儒學思想論略[J].天津社會科學,2003(04):130-133.
[15]伍成泉.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對道教的影響[J].中華文化論壇,2007(02):101-106.
[參考文獻]
[1]夏增民. 儒學傳播與漢魏六朝文化變遷[D].復旦大學,2007.
[2]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399.
[3][美]杜維明著.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M]. 錢文忠、盛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150.
[4]郝虹.魏晉儒學盛衰之辨——以王肅之學為討論的中心[J].中國史研究,2011(03):45-59.
[5]《三國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魏略》.
[6]周培佩.<隋書·經籍志>與魏晉南北朝學術[J].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23(02):65-67.
[7]孫寶.東晉儒學文化型態與士風[J].理論月刊,2008(07):44-47.
[8]武劍青.從“春秋決獄”到“納禮入律”——淺析儒家思想融入魏晉北朝諸律的必然性[J].柳州師專學報,2005(02):127-129.
[9]孫寶.儒家政教觀與魏晉賦格建構[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8(05):1-6.
[10]吳艷.21世紀以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研究述論[J].唐都學刊,2017,33(06):92-98.
[11]薛勝元.儒學分裂與玄學產生——論漢魏社會思潮的變化[J].文史博覽(理論),2012(06):39-41.
[12]巴曉津.玄學代表人物的儒家素養與魏晉儒學之傳承[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2):32-36.
[13]李承貴.儒佛道三教關系探微——以兩晉南北朝為例[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04):12-18.
[14]湯其領.試論東晉南朝時期的佛儒道之爭[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06):86-89.
[15]樂勝奎.梁武帝的儒學思想論略[J].天津社會科學,2003(04):130-133.
[16]伍成泉.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對道教的影響[J].中華文化論壇,2007(02):101-106.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