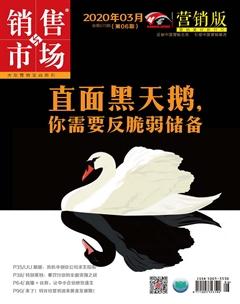潛在紅利如何吃下?
陳敘杰

近期,明星火鍋、高端日料、品質正餐、城市老字號等高品質、高客單品牌幾乎一窩蜂地出現在外賣平臺上。這似乎是一場“極不公平”的降維打擊,這對一些純外賣品牌,包括一些早前一直處于中下等、靠低價和補貼獲取訂單的做外賣的“弱”門店來說,他們的日子愈發難過了。對于這些剛入外賣戰場的“新”品牌來說,如何做好外賣?如何在疫情結束后更客觀地權衡外賣與堂食之間的關系?如何讓兩者搭配且相得益彰?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
餐飲業多輪淘汰潮拉開序幕
所謂危機,指的是以危為先、以機為后的綜合環境發展轉折點。對于能力不足且不自知更無力求存的群體,基本就只有危而沒有機,而對于積極求變的群體,危機也即造化。
一場危機,通常多以淘汰作為序幕。2019年12月,一些餐飲人盤點和總結后發現自己在行業內毫無建樹,在資產和財產端也一無所得,這些人認清事實后毅然離開了餐飲業,這是行業正常的新陳代謝。即使該時間線與疫情起源重合,但兩者毫無關系,淘汰他們的不是疫情,而是老板們自己的所為。
成都有一個名為“爛李子”的甜品品牌,老板用私人微信接單并親自開車在全成都送貨,這樣的案例在當下并不少見。從線上看,單單一個產品展示頁也有頗多差異化,會來事兒的老板寫安心卡、上傳消毒照片、公布員工健康證,甚至有的還在朋友圈實時更新消毒視頻和開直播等。
但也有大量的老板“不動如山”,之前外賣怎么做,現在依然怎么做,哪怕平臺降傭,他們也毫無動靜,有些甚至連外賣安心卡都沒心思做。一旦常規方式導致外賣接不到單,或者安全措施不到位導致一單安全事件,親自操作后也無力破局,被現實打擊后,這些門店在開工后也得撤出行業,這是疫情之下的又一次淘汰潮。
按這個趨勢再往后衍生,隨著一些老板資金流衰竭或從業信心的持續下滑,下一輪淘汰潮也會如期來臨。不可否認的是,多次洗牌過后,餐飲業的整體素質會被拔到極高的水平。
倒逼餐飲品牌,重構商業模式與贏利方式
從多輪淘汰潮的基本路徑可以看出,疫情最基本的福利是對行業優勝劣汰式的洗禮,待疫情結束,之前被淘汰掉的區位重新被填滿需要一定的時間,更需要潛在從業者有重建的勇氣,此時更多的人會將目光投向疫情磨煉之后依舊留存下來的品牌。
對于這些品牌,顧客更信任、行業更依賴,在疫情后的重建階段,這些明星品牌會進入客流的高峰、口碑的高峰、品牌擴展的高峰,甚至是加盟商擁入的高峰等。我們將之稱為“底層紅利”,這幾乎與非典后期餐飲業的反彈式紅利如出一轍。
從當下可以看出,新冠疫情切斷了餐飲業以堂食為先的經營思路,更嚴重的是,大競爭和弱需求之下,外賣也有所受阻。對于餐飲人來說,最艱難的不是沒有了現金流,而是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在堂食和外賣平臺之外找到新的餐飲贏利方式。但往往,問題和危機的背后,也可能是一場潛在的造化。
從當下回頭看,品牌化、連鎖化是非典給餐飲業留下的發展紅利,而如果我們從未來回頭看,在堂食和外賣之外,找到餐飲業經營餐飲產品之外的新路徑,將是新冠疫情給餐飲業留下的潛在紅利。
換句話說,當新冠疫情過去,餐飲業的贏利方式和商業模式將會迎來新一輪革命性的變化,行業將會從堂食和外賣的雙增長形式走向多渠道和多維增長的新局面。
餐飲業將迎來結構性升級與紅利
且先來對比傳統餐飲和新餐飲的差異化。傳統餐飲就是給顧客提供一個飲食場景,主客關系在顧客用完餐之后立即完結。新餐飲的關鍵詞是IP化溝通,簡單說傳統餐飲時代是人找餐廳,而新餐飲前期是餐廳找人。要實現這一點,餐廳需要有品牌建設,形成獨特的記憶性IP,以顧客攔截的形式做主客溝通。再之后,線上化成了新餐飲的一個顯著標簽,究其根本,所謂新餐飲不過是單純的信息交流而已,目的是通過信息交流實現顧客到店消費,或者顧客點外賣的時候能主動搜索品牌方。
當下,疫情幾乎切斷了九成以上的堂食入口,導致從業者們集中擁入外賣平臺,激烈競爭之下,似乎外賣也不是一條好的出路了。
生物學告訴我們,幾乎所有的環境變化都必然倒逼生物本身生存結構的被動性變化。
1.新餐飲后期的三大結構性變化
新餐飲是前些年的概念了,我們將之分為兩個階段,如果早前屬于新餐飲時代的前期,那么當下就屬于新餐飲時代的后期。
我們觀察到,在疫情之下,餐飲業出現了三個結構性的變化。
第一,從簡單的信息交流進入以下單為核心的產品交流。
所謂的信息交流,指的是告訴顧客一個信息,然后將信息作為引子,將顧客導流到線下消費。以開業為例,餐廳開業前后一般會在各大公眾號做推廣,然后以發放優惠券和紅包的方式吸引消費。
但疫情切斷了堂食的后路,整個行業的消費邏輯就從提供信息升級到信息即訂單的新格局,其更強調了零售產品的可能,如半成品、生鮮、料理包、特殊調料、衍生品等。
信息即訂單帶來了兩個升級:一是行業大規模從單一餐品升級到零售產品的疊加;二是行業的獲客路徑從單一的外賣平臺升級到多維并存,如當下我們從公眾號、小程序、朋友圈等渠道都能看到餐飲品牌的銷售入口,有了零售產品的補充,幾乎每一個溝通頁面都支持用戶即時下單。
第二,從產品競爭升級到訂單競爭。
如果大家都在推產品,行業勢必進入更為激烈的產品訂單競爭,從產品競爭到產品訂單競爭有一個本質化的區別。產品競爭看的是價格之外的價值溢出,而產品訂單競爭除了看價值溢出外,用戶更關注訂單信任。
比如,某餐廳的后廚是封閉的,顧客雖然覺得菜品不錯,但也可能有一些簡單的質疑,對封閉后廚來說,衛生質疑便是其一;兩家餐廳的產品競爭,假設價格相差無幾,一家常規經營,另一家做了產品安心卡,顧客會怎么選?答案是必然的。
在產品信任、訂單信任方面,全明檔廚房、后廚操作直播、后臺實時上傳清潔內容的記錄、公示等也是有力證明,這些行為在新冠疫情當下確實讓品牌方收獲頗豐(訂單量、公信力等)。
第三,主客關系升級,從單一的溝通進入多維的交流。
溝通和交流都是主客關系中通過信息來傳導的遞進場景。
從餐飲業來看,早期的溝通極為簡單粗暴。同樣以開業為例,常規操作是放個鞭炮或者放一些花籃來代表門店的開業宣言,老板頂多在網上送一些優惠券或者上線點評而已。
我們將這種撒網式傳播信息的行為稱為單一或者單向的溝通,其不過就是提供一個場景信息,或者以優惠券的形式實現引流而已。
在深受疫情影響的當下,我們看到多數餐廳的員工開始有了發朋友圈賣餐廳產品的行為了,比如發團餐訂單、零售產品等,員工既是操作員又是客服,更是銷售員。這種主客雙方(顧客與餐廳,包括餐廳與員工等)有信息回流的行為,我們稱之為交流。
再來看一個轉變,幾個月前,某顧客點了一份香菇雞,在備注上寫明“點了2元一份的鹵蛋,給我換成2塊錢的香菇”。商家給顧客配了鹵蛋并道歉,“我們的香菇雞是標準化的,無法給你加香菇。”過去是加錢也不給香菇,而現在則有了明顯性的變化,顧客備注了同樣的內容,商家不僅配送了鹵蛋,還給顧客加了香菇,回復顧客:“難得你確實愛吃香菇,只要是你點,都給你免費加。”
為什么有如此明顯的轉變?一是當下的訂單來之不易,二是比起用優惠券去拉新,老顧客的復購和關系遞進更為值錢。所以就很清晰了,所謂的交流就是清晰顧客意見,并以此為“砝碼”來形成一定的訂單增量。
2.紅利稍縱即逝,品牌方需主動表述
上文提及的是疫情危機給餐飲業帶來的三大結構性升級,且可能成為未來餐飲業落地的經營標配。但問題是:疫情期依舊留守行業、用成本開路來試出新玩法的品牌們難道就沒有專屬紅利嗎?
先回到2003年非典時期的中后期,當時的餐飲業還處于緩慢恢復狀態,多數潛在入局者依然在觀望,而這個時候,肯德基在逆境下連開兩店,且大獲全勝。
為什么?原來肯德基是非典期間為數不多的安心餐飲之一,加上肯德基捐錢、捐餐券等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都為品牌本身帶來極為豐厚的回報,做到這些前提是信息的公開化。
通過疫情,我們看到了眉州東坡、老鄉雞、西貝等出來發聲的品牌,他們將自己的想法、正在做的事兒以及將要做的事兒全部通過媒體公之于眾。通過媒體信息的分發,我們才看到了這些有血有肉的品牌,也包括疫情下留守品牌們的優秀作為,如開直播、清潔消毒等內容的透明化等。
通過疫情積極改造品牌、賦能行業,不僅讓顧客看到了這些留守品牌的魄力與智慧,更代表了市場公信力與品牌責任等,這是其他后來者永遠無法對比的。
可見在疫情中后期,這些品牌將會成為顧客消費的首選,更會成為加盟商的第一選擇,甚至還有無法比擬的品牌高度與市場親和度,這便是疫情給留守品牌們帶來的專屬紅利。
結語
不得不說,對于一些資金流充足的品牌來說,疫情前期可以算是一次“閉門造車”的大好時機。
前期顧客對餐飲業稍顯保守,這也必然推動餐飲老板們創新行為迭出,但創新也意味著成本的浪費與前路探索的不定。
一些聰明的老板在疫情前期停工,然后開始員工培訓、內部組織架構優化、工作流程重構等。在疫情中后期時,待一些前沿品牌試錯完畢,有了更好的套路后,這時候直接引進并開工也不失為較聰明的應對方式。
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疫情對餐飲業的優化與升級,整個行業的入局門檻將會再度被拔高,單單會做菜已經不適合開餐廳了。這對于潛在從業者們是“壞消息”,但對行業整體格局來說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