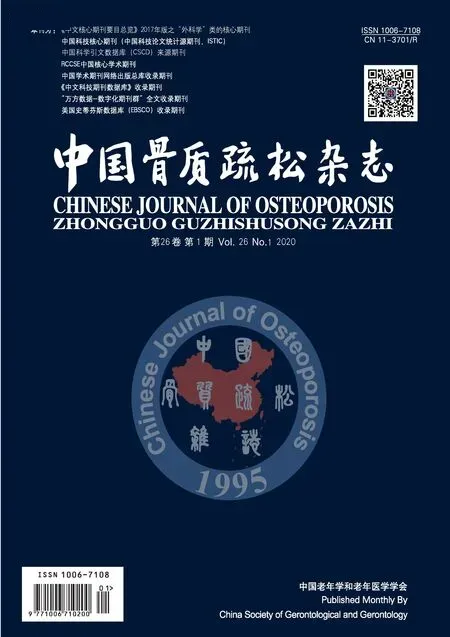基于數據挖掘中老年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的中醫證候研究
笪巍偉 唐德志 金鎮雄 趙永見 舒冰 李曉鋒 王晶 王騰騰王擁軍 施杞 馬勇 郭楊
1.揚州市中醫院骨傷科,江蘇 揚州 225000 2.上海中醫藥大學脊柱病研究所,上海 200032 3.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上海 200032 4.筋骨理論與治法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032 5.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
骨質疏松性骨折(osteoporotic fracture)繼發于骨質疏松,因骨質脆性增加而易發生全身多部位的骨折。人體的骨量隨增齡而丟失,骨微結構退變,造成骨骼強度降低,輕微外力即可誘發骨折,脊柱、髖部及橈(尺)骨遠端為好發部位[1]。
亞洲人口老齡化的趨勢迅速增長,過去的30年中,在中國發生脊柱骨折的患者占50歲以上人口的15%,而其他多數國家的髖部骨折率增加了2~3倍,到2050年保守估計約超過50%的中老年人群將發生骨質疏松性骨折[2]。由于骨量低下可導致骨折愈合時間延遲,斷端骨痂形成質量及力學性能不足,再發骨折的風險明顯升高;同時,骨折內固定物把持力不足、穩固性差、失敗或松動的風險增加[3]。另外,骨質疏松性骨折可顯著增加致殘、致死率和昂貴的醫療保健費用,因此,成為全世界中老年人群的主要健康負擔[4]。
祖國醫學則將骨質疏松性骨折歸屬于“骨痿骨折”的范疇,認為其發病內因是由于腎、肝、脾虧虛,致筋骨、肌肉失養;外因是跌仆損傷或發力失當、屏氣閃挫,造成骨斷筋傷,氣血經脈失暢,瘀血阻滯不通而痛[5]。目前國內有關骨質疏松性骨折的證候診斷及分型標準尚未得到重視和統一,相關研究缺乏。因此,本研究通過對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中醫證候的問卷調查,分析臟腑、氣血、陰陽與骨質疏松性骨折之間的相關規律性,從而為臨床防治骨質疏松性骨折提供一定的中醫藥理論認識。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通過跟骨骨密度儀檢測,篩選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收治于上海龍華醫院骨傷科病房的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80例,其中男24例,年齡52~87歲,體質量35~95 kg;女56例,年齡52~85歲,體質量30~77 kg,絕經年數1~38年。所有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后填寫中醫證候問卷調查量表。
1.2 納入標準
(1)輕微外力(跌倒外傷)所致的新鮮脆性骨折,如脊柱骨折、髖部骨折、腕部骨折、肱骨骨折、膝部骨折、踝部骨折等;(2)年齡≥50歲,性別不限;(3)伴骨質疏松癥,跟骨骨密度檢測T值<-1.0 SD;(4)X線片已有骨質疏松改變者[6-7]。同時滿足條件(1)、(2),或滿足條件(1)、(2)、(3),或條件(1)、(2)、(4)。
1.3 排除標準
(1)年齡<50歲,非輕微暴力損傷所致(如車禍撞擊傷等);(2)開放性、陳舊性及病理性骨折;(3)有嚴重的痛風、類風濕性關節炎及腫瘤等病史;(4)精神和認知功能障礙;(5)拒絕合作者。
1.4 中醫證型的劃分
查閱國內有關骨質疏松癥中醫證候文獻,綜合謝雁鳴團隊[8]的流行病學調查、黃宏興團隊[9]的聚類分析以及國內學者對絕經后婦女骨質疏松癥證候的研究[10-11]。本研究選取其中較為共識的證候作為觀察指標,將骨質疏松性骨折的中醫證候分為脾腎陽虛、肝腎陰虛、氣滯血瘀、其他證候4類。
1.5 調查量表
本研究依托上海中醫藥大學脊柱病研究所主持的“上海市衛生系統重要疾病聯合攻關項目”,并通過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醫學倫理批號:2014 LCSY12號)。問卷量表中加入脾腎陽虛證型的常見癥狀,依據《中醫臨床診療術語癥候部分》主要包括畏冷肢涼、面色晄白、腰酸、久泄久痢、或完谷不化、舌淡胖、苔白滑、脈沉遲無力等。中醫辨證由一名副高以上職稱醫師完成。
1.6 骨密度測定方法
所用儀器為上海中醫藥大學脊柱病研究所購置的跟骨Hologic超聲骨密度儀,按Hologic公司提供的操作說明進行測量,由電腦軟件自動得出T值,保存及記錄。
1.7 統計學分析
所有問卷調查數據由雙人錄入電腦Excle存檔,數據采用SPSS 18.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SPSS Clementine 12.0軟件進行數據挖掘。
2 結果
2.1 中老年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中醫證候分析
2.1.1骨折分布:髕骨骨折、踝關節骨折、脛骨骨折各1例,跟骨骨折2例,腕部骨折4例,肱骨骨折10例,脊柱骨折25例,髖部骨折36例。
2.1.2中老年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中醫證候分布情況:80例中老年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中,脾腎陽虛型37例(46.25%),男11例,女26例;肝腎陰虛型13例(16.25%),男4例,女9例;氣滯血瘀型14例(17.50%),男7例,女7例;其他證型16例(20.00%),男2例,女14例。其中,男性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中,脾腎陽虛型占45.83%,肝腎陰虛型占16.67%,氣滯血瘀型占29.17%,其他證型占8.33%;女性患者中,脾腎陽虛占型46.43%,肝腎陰虛型占16.07%,氣滯血瘀型占12.50%,其他證型占25.00%。
2.1.3根據年齡、體質量、4種中醫證候的分布情況: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中脾腎陽虛型主要分布在70~85歲、40~60 kg的患者中,肝腎陰虛型主要分布于75~85歲、40~70 kg的患者中;氣滯血瘀型分布相對集中于65~75歲、50~80 kg的患者中,見圖1。

圖1 體質量、年齡與中醫證候的分布關系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weight, age, and TCM syndrome

圖4 性別、骨折部位與中醫證候的關聯度Fig.4 The relevance between gender, fracture site, and TCM syndrome
2.1.4既往骨折患者中醫證候的分布情況:60歲以上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中,脾腎陽虛型既往骨折1~3次相對較多,見圖2。同時,絕經后10~30年的女性患者中,脾腎陽虛型既往骨折1~3次(3A),其中與既往發生1次骨折呈強鏈接(粗實線),10~20年、20~30年兩個階段與既往發生2次骨折呈中等鏈接(細實線),而20~30年與既往發生3次骨折呈中等鏈接(細實線)(3B),說明脾腎陽虛型患者隨著年齡及絕經年數的增加,至少出現2次及以上次數骨折,見圖3。

圖2 既往發生骨折患者的中醫證候分布情況Fig.2 Distribution of TCM syndromes in patients with previous fractures

圖3 脾腎陽虛型絕經后女性患者既往骨折情況Fig.3 Previous fractures of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spleen and kidney yang deficiency
2.1.5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中醫證候的分布情況:從不同證候患者與骨質疏松性骨折部位關聯情況(4A)看出,脾腎陽虛型女性患者與髖部、脊柱骨折呈中等鏈接(細實線),其次是脾腎陽虛型男性與髖部骨折呈弱鏈接(細虛線)(4B),說明脾腎陽虛型患者多易發生髖部和脊柱骨折,見圖4。
3 討論
現代醫學將骨質疏松性骨折的危險因素劃分為性別、年齡、民族、家族史、既往骨折史等不可控因素;以及體質量指數、生活方式、性激素水平及服用藥物等可控因素[1]。目前基于以上危險因素所建立的骨質疏松性骨折風險評估工具存在中、西醫學認知思維的差異。那么針對我國中老年人群的評估,是否可以結合中醫證候學方面的相關研究內容,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預測的個體化和準確性。
中老年人骨質疏松性骨折作為骨質疏松癥的嚴重并發癥,其發生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骨質疏松癥證候類型的影響[12]。因此,骨質疏松性骨折的中醫證候多與骨質疏松癥相似,常歸屬于“骨痿”“骨痹”等范疇[13]。國內學者指出骨質疏松性骨折的證候要素靶位主要包括腎、肝、脾[14],其實證以血瘀、氣滯為本病的主要病性證素,氣血是濡養筋骨、通利關節的重要物質基礎,當氣血瘀滯時則筋骨、關節失養而存在骨質疏松性骨折的風險,故氣滯血瘀乃骨質疏松性骨折發生的重要促進因素[15];虛證則常以陰、陽、氣的虧虛為主要病性證素,三者中以陰虛為最重要的病機改變[5]。臨床上通常將骨折分為三期辨證論治,早期治法為活血通瘀、行氣止痛;中期治法為活血化瘀、通腹下氣;后期治法則以滋補肝腎、強筋健骨[16]。
3.1 腎主骨
腎為“先天之本”“主藏精,精生髓,髓養骨”,腎的功能平衡及腎精的盛衰將影響骨的生長、發育和強盛、衰弱的全過程。類似于現代研究發現,腎臟能夠將維生素D最終轉化為高活性的1,25(OH)2D,并經1,25(OH)2D促進腸道鈣和磷的吸收和腎小管內鈣的重吸收,還通過直接調節骨骼代謝,以維持血液循環中的鈣磷穩態[17]。
3.2 脾主肌肉
脾胃為“后天之本”“為氣血生化之源”,可濡養先天之精,腎精充盈則骨有所養。《靈樞·決氣》曰:“谷入氣滿,淖澤注于骨。”脾胃虛弱,則生化乏源,氣血虧虛,骨髓失養;另外,“脾在體合肌肉、主四肢”,脾胃虛弱,化源不足,導致肌肉消瘦,四肢痿廢,則骨失所用,進而導致廢用性骨質疏松。老年人在寒冷季節易跌倒而發生骨折,可能與低溫造成神經肌肉功能的損傷密切相關;同時,在冬季陽光光照時間縮短,導致維生素D的合成減少,從而對骨密度產生不利影響[18]。可見,老年人發生骨質疏松性骨折的根本原因不僅包括骨量的下降,還涉及肌肉功能的衰退。
脾氣健運可能通過調節線粒體的氧化、肌酸磷酸激酶的代謝、肌糖原的酵解及蛋白質、糖等能量物質的貯存功能,從而保證骨骼肌的正常活動所需[19]。同時,在腎臟及骨骼肌中表達的CYP27B1基因作用下,可轉化、合成具有活性的1,25(OH)2D,進而上調骨骼肌中的維生素D受體,抑制成肌細胞的增殖,促進其分化,從而調節骨骼肌損傷的修復和再生[20]。腎與脾通過體內代謝的相互作用,共同影響、調節骨骼及肌肉的微環境,因此,在預防中老年人骨質疏松性骨折的發生,需重視脾腎的相關性,提高骨骼的強度、肌肉的協調性。
3.3 肝主筋
肝藏血、腎藏精,肝腎同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中精氣的充盛有賴于血液的滋養,肝血不足可引起腎精虧損,進而致骨髓失養[21]。《臨證指南醫案·痿·鄒滋九按》曰:“夫痿證之旨…蓋肝主筋,肝傷則四肢不為人用,而筋骨拘攣”。說明肝主筋、肝藏血的功能關系筋骨生理功能的正常與否。研究表明,進入血液的維生素D3首先在肝臟中酶的催化作用下形成25羥維生素[25(OH)D],才能進一步被腎臟利用、轉化為高活性的1,25(OH)2D[22]。血漿中的維生素D主要以25(OH)D的形式存在,并以此儲存于肝臟中,可見肝腎共同調節機體鈣磷代謝及骨骼鈣化的功能。
3.4 血主濡養
《靈樞·本臟》曰:“是故血和…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氣血充盛,則筋強骨健;氣血運行障礙,瘀血阻絡,則不利于細胞間物質交換[23],影響骨的營養及骨代謝[24]。中醫學認為,血瘀不僅是骨質疏松性骨折的標,還是其本。《景岳全書》云:“跌撲傷而腰痛者,此傷在筋骨而血脈凝滯也。”年老患者,因氣滯血瘀致脈道不暢,不通則痛;瘀血不去,新血不生,則骨失所養[5]。瘀是老年者的常態,又是其生理特點及貫穿疾病不同階段的病理因素,分為已瘀、欲瘀和未瘀3種程度[25],可表現為主證、或兼證,故治療老年疾患時因兼顧靈活運用“活血”法。
綜上所述,骨質疏松癥及骨質疏松性骨折總屬本虛標實,以肝、脾、腎及氣血虧虛為本;氣滯、血瘀、痰濕為標[11,26]。脾腎陽虛、瘀血阻絡證不僅是老年性骨質疏松癥患者骨密度最低的證型,同時還是總骨折、多次骨折及髖部骨折發生率最高的證型[27]。其中,脾腎陽虛證型是中老年骨質疏松癥患者的重要證型,同時,脾腎陽虛型中老年女性患者更易發生髖部和脊柱骨折,尤其是絕經后年數較長者易發生多次骨折,故在臨床防治中老年骨質疏松癥和骨質疏松性骨折時,應重視“脾腎相關”“先、后之本”理論的運用和指導,還需關注“血瘀”在疾病過程中的影響,“活血”法的合理運用能夠進一步提高臨床療效。由于本研究調查的樣本量小,結果還需要以后收集更大的樣本量來進一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