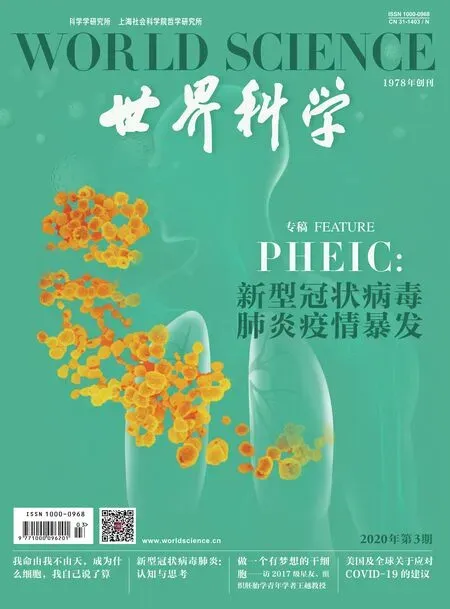“零號病人”的誘人謊言
編譯 喬琦
在傳染病詞典中,“零號病人”這個術語代表傳染病暴發的起始病例,也就是第一個表現出疾病感染癥狀的人。傳染病可以追溯到單個個體的想法、對這個人不計代價的搜尋以及對疾病傳播路徑的描繪,已經成了流行文化中反復出現的主題。像《傳染病》(Contagion,2011),《十二猴子》(12 Monkeys,1995)和《28天后》(28 Days Later,2002)這樣的電影都描繪了由一人引發的傳染病帶來的可怕后果,而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初始病毒攜帶者傷寒瑪麗(Typhoid Mary)早已成了疾病傳播者(有時甚至是故意傳播)的同義詞。
在美國艾滋病歷史中,零號病人是一位名叫蓋爾坦·杜加(Ga?tan Dugas)的加拿大空乘的綽號。人們認為,杜加在海地或歐洲感染上了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也即艾滋病病毒),把這種病毒帶到了北美并傳染了數百名性伴侶。然而,杜撰出“零號病人”一詞并認定杜加為艾滋病初始病例并非醫學界,而是美國記者蘭迪·希爾茨(Randy Shilts)。他的作品《世紀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1987)記錄了艾滋病暴發之初的情況,內容穿插描述了紐約和舊金山同性戀群體中艾滋病的傳播情況,還控訴了里根政府對艾滋病及其帶來的痛苦漠不關心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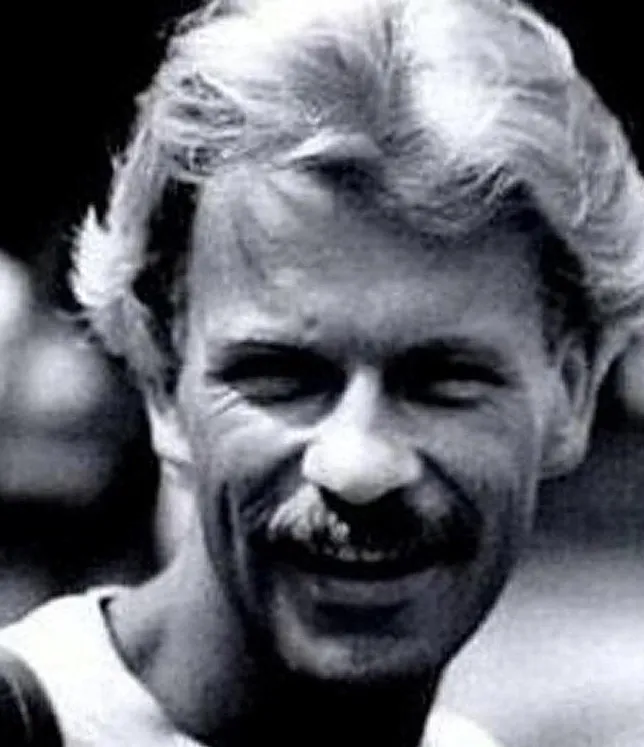
在美國艾滋病歷史中,綽號“零號病人”——蓋爾坦·杜加
在醫學文獻中,零號病人的標識是“Patient O”——是字母“O”(outside),而不是數字“0”——表示這個病例的地理位置在加利福尼亞之外,而對艾滋病的研究正是發源于加州。然而,希爾茨在書中改稱杜加為“零號病人”,并把他描繪成了一個應該受到所有人唾棄的人物:在希爾茨筆下,杜加隨意甚至惡意地同伴侶發生性關系,全然不顧他們的健康,即使在醫生勸阻后也毫不收斂。希爾茨稱杜加為“魁北克版傷寒瑪麗”,并把他描述為一個“說話帶著法國口音的帥氣金發”男子,會“在和你發生性關系后,打開房間里的燈,指著他的卡波齊氏肉瘤說:‘我得了同性戀癌,馬上就要死了,你也是一樣’。”
自此之后的幾十年里,杜加就一直以艾滋病“零號病人”的身份為人們所熟知。然而,最近在《自然》(Nature)雜志上發表了相關文章的作者們卻發現,實際上,艾滋病病毒早在杜加出現之前就進入了美國。這些研究人員運用新遺傳分析方法研究了保存下來的血液樣本,結果發現,艾滋病病毒很有可能是在1971年以受污染血制品(如血漿)這樣的形式從加勒比海地區抵達美國的。因此,杜加,這個被指責為開啟美國艾滋病疫情的罪魁禍首,并不是疾病的源頭,只是這種迄今已造成全球3 500多萬人死亡的疾病的又一個受害者。
既然零號病人杜加的故事完全沒有科學依據,純粹只是一名記者為追求文學素材而虛構出來的產物,那么,為什么這個故事經久不衰?是什么讓初始病例這種想法如此誘人?為何我們需要這些故事來理解超出我們認知范圍的事物?我們對這些故事的癡迷又反映了什么問題?
即便是在杜加之前,有關疫情暴發的故事中也充斥著零號病人。1900年,公共衛生官員在舊金山環球酒店的地下室內發現了一位名叫黃初景的41歲中國男子的尸體。他們懷疑黃初景的死因是黑死病(淋巴結鼠疫),便立刻下令隔離當地唐人街。一天之內,所有白人都在政府的指導下從該街區撤出,衛生部下令挨家挨戶蒸熏消毒,并給所有唐人街居民接種疫苗。在20世紀初的紐約,后來被稱為“傷寒瑪麗”的愛爾蘭移民瑪麗·馬龍(Mary Mallon)被強制隔離,原因是公共衛生官員一口咬定她在為那些毫無戒心的家庭做飯的時候故意傳播疾病。在上面這兩個例子中,政府以科學為名實行強制措施,這是利用了當時存在的普遍觀點:人的種族和階級會影響甚至決定他們對疾病的態度和反應。
零號病人的故事之所以如此誘人,是因為這樣一個人物方便了我們在傳染病暴發時推卸責任。零號病人是明確的疾病傳播的載體,讓人們注意到了人際接觸的潛在危險,并且促使健康人群遠離感染者。當把零號病人定義為具有明顯行為、性取向或種族特征的人時,我們中沒有這些特征的人就可以寬慰自己沒有得病的風險。零號病人既沒有自控能力,也沒有主動避免把疾病傳染給他人的道德信念。他/她越是偏離既定社會規范,就越可能遭受譴責。正如學者普里西拉·沃爾德(Priscilla Wald)在《傳染病學》(Contagious,2008)一書中寫的那樣,這種污名化既是“一種孤立感染者、防止疾病擴散的形式”,也是“一種識別病毒主體的手段——這在那些蓄意傳染者的謠言里,就演變成了惡意的傳播”。據報道,杜加的性伴侶數量常年保持在250個左右——他的這種“出格”性行為和明知自己HIV陽性卻不加克制的做法都成了公眾眼里他應當承擔更多責任和譴責他不道德的有力論據。
無論是過去的疫情,還是現在的傳染病,零號病人這個形象引發的共鳴,凸顯了我們希望將新信息嵌入舊體系的集體愿望。零號病人故事中對疫情的描述讓我們感到熟悉、感到寬慰。我們需要讓這些看似無序的疫情恢復秩序,零號病人的故事正是利用了我們的這種心理。這個故事將個體或群體的行為劃分成非自然、異常、易于滋生疾病三類。舉個例子,2004年H5N1暴發時公眾的言論就是如此——H5N1是當年發源于亞洲部分地區的一種致命禽流感病毒,人類與感染病毒后的禽類(無論是死是活)密切接觸后,就很有可能感染H5N1。再想想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埃博拉起源于西非的一個村莊,由于森林砍伐過度,感染了病毒的野生動物接觸人類的概率大大增加。這些現實中的疫情,以及電影《極度恐慌》(Outbreak,1995)和《傳染病》(Contagion)中描繪的那些,都把疾病起源地定在了西方語境下這個世界中的“原始”“前現代”部分——通常是非洲或亞洲(非洲人或亞洲人),從來與西方無關。傳統生活方式與現代性外表間的碰撞,尤其是資本的國際流動以及承載這種流動的飛行旅行,大大突出了新與舊并存給人們帶來的不安,并切切實實地威脅著全球人類的健康。
人們在疫情暴發時對零號病人故事的熱衷并不只是一種推卸罪責的方式,它還勾勒出了對公共衛生造成嚴重現實后果的傳染病引發的社會反應和政治反應。杜加成了HIV的化身,這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影響疾病傳播和公民衛生健康的結構性因素(比如貧困和醫療保障制度)轉移到了對個體行為的分析之上。20世紀80年代,流行病學理論對男同性戀的關注掩蓋了女性HIV攜帶者人數上升的事實。此外,等到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明確感染艾滋病的高風險人群時——同性戀者(homosexuals)、血友病患者(haemophiliacs)、海地人(Haitians)以及癮君子(heroin users),也就是大家熟知的4-H俱樂部——幾乎沒有人討論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那么多海地人感染艾滋病死亡。最近這些年起源于發展中國家的傳染病——例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凸顯了全球衛生狀況和疫情暴發影響的差異。任何旨在盡可能降低未來疫情暴發影響的項目都必須設法解決全球貧困問題和貧富差距問題,而不只是簡單地思考那些保護工業化國家免受第三世界威脅的新方法。
杜加并非北美HIV源頭的聲明不太可能改變我們如今對艾滋病這種已經肆虐了30多年的傳染病的看法。不過,這確實提供了一個挑戰“零號病人”思維定勢的機遇,并且也有助于我們反思零號病人影響我們面對傳染病時的反應方式。這類有關疫情暴發的故事是一種有能力影響政治決策并進而影響公眾健康的工具。杜加恢復“清白”一事應當敲響警鐘,警示我們不要再過度迷信零號病人的故事。所有這些傳染病的源頭都是它周圍的結構性因素。把罪責全部推到零號病人身上只能讓我們忽視更重大的任務:解決影響全世界人民健康的不平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