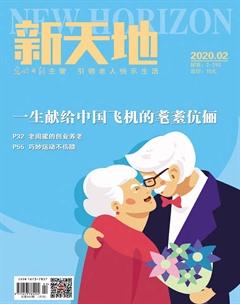白淑湘:舞者傳奇
余瑋

眼前這位步履雅致、裝束淡雅、談吐優雅、舉止高雅的長者,就是當年《紅色娘子軍》的主演白淑湘。熱愛她的觀眾曾記下了她那雅麗、抒情、渾身上下都能“說話”的舞姿。三代領導人都曾觀看過她的演出,對她鼓勵有加。作為第一代吳瓊花的芭蕾舞劇扮演者,白淑湘自稱是“開拓、奠基、鋪路”的一代。
簡單的寒暄過之后,她談起了自己終身的熱愛:“舞蹈藝術是個美的藝術,大家都愛看芭蕾舞,就是覺得它非常美,但是它背后很辛苦,要付出很多……”
白天鵝變身“吳瓊花”
早年,白淑湘是東北人民藝術劇院兒童劇團的小主角。13歲那年,還榮幸地參加了賀龍率領的第三屆赴朝慰問團。次年底,新中國的第一個專業舞蹈家的搖籃——北京舞蹈學校誕生,白淑湘招收到這個中國舞蹈界的第一所學府,從此與芭蕾舞結緣,并是世界古典芭蕾舞劇《天鵝湖》中國版的首位主演。于是,她有了中國芭蕾舞壇“起飛”的第一只“白天鵝”一說。
1963年秋,周恩來總理觀看了北京舞蹈學校實驗芭蕾舞團演出的芭蕾舞劇《巴黎圣母院》。隨后,周恩來對著名舞蹈編導蔣祖慧建議,中國芭蕾界可以邊學習西方古典芭蕾,邊創作中國革命題材的芭蕾舞劇:“從1954年北京舞蹈學校建校開始,你們搞芭蕾差不多10年時間了吧,已經演了好多歐洲的古典劇目,都是排別人的節目。你們能不能自己搞些創作呢?可以搞點革命化、大眾化的作品,不宜老是跳王子、仙女。”
這年12月,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召集舞蹈界知名人士座談,討論編演芭蕾舞現代戲問題。芭蕾舞團團長李承祥在會上建議改編當時已經深入人心的電影《紅色娘子軍》,并獲得通過。《紅色娘子軍》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排練完畢。
要“破天荒”將西方芭蕾技巧與中國革命歷史背景相互融合,并非易事。“我們借鑒了中國戲劇和武術的程式,加強了對抗性動作。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紅色娘子軍》在北京天橋劇場首演。周恩來觀看演出后走上臺,對芭蕾舞《紅色娘子軍》給予了肯定:“我的思想比你們保守啦。我原來想芭蕾舞要表現中國的現代生活恐怕有困難,需要過渡一下,先演個外國革命題材的劇目。沒想到你們的演出這樣成功!”
人生舞臺上的“紅”與“黑”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上演前,一個突如其來的罪名被強加到白淑湘的頭上,被當作“白專”批評。
一次偶然的時機,周恩來提到了白淑湘,這給在干校改造的她帶來了一線曙光。經過一番周折,白淑湘于1974年終于回到了芭蕾舞團。
白淑湘已經34歲。身體除了落下多種疾病外,肌肉已變得僵硬,體重大大超重。怎么辦?難道就此告別日思夢想重返的舞臺嗎?不!白淑湘拿出自己的韌勁,練長跑,泡游泳池,節制飲食;上午練,下午練,晚上還練。“記得那天我握著練功桿的時候,悲喜交加地哭了,似乎積攢近10年的眼淚在一剎那都涌了出來。”
經過短短兩個多月的拼搏苦練,奇跡竟又一次出現了:隨著體重由129斤急劇降到106斤,她的基本功也迅速恢復。但直到1978年,她才真正得到完全施展才華的機會,可此時一個芭蕾舞演員的黃金年代早已結束。
復出后不久,白淑湘等去美國演了將近兩個多月的《紅色娘子軍》,產生了轟動效應,并引起國外同行研究和探索中國現代芭蕾藝術的興趣。美國著名舞蹈藝術家瑪沙格雷姆觀看演出后非常驚訝,認為“中國的芭蕾舞很有張力,紅色經典現象值得深思”。
回歸芭蕾舞的白淑湘如魚得水,又主演了《沂蒙頌》《草原兒女》《杜鵑山》等。
有一種精神叫“紅色娘子軍”
今天,“紅色娘子軍”這一流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色經典再度升溫,證明了紅色文化經典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和生命力,也彰顯了紅色精神的力量。在作為國家最高芭蕾舞藝術演出院團的中國芭蕾舞團,《紅色娘子軍》是一門必修課。從第一代“瓊花”到第六代“瓊花”,每一個人都要經歷“娘子軍”的洗禮,從一招一式到精神內涵。白淑湘高興地看到,吳瓊花的扮演者們仍在不斷改進、突破。
白淑湘強調,她們那一代是開拓、奠基、鋪路的一代。“舞臺是我的生命。可是,‘文革造成了一個斷檔,到1986年培養出馮英、張丹丹這批新人出來才接上我,我充當的是一個鋪路石的角色。”
“好些報道說我50歲那年離開了舞臺,其實我一直演到了65歲才正式離開芭蕾舞舞臺,但直到現在我沒有退休。”這么多年來,白淑湘對中國芭蕾舞事業的熱愛與牽掛之情從未改變,并對中國芭蕾藝術的創新有著敏銳而深邃的思考。
如今的芭蕾舞臺上雖然不見了白淑湘深情的舞姿和靈巧的舞步,但這位“德藝雙馨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在擔任多項社會職務的過程中,在更廣闊的社會舞臺上,發揮自身的優勢,忙碌著、奉獻著。在白淑湘眼里,芭蕾是最美的、最富有魅力、最能讓人心曠神怡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