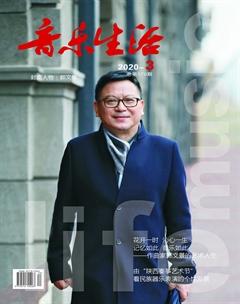關于疍家“水上民歌”名稱與概念問題
郭建民 趙世蘭

一、疍家“水上民歌”
疍家“水上民歌”亦稱“咸水歌”,她是流傳于嶺南一帶的一朵獨具地域特色的藝術奇葩,具有悠久的歷史。
從歷史成因看,由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朝代頻繁更迭,戰火連綿以及氣候變遷等原因,造成大批北方中原流亡家眷和難民越過長江,向嶺南一帶海域不斷遷移和漂流,“水上民歌”是疍家人創造的一種獨特的精神生活方式。福建、廣西和海南疍家“水上民歌”傳承了廣東稱之為“咸水歌”的種種優長,分別創立了屬于自己的鮮明風格,與廣東咸水歌相比,既異曲同工,又迥然相異。“水上民歌”是中國漢族民歌大家庭中的一員,是廣泛傳播于中國南海熱帶海域的“音樂珍品”。
從文化屬性看,“水上民歌”具有陸地和海洋雙重屬性;從族系屬性看,“水上民歌”雖然是漢族民歌的一員,但由于長期遷徙漂流,多個省份跨越,并與當地少數民族生活在同一片區域,形成了多元文化“血統”;從音樂和審美特征看,在傳承了廣東“咸水歌”吟誦調,口語化等特點的基礎上融入了少數民族民間音樂元素,從而創造了包括有獨唱、二重唱、多人表演唱的水上歌謠、敘事民歌、抒情短劇等多種表演樣式;從語言特征看,傳承了廣東粵語,逐漸同化并融入了海南瓊語、福建閩語、廣西壯語和當地方言,語言委婉、韻味十足、極富特色;從內容和形式看,藝術表現力豐富、感染力強。但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多地疍家“水上民歌”沿用廣東“咸水歌”的稱謂至今。
海上生活催生了疍家人開朗、豪爽、樂觀的性格特質,他們熱愛生活,熱愛海洋,熱愛和平,作為漢族族群,與黎苗壯等少數民族友好相處,關系和諧融洽,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了豐富多彩的
“咸水歌”。早年廣東習慣將疍民唱的歌稱之為“咸水歌”,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帶、沿海區域別稱疍歌、蜓歌、蠻歌、咸水嘆等,因為她有大海的滋味、大海的意蘊,故“咸水歌”一詞被大家認可并在廣東一帶廣泛流行開來,因為她是疍家人創造的民歌,所以又被廣泛地稱其為疍歌、蜓歌、蠻歌、咸水嘆、白話魚歌、后船歌等,后來許多學者專家冠名為水上民歌、船上小調、南海情歌、疍家歌謠、疍家調、吉普賽之歌等,叫法和稱謂多達幾十種之多。
“咸水歌”也好,“水上民歌”也罷,她經過了千百年的口耳傳承,成為地域特色鮮明的南海民歌,它是疍家人脫口而出的歌謠,也是疍家人生活中疏通和交流情感的橋梁,歌中蘊含著疍家人的文化審美以及為人處事的生活理念和哲學,可以毫無夸張地說,“咸水歌”同疍家人的生活生生相息,不可分割,她是疍家人出海起航和豐收歸來的“集結號”,傾注了疍家人難以割舍的精神寄托,更有學者形象地稱其為疍家人撫慰心靈和寄托精神的“海上圣經”。
二、海南疍家“水上民歌”名稱與概念繁雜多樣
關于海南疍家“水上民歌”名稱和具體概念,與“兩廣”和福建大致一樣,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有的是按照疍家人口頭習慣隨意而叫,有的則是研究者按照約定俗成的稱謂來稱呼,花樣百出、繁雜多樣,雖然疍家“水上民歌”同屬疍家人所創造,但卻出現了有多種叫法和不同解讀的混亂現象,令人費解和堪憂。比如廣東、福建、廣西等地大多都將其稱之為“咸水歌”、“疍歌”或“疍家歌謠”。許多關于疍家音樂文獻以及新媒體,如百度網、搜狐網等也都對此從不同的視角加以解讀,稱謂和叫法如此復雜多樣、眼花繚亂,致使疍家“水上民歌”概念混淆,產生對疍家“水上民歌”歷史文化與傳播研究產生諸多誤讀和曲解。歸納起來的名稱與概念有如下幾種:
第一種來自《音樂詞典》:“咸水歌”是民歌的一種。主要流傳于廣東中山、番禺、珠海、南海、廣州市等地,農民每逢中秋夜,大家搖船聚集到江心斗歌、聽歌,成為中秋“咸水歌”擂臺。“咸水歌”的曲調,一般都系隨字求腔,結尾處有固定的襯腔。由于演唱活動頻繁,內容不斷豐富,曲調也隨之不斷發展。歌詞為兩句一節,每句字數不均,每節詞同韻,各節可轉韻。曲式結構為上下句。每句的句首和句尾有基本固定的襯詞和襯腔,結尾時都用滑音下行。六聲徵調式,音調悠揚抒情。另有“大蹭歌”、“姑妹歌”亦屬于“咸水歌”,歌詞格式、曲式結構、調式等與“咸水歌”基本相同。但句首、句末的襯詞、襯腔不同。這里有一點需要說明,由于歷史原因,海南把疍家“水上民歌”稱之為廣東“咸水歌”已成習慣,從而造成解讀不夠全面和前后無法對應等諸多問題。1985年的海南諸島隸屬廣東管轄,1988年海南諸島從廣東省分離,創建為海南省。因此,當年《音樂詞典》的解讀未涉及海南疍家“水上民歌”也在情理之中。再者,雖然海南疍家“水上民歌”的音樂與“兩廣”、福建的“咸水歌”具有一定的歷史淵源,但經過了千百年“口耳相傳”的傳播過程,加之海南屬多民族省份,且地處熱帶海域,氣候環境獨特,音樂通過“個體遺傳”到“社會遺傳”的過程中發生、發展或變異的情況想來也是必然的。雖然海南疍民演唱海南疍家“水上民歌”仍然有廣東“咸水歌”的一些痕跡,例如語言部分沿襲了廣東粵語,而事實上,海南疍家“水上民歌”早已融入了瓊語的諸多元素,并夾雜了當地鄉音及俚語——即帶有方言的韻味等地方文化色彩,也催化和生成了海南疍家“水上民歌”中鮮明的地域特色。
關于這一論點,廣東疍民文化研究學者吳競龍的《水上情歌》一書中的“水上居民的歷史”一節,簡要敘述了疍民的歷史與文化淵源,其中就有五種學說觀點。他認為:早期的嶺南疍民操廣東(粵)語,這是早期疍民最初的也是最習慣了的基本語言。因此,到了廣西的疍民其語言特點是粵語+廣西方言;漂流到福建的疍民,其語言特點是粵語+閩南語;隨海漂流到熱帶海域的海南疍民,其語言特點是粵語+瓊語+當地方言。關于疍家語言變遷和語言同化的問題,筆者將在另一篇文章中詳細分析論述。
關于海南疍家“水上民歌”語言復雜的特性,仍有一些疑惑擺在我們面前,并等待著合乎邏輯的答案。從北方向嶺南遷徙的大批漢族居民,原本使用中原等地的北方語言,在經過長江以南的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再到嶺南的廣東等地,按正常邏輯應該也會繼續沿用北方語言,他們究竟是什么時候開始入鄉隨俗,同化并熟練掌握了廣東粵語?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們經過千百年的歷史變遷后,仍以廣東粵語為主要的溝通語言沿襲至今?在科技發達、社交廣泛便捷的現狀下,疍家人為什么仍沿用著粵語?海南疍家人與“兩廣”、福建、廣西的疍家人在語言習慣上,尤其是在演唱疍家歌曲的語言上,有無區別?兩者主要的區別在什么地方?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在目前學術界卻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這也為今后疍民音樂文化研究,尤其是為疍民語言學理論研究留下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課題。
語言往往是決定某種民歌音樂形態和風格特征的重要元素之一,按照語言與音樂互相影響的思維邏輯來分析,可以將廣東粵語作為早期疍民的基本語言,漂流到什么地區就融進當地的語言。因此,“兩廣”、福建和海南的疍民各自運用粵語+夾雜當地語言的文化習俗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十分有趣的。對此,也許有人還會產生疑問:千百年的漫長歲月,為什么各地疍家人僅僅融進少量當地方言,而一直堅持和習慣沿用廣東粵語呢?究其原因,一直在海上漂流生活的極為特殊的族群,因此,也就造成了疍民——長期與陸地隔離、與大陸各個民族文化交流、接觸的機會較少。因此,造成今天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疍民一直以來,在物質和文化生活的語言交流上,特別是在演唱疍家音樂歌謠方面,仍然堅定不移地保留和沿用著廣東粵語+當地語言——混合語言的習慣和風格。也就造成了今天我們所提到的疍家音樂在語言上的一個十分有趣的語言文化現象,但這又不失為一種鮮明的語言文化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疍家“水上民歌”在語言(粵語)上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但是根據“音樂與地理環境氣候關系”——即“音地關系學說”的學術觀點,不同的地貌環境以及氣候特征對其個性特征,比如對于旋律、節奏等音樂形態、音樂風格以及音樂傳承的方向,都具有決定性作用和影響。比如:廣東、廣西、福建以及海南的疍家“水上民歌”,其表現主題、內容等方面就有很大不同,其音樂形態、表達形式以及演唱中的襯詞、韻腔和韻味也迥然不同。
第二種來自百度網的解釋新穎且極具有時代特征:“疍家音樂是疍民演唱的通俗歌曲,大家稱之為疍家歌謠、漁歌或咸水歌,它就像是海上人家的《詩經》。“咸水歌”在疍家人生活、勞作中產生,是疍家人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哪里有咸水,哪里就有“咸水歌”,“咸水歌”抒寫了疍家人的歷史。
第三種釋義富有詩意且更加形象化,頗具文學特征:“咸水歌”的名字來自各處,有多種傳說:其一,它與疍家人生活的環境氣候存在因果關系,絕大多數疍家人生活在的海河交匯地帶,疍家人的歌聲伴隨著南海咸水的潮起潮落,從一條條小船上傳出,天長日久,“咸水歌”的名字不脛而走。其二,另外一種說法則認為“咸水歌”的‘咸字主要表達的是男女互相表達情感的情歌,因此也有“南海情歌”極富詩意的美稱,疍家人常年生活在小船上,生活孤獨寂寞,相當一部分“咸水歌”表現男歡女愛的內容也在情理之中。

三亞疍家水上民歌傳承人郭亞清夫婦,現場演唱水上民歌
“咸水歌”是疍家人用以宣泄生活的孤寂和苦悶的最佳方式,經過傳承和發展,逐步發展成為疍家人重要的文化載體。無論婚喪嫁娶,互訴衷腸,都可以通過“咸水歌”來表達。
關于疍家人以及由他們創作的“咸水歌”,清初文化學者屈大均曾有過這樣一段形象的概括:“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滘。”可以毫無夸張地說,“咸水歌”是疍家人海上黯淡生活中的一縷陽光和希望。與其他喜歌、好歌的族群一樣,疍家人把喜、怒、哀、樂統統唱到歌里了,疍家人一路漂泊,一路高唱,無論生活多么艱難都抑制不住唱歌的心。
關于海南疍家“水上民歌”的名稱與概念問題,筆者以為,通過對相關資料中的一些功能和藝術特征進行梳理歸納、概括與提煉,而后方能對其名稱與概念得出一個較為客觀和精準的名稱和解讀。
長期以來,海南疍家人被俗稱為“海上吉普賽人”,他們為了生存,漂流到南海熱帶海域,成為早年的“闖海人”。漂泊不定的海上生活改變了自己的身份,卻練就了堅韌剛毅的性格,疍家人延續了北方中原人的開放爽朗,融進了海上生活的優良習性,疍家人之間和諧相處、熱愛生活、熱愛海洋,疍家人用自己的聰明和智慧,創造了多姿多彩優美動聽的歌謠,疍家“咸水歌”數量龐大、形式多樣、朗朗上口,具有簡單易學、易傳播的特性和優勢,音樂風格淳樸自然,飽蘸了海洋之氣韻,浸滿了大海之滋味。
第四種解讀來自三亞疍家文化博物館館長、疍民出身的鄭石喜,他認為:“咸水歌”是疍家人在海上捕撈中發自內心的歌聲,它經過了千百年的傳唱,形成了水上人家獨特的音樂曲調,它是生活中疍家人相互傾訴的歌謠,表現了疍家人的生活情趣,包含著疍家人日常生活中為人處世的諸多道理。疍家“咸水歌”地域特色鮮明,歌詞內容猶如大海,表演藝術樣式多種多樣,它是流傳在中國熱帶海洋古老的“水上民歌”,是中國海洋文化寶庫中獨一無二的稀世之寶,是中國南海民歌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結語:
總而言之,由于海南疍家“水上民歌”與其它地方民歌傳承方式一樣,采用傳統的“口耳相傳”方式,未能形成或留下原始樂譜。傳承方式具有主觀性和隨意性,從名稱、概念、風格特征到旋律、歌詞、曲式等方面,缺少了“樂譜”作為依據,不僅造成了音樂變異和演化普遍存在的現象,同時也造成了其叫法、稱謂和概念解讀混亂的現象。為了更好地將海南疍家“水上民歌”進行傳承和傳播,將其概念和稱謂梳理清楚就顯得尤為重要,首先需要根據其歷史成因、文化功能等進行分析和研究,對其音樂特點、風格樣式、表演形式等進行合理的分類整理,而后進行客觀全面地釋義和準確概括,為學術界深入研究提供可靠理論依據,為海南疍家“水上民歌”縱深發展,并轉化為傳播領域,提供規范統一的理論概念。
郭建民 ? ?三亞學院音樂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
趙世蘭 ? ?三亞學院音樂學院教授、學校教學督導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