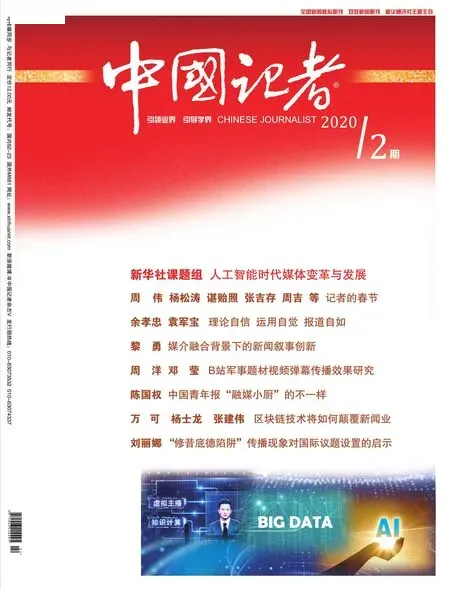“修昔底德陷阱”傳播現(xiàn)象對(duì)國(guó)際議題設(shè)置的啟示
□ 劉麗娜
內(nèi)容提要 “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國(guó)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的高頻熱詞,也是一個(gè)成功的議題設(shè)置案例,在國(guó)際傳播領(lǐng)域形成“病毒式傳播”效應(yīng)。探究這一概念議題成功傳播的背后原因,總結(jié)其傳播特點(diǎn)和規(guī)律,對(duì)我國(guó)媒體提高國(guó)際傳播議題設(shè)置能力具有啟示。本文對(duì)中英文主要媒體對(duì)“修昔底德陷阱”的報(bào)道做了對(duì)比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推動(dòng)“修昔底德陷阱”成為國(guó)際熱詞具有六大因素,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對(duì)我國(guó)媒體國(guó)際傳播議題設(shè)置的五點(diǎn)啟示。
筆者通過大量文獻(xiàn)閱讀分析,廣泛參加研討會(huì)調(diào)研,并與“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的核心推動(dòng)者、《注定一戰(zhàn)——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作者、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當(dāng)面采訪交流等方式,總結(jié)提煉出以下觀點(diǎn)。
一、推動(dòng)“修昔底德陷阱”成為國(guó)際熱詞的六大因素
概念傳播的成功,在于入腦入心,影響決策,最終改變現(xiàn)實(shí)。整個(gè)傳播鏈,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jié)果,筆者將其劃分為六個(gè)方面。
第一、學(xué)術(shù)因素,原創(chuàng)核心概念,內(nèi)涵簡(jiǎn)潔清晰。“修昔底德”在世界歷史學(xué)界具有崇高地位,幾乎等同于“歷史”之義。借用這位史學(xué)“先圣”命名,體現(xiàn)了戰(zhàn)略學(xué)者艾利森發(fā)明概念的眼光。艾利森研究發(fā)現(xiàn),500年間,16次崛起大國(guó)與守成大國(guó)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中,有12次陷入戰(zhàn)爭(zhēng)沖突。這個(gè)獨(dú)到的史實(shí)發(fā)現(xiàn)是“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得以生發(fā)的基礎(chǔ)。從學(xué)術(shù)研究角度,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概念界定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起點(diǎn),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層次性劃分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原點(diǎn),二者之間的張力就構(gòu)成研究的范式和動(dòng)力。概念拋出后,引發(fā)學(xué)界追捧和爭(zhēng)議。一方面,有大量學(xué)者接續(xù)論證,媒體紛紛引用這個(gè)概念,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學(xué)者公開對(duì)其提出批判。例如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家錢乘旦就稱這個(gè)陷阱概念是杜撰而非鐵律。美國(guó)前駐聯(lián)合國(guó)大使泰瑞·米勒也認(rèn)為這個(gè)概念是“明顯的胡言”。不過,從傳播角度,正反兩方面的評(píng)價(jià)同時(shí)放大了其傳播影響力。
第二、現(xiàn)實(shí)因素,概念主題重大,契合國(guó)際張力。考慮到當(dāng)前國(guó)際格局中的力量轉(zhuǎn)換,中國(guó)作為崛起大國(guó),對(duì)國(guó)際秩序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美國(guó)作為守成大國(guó)的感受日益焦慮。“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可謂適時(shí)應(yīng)勢(shì),因此在短時(shí)間內(nèi)備受關(guān)注。艾利森接受筆者采訪時(shí)說,這個(gè)詞之所以能夠廣泛傳播,是因?yàn)樗婕暗膯栴}至關(guān)重要。他說:“在今天紛繁的新聞噪音中,修昔底德陷阱這個(gè)‘大主意’能幫人們看到背后的動(dòng)因,提醒我們它為何如此引人關(guān)注。”著名歷史學(xué)家、斯坦福大學(xué)教授尼爾·福格森在2019年3月的中國(guó)發(fā)展高層論壇上說,正是由于中美關(guān)系的重要性,使得《注定一戰(zhàn)》成了全球暢銷書。

第三、情感因素,針對(duì)人類恐懼,形成心理共振。恐懼是一種人類天性,尤其是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恐懼,對(duì)沖突的關(guān)注,更是世界各國(guó)民眾的共同擔(dān)憂。尋求安全感,戰(zhàn)勝內(nèi)心恐懼,是人類共同的原始心理行為。中國(guó)政治學(xué)者王緝思研究認(rèn)為,“安全”是世界政治終極目標(biāo)之首。遍觀世界歷史,制造恐懼是統(tǒng)治者慣用的政治手段。對(duì)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學(xué)者而言,一個(gè)概念,能讓人產(chǎn)生深刻的情感共振,這是學(xué)術(shù)成功的重要因素。泰瑞·米勒接受筆者采訪時(shí)說,“有些人要靠制造沖突來贏得名聲。”
第四、政策因素,進(jìn)入決策視域,形成思想轉(zhuǎn)化。學(xué)者提出一個(gè)學(xué)術(shù)詞匯,如果得不到政治家和決策者的關(guān)注,其傳播廣度和深度往往有限。“修昔底德陷阱”一詞推出不久,就受到中美思想界、政界,以及全球多個(gè)主要國(guó)家領(lǐng)導(dǎo)人的關(guān)注。2015年9月22日,習(xí)近平主席訪美期間,在美國(guó)華盛頓州當(dāng)?shù)卣兔绹?guó)友好團(tuán)體聯(lián)合歡迎宴會(huì)上發(fā)表演講時(shí)說:“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guó)之間一再發(fā)生戰(zhàn)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015年9月25日,國(guó)家主席習(xí)近平在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山集體會(huì)見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參議院和眾議院領(lǐng)導(dǎo)人時(shí)說,中美關(guān)系發(fā)展要防止跌入所謂大國(guó)沖突對(duì)抗的“修昔底德陷阱”,要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使兩國(guó)關(guān)系發(fā)展成果更多惠及兩國(guó)人民和世界人民。2017年1月18日,習(xí)近平在聯(lián)合國(guó)日內(nèi)瓦總部發(fā)表了題為《共同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主旨演講,其中提到,“只要堅(jiān)持溝通、真誠(chéng)相處,‘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
美國(guó)前總統(tǒng)奧巴馬2015年9月24日在華盛頓與來訪的習(xí)近平主席會(huì)晤時(shí)表示,我不認(rèn)同守成大國(guó)和新興大國(guó)必將發(fā)生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國(guó)尤其是美中之間更要盡量避免沖突。我相信美中兩國(guó)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國(guó)現(xiàn)任總統(tǒng)特朗普較少使用高階學(xué)術(shù)詞匯,但他上任后的種種單邊主義、保護(hù)主義行為,使中美兩國(guó)思想界對(duì)“修昔底德陷阱”的擔(dān)憂有增無減。
考慮非期望產(chǎn)出的中國(guó)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測(cè)度及差異分析 … ……………………………… 劉丙泉,王 超(2.45)
第五、傳播因素,強(qiáng)勢(shì)媒體力推,“N次”現(xiàn)象傳播。圍繞“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形成了原創(chuàng)書籍、新書評(píng)論、理論解讀、媒體專欄、專家引用等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傳播,不斷放大,形成“N次傳播”的乘數(shù)效應(yīng)。本文在重點(diǎn)研究英美主流媒體時(shí)發(fā)現(xiàn),在影響國(guó)際社會(huì)輿論的英語傳播場(chǎng)域中,最受知識(shí)界思想界關(guān)注的幾大英語媒體里,以英國(guó)《金融時(shí)報(bào)》及FT中文網(wǎng)最為熱衷傳播這個(gè)概念。“修昔底德陷阱”一詞甚至被《金融時(shí)報(bào)》評(píng)為2018年的年度詞匯,在2018年12月19日,該報(bào)資深專欄作家拉赫曼專門撰文點(diǎn)評(píng)。此外,《華爾街日?qǐng)?bào)》《紐約時(shí)報(bào)》《華盛頓郵報(bào)》《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國(guó)家利益》《大西洋月刊》《外交》雜志等各大頂級(jí)學(xué)術(shù)刊物和主流媒體,也是這一概念的重要傳播載體。自2011年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8年來,“修昔底德陷阱”的傳播正好趕上智能手機(jī)、移動(dòng)傳播大發(fā)展、傳統(tǒng)媒體和新媒體大融合的歷史潮流。中國(guó)走在全球前列的“兩微一端”,使新詞傳播的速度、廣度和深度都極大拓展,不斷突破時(shí)空邊界。關(guān)于中英文主要媒體對(duì)“修昔底德陷阱”的報(bào)道,本文將在第二部分細(xì)述。

第六、個(gè)人因素,學(xué)界導(dǎo)師影響,“旋轉(zhuǎn)門”效應(yīng)顯著。已近八旬的格雷厄姆·艾利森從上世紀(jì)70年代初出茅廬,至今在學(xué)界政界活動(dòng)已長(zhǎng)達(dá)半個(gè)世紀(jì),其學(xué)術(shù)背景橫跨哈佛和劍橋這兩所歐美一流大學(xué)。他是哈佛大學(xué)肯尼迪政府學(xué)院首任院長(zhǎng),哈佛大學(xué)肯尼迪政府學(xué)院貝爾福科學(xué)與國(guó)際事務(wù)中心主任、教授。1977年至1989年期間,在艾利森的領(lǐng)導(dǎo)下,哈佛肯尼迪政府學(xué)院由一個(gè)尚未成熟的小型項(xiàng)目成長(zhǎng)為一個(gè)世界級(jí)的專業(yè)公共管理學(xué)院,學(xué)生遍布世界,其中大多已經(jīng)是各國(guó)精英。里根總統(tǒng)時(shí)期,他曾任國(guó)防部長(zhǎng)的特別顧問;他還是美國(guó)國(guó)防部多任部長(zhǎng)的國(guó)防政策委員會(huì)成員。艾利森曾兩次獲得國(guó)防部最高公民獎(jiǎng),以及公共服務(wù)特別獎(jiǎng)?wù)碌仁鈽s。他在30歲左右就在學(xué)界嶄露頭角,首部著作《決策的本質(zhì):解釋古巴導(dǎo)彈危機(jī)》于1971年出版,并于1999年經(jīng)修改后再次出版。該書以40多萬冊(cè)的銷量在20世紀(jì)政治科學(xué)類暢銷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根據(jù)筆者調(diào)研,西方主流媒體最早開始刊登“修昔底德陷阱”一詞是《紐約時(shí)報(bào)》2011年1月31日的一個(gè)“新詞匯編”,其中引用了哈佛大學(xué)艾利森教授提出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標(biāo)簽,并用之比喻中美關(guān)系,其新聞背景是時(shí)任中國(guó)國(guó)家主席胡錦濤訪美。2012年8月1日,艾利森開始在英國(guó)《金融時(shí)報(bào)》發(fā)表文章,正式全面闡述“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此后,艾利森開始在中美學(xué)界不遺余力地推廣他的這個(gè)概念。一方面,他本人撰寫了大量文章,在核心報(bào)刊上發(fā)表;另一方面,他游走在美國(guó)和中國(guó)政學(xué)商界,像“布道者”般傳播自己的思想發(fā)明,成為各方座上賓。本文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6年來,艾利森本人撰寫的涉及這個(gè)概念的公開文章不下20篇,都刊登在有影響力的媒體上。2017年艾利森出版專著《注定一戰(zhàn):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2018年,隨著中美貿(mào)易戰(zhàn)的發(fā)酵和霸屏,《注定一戰(zhàn)》成為從紐約、華盛頓、北京到上海的中美關(guān)系領(lǐng)域重要談資。2019年1月,《注定一戰(zhàn)》一書的中文版出版發(fā)行。從時(shí)間跨度上看,“修昔底德陷阱”一詞逐步達(dá)到今天的傳播熱度已經(jīng)過8年。
二、中英文主要媒體對(duì)“修昔底德陷阱”的報(bào)道
概念、理論、思想的傳播離不開新聞媒介。“修昔底德陷阱”一詞的廣泛影響力,離不開大眾傳媒的放大、疊加傳播,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乘數(shù)效應(yīng)。本文梳理了英文主要媒體的相關(guān)報(bào)道。考察時(shí)段從2011年1月至2019年3月31日。
1.英文報(bào)刊相關(guān)報(bào)道
《金融時(shí)報(bào)》英文網(wǎng)站,第一篇文章是艾利森于2012年8月21日發(fā)表的《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修昔底德陷阱在太平洋苗頭初現(xiàn)》)。8月28日,F(xiàn)T中文網(wǎng)將該文翻譯并修改標(biāo)題為《美國(guó)應(yīng)接納中國(guó)的崛起》后刊發(fā)。自此,這一詞開始在中國(guó)國(guó)際關(guān)系學(xué)界和傳播界成為“病毒式”傳播新詞。截至2019年3月31日,《金融時(shí)報(bào)》共刊登31篇相關(guān)文章,F(xiàn)T中文網(wǎng)更多達(dá)64篇。
《華盛頓郵報(bào)》共刊登23篇相關(guān)文章,自2015年6月6日開始刊登第一篇相關(guān)文章《美中權(quán)力平衡》,2017年8月,艾利森的書兩次登上該報(bào)暢銷書榜。
《華爾街日?qǐng)?bào)》在同一時(shí)段內(nèi),共刊登了6條與“修昔底德陷阱”相關(guān)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4篇文章都出自艾利森本人之手。
《紐約時(shí)報(bào)》共刊登12篇相關(guān)文章,其中,2011年1月31日的“新詞匯編”欄目專門選取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詞,該報(bào)的華盛頓首席記者大衛(wèi)·桑格敏銳地關(guān)注到該詞,并加以解釋。
《經(jīng)濟(jì)學(xué)人》雜志共有4篇相關(guān)文章,其中兩篇是對(duì)《注定一戰(zhàn)》一書的書評(píng)簡(jiǎn)介。
引人注意的是,美國(guó)的國(guó)際關(guān)系理論研究重鎮(zhèn)“國(guó)家利益”網(wǎng)站是傳播“修昔底德陷阱”一詞的重要陣地,從2015年到2019年3月底,共刊載了89篇相關(guān)研究文章,其中艾利森本人署名文章多達(dá)17篇,有兩篇是與Dimitri K.Simes聯(lián)合署名,此人是《國(guó)家利益》出版人和CEO,也是國(guó)家利益中心總裁。這顯示出美國(guó)外交學(xué)界對(duì)這一概念的重視,以及艾利森的人脈關(guān)系。
2.三大外電相關(guān)報(bào)道
根據(jù)本文調(diào)研,在路透社、美聯(lián)社和法新社這三大西方主要通訊社中,對(duì)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報(bào)道相對(duì)有限。在統(tǒng)計(jì)時(shí)段內(nèi)總共只有24條。其中,路透社有18條,大部分為綜述和分析文章。美聯(lián)社只有2條,并且都是在“編輯綜述”欄目下,是對(duì)《中國(guó)日?qǐng)?bào)》文章的摘要。法新社也只有4條,第一條是2016年2月19日,《澳大利亞警告北京南海沖突威脅》。
3.中國(guó)主流媒體相關(guān)報(bào)道
本文考察了新華社通稿、人民日?qǐng)?bào)、參考消息、光明日?qǐng)?bào)等主流媒體,一些數(shù)據(jù)如下:
截至2019年3月31日,新華社通稿共播發(fā)帶有“修昔底德陷阱”一詞的文章42篇,其中最早一篇是在2013年12月12日。《人民日?qǐng)?bào)》共刊登了113篇,其中最早一篇是在2011年6月29日,文章題為《誠(chéng)心誠(chéng)意做合作伙伴》。《人民日?qǐng)?bào)·海外版》刊登了58篇。《解放軍報(bào)》刊登了36篇。《光明日?qǐng)?bào)》共刊登了49篇。
《參考消息》共刊登了161篇。第一篇有關(guān)文章是在2011年1月24日,摘譯《紐約時(shí)報(bào)》文章《超級(jí)大國(guó)和新興大國(guó)有時(shí)也能皆大歡喜》。這篇也是國(guó)內(nèi)央媒對(duì)“修昔底德陷阱”一詞最早引入的文章,顯示了《參考消息》對(duì)國(guó)際新詞的敏銳度。
此外,通過中國(guó)知網(wǎng)搜索,截至2019年1月31日,關(guān)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期刊文章有181條,以“修昔底德陷阱”為主題的博碩士論文有5篇,國(guó)際會(huì)議有4個(gè)。不過,這個(gè)統(tǒng)計(jì)顯然是不完整的,實(shí)際數(shù)量應(yīng)該遠(yuǎn)多于此。
通過以上媒體抽樣量化分析,可以初步看出,對(duì)于“修昔底德陷阱”這個(gè)概念的傳播,國(guó)內(nèi)媒體更為敏感和重視,傳播的數(shù)量也多于西方媒體。這從一個(gè)側(cè)面反襯出,中美在國(guó)際權(quán)力關(guān)系中的強(qiáng)弱態(tài)勢(shì)。此外,西方英文媒體中,英國(guó)《金融時(shí)報(bào)》和路透社的報(bào)道無論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都相當(dāng)突出,這顯示出英國(guó)作為已衰落的大國(guó)在國(guó)際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的“旁觀者”角色。
修昔底德陷阱
此概念出自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守成大國(guó)和新興大國(guó)身陷結(jié)構(gòu)性矛盾,戰(zhàn)爭(zhēng)沖突極易發(fā)生。通俗理解,就是“新興大國(guó)與守成大國(guó)必有一戰(zhàn)”。這一觀點(diǎn)的核心源自古希臘歷史學(xué)家修昔底德就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zhēng)給出的“診斷”——“使戰(zhàn)爭(zhēng)變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給斯巴達(dá)帶來的恐懼”。艾利森在《注定一戰(zhàn):中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中研究發(fā)現(xiàn),500年間,16 次崛起大國(guó)與守成大國(guó)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中,有12 次陷入戰(zhàn)爭(zhēng)沖突。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在現(xiàn)代核武平衡下,中美爆發(fā)大規(guī)模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不過,不排除發(fā)生小規(guī)模局部沖突的可能。更為可能的博弈領(lǐng)域是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如貿(mào)易摩擦。許多學(xué)者,如北京大學(xué)教授錢乘旦認(rèn)為,這一陷阱并非修昔底德預(yù)言。有評(píng)論指出,世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雙方都不應(yīng)掉入這一“語言陷阱”。不過,自2011 年1 月,《紐約時(shí)報(bào)》首次刊登出這個(gè)學(xué)術(shù)新詞,迄今已近十年,“修昔底德陷阱”一直保持相當(dāng)可觀的國(guó)際傳播熱度,無疑值得研究深思。
三、對(duì)國(guó)際傳播議題設(shè)置的五點(diǎn)啟示
通過以上量化與質(zhì)化分析,可以看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成功傳播現(xiàn)象絕不是偶然。筆者認(rèn)為,反思這一“現(xiàn)象級(jí)傳播”,對(duì)我國(guó)媒體的議題設(shè)置和輿論引導(dǎo)能力建設(shè)具有啟發(fā),可總結(jié)為以下五點(diǎn):
首先,扶助學(xué)者,發(fā)揮學(xué)界輿論引領(lǐng)。通過以上對(duì)“修昔底德陷阱”一詞的國(guó)際傳播成功原因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在相關(guān)因素當(dāng)中,有著五個(gè)“一”,即一人、一書、一報(bào)、一刊、一校。一人指的是這一概念的靈魂人物格雷厄姆·艾利森;一書指的是《注定一戰(zhàn)》;一報(bào)是在這一概念的傳播中起到先鋒旗手作用的英國(guó)《金融時(shí)報(bào)》;一刊是指美國(guó)《國(guó)家利益》線上線下期刊;一校是指全球頂級(jí)名校哈佛大學(xué)。如果我們想在國(guó)際舞臺(tái)發(fā)出更多更響亮的中國(guó)聲音,并得到世界的廣泛認(rèn)同,需要我學(xué)界發(fā)掘并支持符合我領(lǐng)導(dǎo)人外交思想,符合我輿論導(dǎo)向的國(guó)際學(xué)術(shù)明星。這樣的學(xué)術(shù)靈魂人物需要已經(jīng)具有相當(dāng)?shù)膰?guó)際影響力,能夠在跨國(guó)學(xué)界思想界得到廣泛認(rèn)可,可通過組織跨國(guó)學(xué)術(shù)交流活動(dòng),助其在海外媒體發(fā)表文章等渠道擴(kuò)大其正向輿論引導(dǎo)作用。
其次,內(nèi)外并重,放大媒體擴(kuò)音作用。一方面,要“固船出海”,提升我國(guó)內(nèi)主要媒體自身的國(guó)際傳播力,可與學(xué)術(shù)靈魂人物合作,保持一定的發(fā)聲頻率。另一方面,要繼續(xù)“借船出海”,善借國(guó)外大媒體,在其上發(fā)表有學(xué)術(shù)水準(zhǔn)、有影響力的文章。例如,北京大學(xué)、清華大學(xué)、復(fù)旦大學(xué)、中國(guó)社科院等多家大學(xué)和研究機(jī)構(gòu)、知名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成果受到美方學(xué)界重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美方思想輿論。
第三,認(rèn)識(shí)價(jià)值,看清客觀風(fēng)險(xiǎn)警示。盡管“修昔底德陷阱”一詞是美國(guó)人的發(fā)明,但應(yīng)客觀認(rèn)清其雙向價(jià)值。艾利森對(duì)筆者說,他反復(fù)提醒“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要讓大家看到中美關(guān)系中的風(fēng)險(xiǎn),從而避免這一陷阱。他認(rèn)為,中美領(lǐng)導(dǎo)人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這一問題的風(fēng)險(xiǎn)和嚴(yán)峻程度,因此雙方都在謹(jǐn)慎管控分歧。不過,艾利森同時(shí)表示,鑒于中美雙方的經(jīng)貿(mào)摩擦,雙邊關(guān)系“在變得糟糕之前還會(huì)更糟糕。”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前校長(zhǎng)勞倫斯·薩默斯2019年3月在北京的一次研討會(huì)上表示,中國(guó)要讓美方明確其意圖。
第四,加強(qiáng)調(diào)研,做好我方議題對(duì)沖。國(guó)內(nèi)有學(xué)者提示,不要陷入西方話語陷阱的陷阱,認(rèn)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是一個(gè)話語陷阱,要努力構(gòu)建中國(guó)自身的國(guó)際關(guān)系理論體系。誠(chéng)然,在中國(guó)崛起的歷史背景下,這種觀點(diǎn)有其道理,不過,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新語境下,我們面對(duì)西方話語的包圍,無法做到獨(dú)善其身。如果想積極影響西方話語,首先要了解其話語,能夠熟練運(yùn)用其話語,從而才能找到以我為主,革舊鼎新的中國(guó)式話語。但這個(gè)過程將是漫長(zhǎng)的。在此情況下,我方要努力自我創(chuàng)設(shè)議題,以免被動(dòng)應(yīng)對(duì)美方和西方思維下的理論影響。這種議題應(yīng)當(dāng)是針對(duì)當(dāng)前我對(duì)外關(guān)系最重要而緊迫的議題,需要具有簡(jiǎn)潔明晰、兼通中外的特征。最好還能具有物質(zhì)實(shí)際的支撐。從這個(gè)意義考察,習(xí)近平主席倡導(dǎo)的“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和“一帶一路”等無疑是世界級(jí)的重要傳播概念。圍繞這個(gè)“母題”,可以衍生出大量次級(jí)議題,需要國(guó)際傳播鏈上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合力推動(dòng)。
第五,分清對(duì)象,抓住關(guān)鍵少數(shù)受眾。從前面量化分析可見,“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傳播從一開始就是“思想者的游戲”,其傳播范圍是國(guó)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的知識(shí)精英,主要包括中美政界、國(guó)際關(guān)系學(xué)界、主要媒體重要專欄作者等意見領(lǐng)袖。這些人的所思所想所寫所講會(huì)影響更多受眾。但對(duì)于普羅大眾,他們對(duì)“修昔底德陷阱”并無興趣。因此,我方如果創(chuàng)造推動(dòng)新的議題,更應(yīng)看重精英傳播,而非大眾傳播。在當(dāng)前智能傳媒的分眾化傳播時(shí)代,國(guó)際知識(shí)精英具有跨越物理邊界和語言邊界的特點(diǎn),他們是活躍在全球思想輿論場(chǎng)的一群小眾人士,具有相近的閱讀偏好與媒體選擇,但其思想影響力卻是指數(shù)級(j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