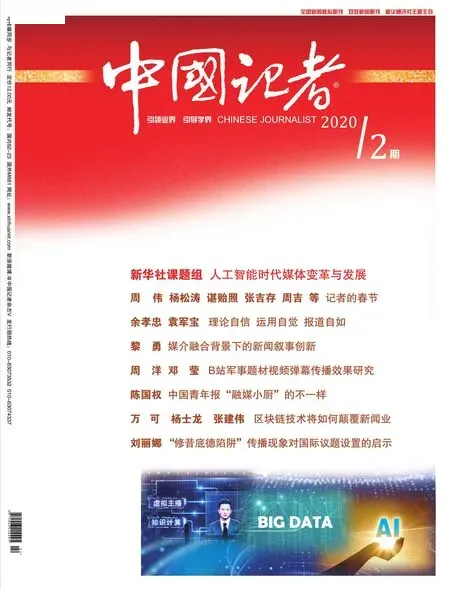九年七獲中國新聞獎:地方媒體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從吉林朝鮮文報經(jīng)驗看國際傳播的可能路徑
□ 本刊記者 張壘
2011年,第十九屆中國新聞獎?wù)皆鲈O(shè)國際傳播獎。2019年,第二十八屆中國新聞獎的國際傳播獎走過了九個年頭。九年之中,身處東北、以民族語言文字為載體的吉林朝鮮文報拿到七個中國新聞獎。這一成績,無論是對于邊境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媒體,還是對于一般的地市級媒體來說,都顯得非常引人注目。
吉林朝鮮文報的成功有一些獨(dú)特優(yōu)勢,如它的主要傳播對象——韓國經(jīng)濟(jì)相對較為發(fā)達(dá),韓國與中國之間的經(jīng)濟(jì)社會和文化交流也非常頻繁。這都為做好對外傳播提供了豐厚土壤。但客觀來看,吉林朝鮮文報能夠九年七獲中國新聞獎,不僅是因為天時地利,更在于在新聞信息的生產(chǎn)和傳播過程中掌握并運(yùn)用了許多規(guī)律性的東西,觀察、發(fā)掘這些規(guī)律,可以為更好地推動國際傳播向前發(fā)展貢獻(xiàn)力量。
2019年12月8日,由吉林日報報業(yè)集團(tuán)、民族出版社共同主辦,本刊學(xué)術(shù)支持,吉林朝鮮文報社承辦的民文媒體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為暨《吉林朝鮮文報中國新聞獎獲獎作品集》出版座談會在長春召開。座談會由吉林日報社總編輯王亮主持,中國記協(xié)副主席、吉林日報社社長張育新,中國記協(xié)書記處書記張百新,吉林省記協(xié)主席李新民,以及來自中國傳媒大學(xué)、吉林大學(xué)等高校的專家學(xué)者參與座談。
一、全局意識、宏觀視野
不少與會專家提到,閱讀吉林朝鮮文報獲獎作品,一個直觀印象是,這些報道都是“大”報道。無論是從標(biāo)題還是故事的內(nèi)核上看,很難判斷出這些報道究竟來自哪一級媒體,體現(xiàn)的是大視野、凸顯的是大情懷、講述的是大故事。中國傳媒大學(xué)電視學(xué)院黨委書記、教授曾祥敏認(rèn)為,這些獲獎作品以家國情懷為立足點和切入點,服務(wù)于區(qū)域性的人群,體現(xiàn)出以人物為主角,以故事為載體,以情感為核心的突出特點。
獲獎作品雖然立足于吉林、立足于圖門江,但講的都是新時代的中國故事,構(gòu)成了一幅新時代的圖景。如《一歸國勞務(wù)人員在圖們江畔建起一座“百年部落”》,講的是一位“結(jié)束10年海外勞務(wù)生活,5年前回到家鄉(xiāng)”的歸國人員,而他思考的問題、做的事情是“國外掙來的錢用在哪兒最合適最有價值?”。首先,主人公的身份非常具有時代特征,其次,主人公的思考也具有普遍意義,是對富裕之后的中國人的共同追問,第三,主人公所做之事——到處收集朝鮮族民俗文物,來建設(shè)一個“百年部落”——更是具有深層次的價值內(nèi)涵:像愛護(hù)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hù)民族文化,這正是我們所倡導(dǎo)的。文章的時代性、民族性,和具有價值導(dǎo)向作用的大眾性正是由此體現(xiàn)出來。

□ 2019 年12 月8 日,民文媒體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為暨《吉林朝鮮文報中國新聞獎獲獎作品集》出版座談會在長春召開。
中國記協(xié)書記處書記張百新指出,從整體看,中國新聞獎的獲獎作品都是具有全局意識和宏觀視野,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和大局的作品。中國新聞獎關(guān)注的都是每年圍繞中心、服務(wù)大局,反映在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新舉措新進(jìn)展的重大新聞。不管是以大見小,還是以小見大,不管用什么樣的表達(dá)方式,最終體現(xiàn)出來的必須是主題主線。圍繞主線開展主題報道,是我們從事新聞報道的一項基本的工作內(nèi)容。比如,2017年是黨的十九大的召開之年。那么,迎接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就是這一年宣傳思想工作的主線。中國新聞獎的評選,同樣要圍繞這一主題主線。換句話說,反映這一主題主線的報道,而非圍繞一省一地、某個企業(yè)的報道,更受中國新聞獎的青睞。
二、本土資源、地方特色
不可否認(rèn),重大活動、重大突發(fā)事件、重要典型人物,這些都是獲獎最集中的領(lǐng)域。但在重大事件報道方面,與央媒相比,地方媒體顯然不占優(yōu)勢。可以說,軟性的文化才是地方媒體最有競爭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領(lǐng)域。對民族地區(qū)媒體來說,文化往往還被賦予一定程度上的神秘色彩,也是讀者最感興趣的地方——了解別人不同的生活模式是人的本能。這就使得相關(guān)報道非常容易調(diào)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而能夠體現(xiàn)文化的,則是特殊的、具有高度識別性的“符號”。仔細(xì)閱讀吉林朝鮮文報的獲獎作品,會發(fā)現(xiàn)這些作品都有著非常強(qiáng)烈的符號色彩,比如“圖門江”“長白山”“百年部落”,這些符號和由此而來的神秘感,輔之以讀者的想象,就為文章打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chǔ)和鋪墊。
有了文化色彩、凸顯出符號標(biāo)識,相當(dāng)于給讀者正式發(fā)出了閱讀的邀請函。但讀者受眾來不來,來了之后體驗如何,這就需要豐富的報道內(nèi)涵來支撐。地方媒體最大的優(yōu)勢就是對于吾土吾民的深切觀察,比如,在外人眼中,圖門江只是一條河,但在當(dāng)?shù)厝说纳罾铮休d的卻是百年悲歡。而寫出這種感覺,需要的就是“俯下身、沉下心,查實情、說實話”,這是地方媒體,尤其是民族地區(qū)媒體的最強(qiáng)優(yōu)勢,也是最能達(dá)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地方。
運(yùn)用好地方優(yōu)勢,除了貼近、深入之外,還要把握好報道的“反思性”,這種“反思性”就是要挖掘出地方性和全局性,地方族群文化和中華民族整體文化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比如,《悠悠圖門江綿綿百年悲歡——下馬來姜寶今奶奶一家的故事》一文中,描寫在下馬來生息百年的姜寶今老奶奶一家遷移、定居和奮斗故事,不僅是寫朝鮮民族的百年史,更是通過社會變遷反映出國家發(fā)展和個人幸福的關(guān)聯(lián),反映出國家進(jìn)步和民族興旺的邏輯,從而達(dá)到既“進(jìn)得去”又“出得來”的效果。
專家認(rèn)為,做好國際傳播,還需要把握好中國觀與世界觀——一方面從世界看中國,另一方面以中國的視角來觀世界。在吉林朝鮮文報的獲獎作品中,獲得第二十三屆中國新聞獎和第二十五屆中國新聞獎的兩篇作品,恰好形成了一個非常鮮明的對照。兩個都是系列報道,前一個是“韓國人眼里的中國——撥開云霧看虛實”,后一個是“韓國正值中國風(fēng)時代”。所謂“以世界看中國”,就是不僅要熟悉我們自己究竟是什么樣,還要了解別人眼中和世界眼中的我們,并由此作出具有針對性的、有效的回應(yīng)。這樣,才能起到增信釋疑的效果,才能發(fā)揮架起溝通橋梁的作用。而所謂“以中國來觀世界”,就是在看待國際事務(wù)中,把握好自己的原則立場,把握好自己的“主體性”,不是亂花漸欲迷人眼,做到亂云飛渡仍從容。傳播(Communication)的本意是“交流”“交通”,國際(International),也是指國家間的相互聯(lián)系,國際傳播的解疑釋惑,前提就在于對雙方的深入了解。而這正是民族地區(qū)媒體,尤其是民族語言文字媒體能夠大有作為的地方。吉林朝鮮文報的獲獎作品《韓國人眼里的中國——撥開迷霧看虛實》,就是一種初步嘗試。在這種語言文化的交叉處、重疊處做文章,還需要由淺到深不斷探索。
在討論中,與會專家達(dá)成共識,地方媒體要發(fā)掘好本土資源,體現(xiàn)出地方優(yōu)勢,核心還是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增強(qiáng)“四力”問題。文化、地方、語言三大優(yōu)勢能不能發(fā)揮出來、發(fā)揮到什么程度,關(guān)鍵看是不是做到了“三貼近”,是不是踐行了“走轉(zhuǎn)改”,是不是真正運(yùn)用好了“腳力、眼力、腦力、筆力”。
三、周邊傳播、文化外交
在我國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傳播中,民族地區(qū)媒體是做好周邊傳播的骨干。周邊國家和我國大多處于同一個文化圈,對民族地區(qū)媒體來說,往往還有著歷史淵源和風(fēng)俗習(xí)慣上的相近性,做好對外傳播具有先天優(yōu)勢。與會專家認(rèn)為,從吉林朝鮮文報的經(jīng)驗來看,民族地區(qū)媒體做好以周邊國家為核心的對外傳播,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先網(wǎng)后報,渠道優(yōu)先。早在十年前,吉林朝鮮文報在采編流程上就在國內(nèi)新聞界率先采取先網(wǎng)后報的運(yùn)作模式,所有新聞信息先在網(wǎng)上發(fā)布,然后從網(wǎng)上發(fā)布的信息中再進(jìn)行選擇,刊登在報紙上。這也成為今天媒體融合發(fā)展的主流模式。這種模式背后其實是一種渠道優(yōu)先的思維。和對內(nèi)傳播不同,對外傳播面對的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地方”,而是文化意義上的“區(qū)域”,不是地理空間,而是一種文化空間。報紙是地理空間的產(chǎn)物,而網(wǎng)絡(luò)則是文化空間的現(xiàn)象。因此,先網(wǎng)后報在本質(zhì)上實現(xiàn)的是從地理空間到文化空間的戰(zhàn)略轉(zhuǎn)移。
二是開放合作,媒體外交。除了很早就介入融合發(fā)展,吉林朝鮮文報還走出國門,在地方媒體中率先創(chuàng)辦海外版。我國媒體曾經(jīng)有過一陣創(chuàng)辦海外版的熱潮,不僅中央媒體,新民晚報等地方媒體也曾經(jīng)先后在世界各地設(shè)立記者站、創(chuàng)辦海外版。囿于經(jīng)濟(jì)實力和現(xiàn)實需求,民族地區(qū)媒體創(chuàng)辦海外版規(guī)模不可能太大,因此,其功能也有新變化。地方媒體海外版的主要功能在于三個平臺:展示平臺、合作平臺和外交平臺。展示平臺自然是把中國的新聞和故事講給對象國,合作平臺則是海外版作為對象國認(rèn)可的媒體,可以更好地和當(dāng)?shù)氐纳鐖F(tuán)、媒體開展合作,而外交平臺則是基于這種合作,使媒體能夠更好地發(fā)揮公共外交的職能。媒體也是由具體的人來創(chuàng)辦和運(yùn)作的,有了良好的日常合作和深入交往,就為重大宣傳需要和突發(fā)事件的應(yīng)對處理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礎(chǔ)。
三是情理交融,尋找共性。民族地區(qū)媒體處在重疊區(qū)域,有著雙重身份。周邊傳播也應(yīng)該像邊民的交流一樣,突出共同點、少講大道理。以吉林朝鮮文報為例,它的國際傳播講的是文化、講的是歷史、講的是故事。實踐證明,七分故事、三分道理才能更好地讓受眾接受,訴諸情感的軟性傳播往往比訴諸理性的硬性宣傳更有效果。想要“讓人入道”“啟人悟道”,就要善于觸動受眾最敏感的心弦。獲獎作品《平安歸來吧,兒子》就是成功地找到了“朝鮮族中國人”這個中韓兩國人民共同的關(guān)注點,讓中韓兩國人民有了共同的企盼。正是在這種對于共同的追求中,兩國人民的感情得以進(jìn)一步地加深。從理論上來說,有著共同目標(biāo)的運(yùn)動有助于把不同的群體整合在一起,而媒體通過不斷地尋找和有意識地制造這種共同目標(biāo),就能夠更好地加深不同群體之間對共性的認(rèn)識,從而營造出一種集體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