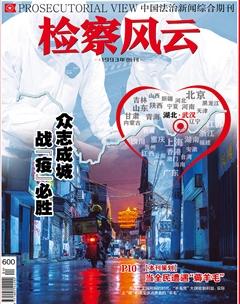氣候生變 小島嶼國家組團“焦慮”
曹怡
在氣候變化的“前線戰場”,不少小島嶼國家面臨海平面上升、島嶼即將被海水吞噬的困境。小島嶼國家面臨的環保問題受到全球關注,也對全球環保政策帶來巨大影響。
海島國家現狀不樂觀
2019年9月1日,颶風多里安(DORIAN)橫掃巴哈馬阿巴科群島,它的風速接近每小時300公里,并帶來近8米高的海浪。颶風多里安帶來的破壞是毀滅性的,巴哈馬衛生部部長表示,死亡人數將會很“驚人”。
多里安的出現引起全球對小島嶼生存脆弱性的關注。人們擔心,全球氣溫上升將帶來更多的極端風暴情況和海平面上升,這將威脅小島國和低洼沿海地區的生存,最終,整個島嶼可能被淹沒。同時,小島國的農民和漁民不僅會因為氣候變暖失去生計能力,還可能因為惡劣天氣而喪命。馬爾代夫一半以上的領土海拔不到1米。“我們受到氣候變暖的影響最大,因此我們一直在堅持倡導和說服其他國家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馬爾代夫駐聯合國大使侯賽因(Mohamed Hussain)說。
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GDP、領土、人口和溫室氣體排放量在世界上占比不到1%,它們的聲音在世界舞臺十分微弱或根本無人問津,然而在氣候問題上,經過30多年的努力,它們已經組成具有發言權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聯盟(AOSIS,以下簡稱小島嶼聯盟),該聯盟的成立離不開以卡梅倫(Cameron)為代表的一小群英國律師團體的助力。
1988年,這一律師團體向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提交了一份法律意見書,呼吁受到海平面上升帶來滅頂之災影響的島國可以建立一個組織,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1990年, 小島嶼聯盟正式成立。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峰會上,卡梅倫先生見證了他所希望發生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署。
小島嶼聯盟發展到現在已有39個正式成員和5個觀察員,它們主要分布在三個地區(加勒比,太平洋,以及橫跨非洲、印度和中國南海的一個島嶼群),包括一些地勢低洼的沿海國家,如伯利茲和圭亞那。它們被認為代表了一種特別的集體利益。單看聯盟中的個體,其能力十分有限,但聚集起來,集體的影響力是巨大的。馬爾代夫政府顧問兼作家馬克·萊納斯(Mark? Lynas)表示:“在其他人認真對待氣候危機之前,小島嶼聯盟早已把它擺上重要的議事日程位置。”島國是最先受到海平面上升影響的國家,因此,小島嶼聯盟成員國冒險向發達國家直言其碳排放給島國帶來的滅頂之災。萊納斯表示:“小島嶼聯盟在改變基調和影響政策方面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聯盟在氣候協議中加入了一些措辭,以解決他們具體關切的問題,例如如何估量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失和損害;如何獲得財政支持等。小島嶼聯盟提供了一個范例,在環保這個領域,聯合行動是唯一能帶來改變的方式,國家之間組織起來,推動國際合作。
在紐約聯合國大會即將結束之際,人們用一整天的時間來關注小島嶼國家的環保問題。領導人審議了2014年薩摩亞峰會提出的可持續發展藍圖“薩摩亞路徑”的進展情況。為什么這樣微小的組織可以產生具有世界性的影響?這可以歸結到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三大優勢。第一個是專注,生存困境使它們思維集中。來自馬爾代夫的侯賽因估計,她在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上花費了70%—80%的時間。第二個是道德論點很有說服力。以不久前在圖瓦盧舉行的太平洋島嶼論壇首腦會議為例,作為該組織的18個成員國之一,澳大利亞堅持在最終宣言中去掉對煤炭的提及,并軟化措辭。圖瓦盧總理埃內萊·索波阿加(Enele Sopoaga)當場斥責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你們關心的是拯救澳大利亞的經濟,我關心的是拯救圖瓦盧的人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加起來約占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三分之一和聯合國會員國的五分之一,這給了它們充足的發言時間和在聯合國的投票權。
環保問題變化多端?
凱文·康拉德(Kevin Conrad)在目睹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海灘消失后成為一名環保活動人士,現在他是雨林國家聯盟的領導人。他回憶起2005年蒙特利爾氣候峰會的戲劇性場面,超過20個國家發言支持美國所反對的加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努力。“這種勢頭說明建立廣泛的聯盟是贏家。”他說。
兩年后,在巴厘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康拉德又一次卷入了“鬧劇”。美國再次反對達成共識,這次是反對制定新的氣候條約。作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代表,康拉德與美國對話:“我們尋求你們的領導,但如果出于某種原因,你們不愿意領導,那請讓開,留給我們。”話音落地,大家歡呼起來,美國很快宣布將加入這一共識。這一時刻成為氣候外交的傳奇亮點。
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秘書長氣候行動峰會上沒有出現類似激動人心的時刻。美國總統特朗普沒有改變讓美國退出巴黎協議的決定,但小島嶼聯盟仍希望能引起轟動,它們準備了一份“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方案”。
首先,小島嶼聯盟想強調需要注意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警告,即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將全球變暖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在去年10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IPCC強調了將升溫幅度控制在1.5攝氏度與將升溫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之間的影響差異。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在今后10年采取大規模的行動。島民們希望看到政府采取行動的決心,他們希望看到更多的碳排放國公開接受IPCC的報告。
其次,小島嶼聯盟尋求如何采取大膽行動的方法。聯合國駐伯利茲大使洛伊斯·楊(Lois Young)表示:“我們所做的貢獻不多,但我們希望以身作則。”伯利茲今年接替馬爾代夫擔任小島嶼聯盟主席,該國將環保目標轉向100%的可再生能源,并規劃出一條實現碳中和的道路。馬紹爾群島率先提交了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計劃。
聯盟外交困難重重
實現碳中和的計劃是昂貴的,比如需要投資加固港口和海水淡化廠以適應島國已經看到的氣候變化。因此,動員金融投資是一個重點。小島嶼聯盟抱怨:“迄今為止一些發達國家并未兌現承諾的資金,很多項目的實施經常被繁文縟節束縛。我們希望一些發達國家作出重大承諾。”
盡管小島嶼聯盟的外交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們也面臨著一系列困難,因為要保持全世界的關注度并不容易。伯利茲曾努力說服世界各國領導人參加2019年9月27日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日”。
此外,世界對氣候變化的憤怒已經蔓延開來,其他國家也紛紛加入進來。對島國而言,氣候問題的關注范圍擴大是受歡迎的,但這意味著它們自己的領導人不再那么有發言權和權威性。
小島嶼聯盟在信息和戰略上基本保持統一,但其成員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方式不同,因此會產生分歧。
目前還不清楚小島嶼聯盟是否能贏得這場氣候外交的斗爭。
小島嶼國家聯盟在信息和戰略上基本保持統一,但其成員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方式不同,因此會產生分歧。目前還不清楚小島嶼國家聯盟是否能贏得這場氣候外交的斗爭。
從長遠來看,物種滅絕仍在向我們步步逼近,因為世界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做得太少了。一些人說,如果道德層面上的理由不成立,那么現在是采取新戰略的時候了,比如采用氣候工程等激進技術。
從樂觀的角度看,全世界對于環保的立法步入了新的階段。以中國為例,1978年《憲法》首次將環境保護納入國家的根本大法,之后1982年和2018年修改的《憲法》都相繼關注環境保護議題,特別是生態文明等環保議題入憲,正式表明中國進入“環境憲法”時代。迄今為止,世界上有148個國家的憲法涉及環境保護條款。這意味著在憲法層面,大家達成了一定的共識。
如果做不到這些,一些小島嶼國家可能要發起多項內容的談判,例如與擁有更多土地的國家就本國居民的移民問題進行談判,或就如何捍衛自己的領海權進行溝通。如果事已至此,那么小島嶼聯盟又回到了聯盟成立的原點——尋找律師助力。
編輯:夏春暉 38675320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