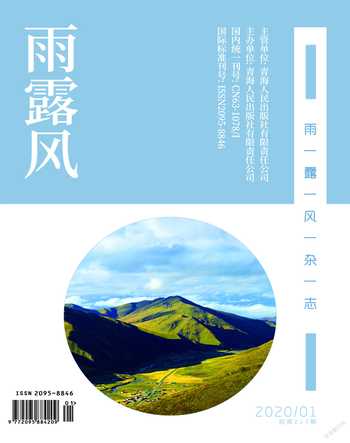《詩經》中“馬”的文學價值探究
任麗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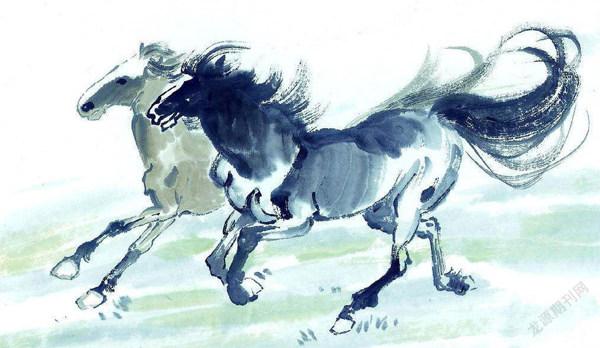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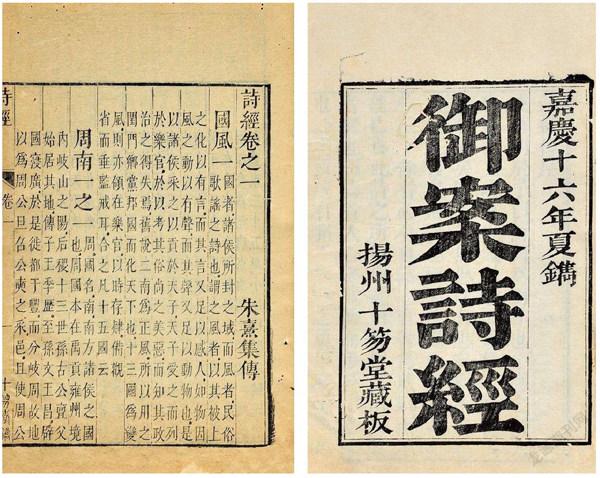
摘要:在周代的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的就是馬,而且其與人類的關系也最為密切。在《詩經》中,則將其作為某種價值事物被大量地反映了出來,而且實際的價值和意義也更具備獨特性。在《詩經》的一些篇章中,大部分人都會將馬應用進來,并且對人進行擬寫,而且借助馬達到抒情的效果,在實際的藝術表現手法中,不但起到了烘托的作用,還起到了比興的作用,而且不論是對大量的作品進行分析,還是對詩歌理論進行深入的探討,都可以發現馬本身的文學價值非常豐富,也為馬文化后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基于此,本文主要對《詩經》中“馬”的文學價值進行深入的探討和分析。
關鍵詞:詩經; “馬” ;文學價值
在古代,與人類關系最為親密的就是馬,而且其在很早的時期就已經被人類馴化。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非常重視馬,而且在西周時期就將“馬政”建立了進來,在當時,“馬政”是一項最不可或缺的政治制度。其中,《魯頌·駉》就是對馬政進行贊揚的詩篇,主要描述的就是負責馬政事物的官吏,統稱為“趣馬”,主要的職務是對馬匹的訓練和牧養等進行負責。在近代的考古中,還在殷墟侯家莊的商王陵墓以及山東淄博等地,發現了一定數量的葬馬坑,基于此可以進一步發現,在古代人們的生活中,馬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于周代而言,其還會舉行與馬有關的各種名目的祭祀,而且在當時馬是人們最為崇拜的對象之一,甚至馬本身已經達到了神化的程度。在《周禮.春官.校人》中,就有對祭馬儀式的描寫:“春祭馬祖,執駒;夏祭馬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藏撲;冬祭馬步,獻馬。”由此可以進一步發現,在不同的季節,均有祭馬的意識,而且實際的內容也各不相同。此外,在《小雅·吉日》中,也有與馬神祭祀相關的內容。正是在當時馬的地位如此高,才會將其作為最珍貴的禮品,饋贈給諸侯以及天子。由于在周代的社會生活中,馬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詩經》中才會頻繁地出現馬,而且在《詩經》中也將馬作為了最重要的內容,其對于人類本身而言,并非是一種已經被馴化的動物,而是具備非常重要的文化意義,并且在《詩經》中,馬的文學價值也是不可忽視的。
一、《詩經》中“馬”的表現形式
人們與馬之間不但有著密切的聯系,還有著喜愛之情,不僅如此,人們還極為重視馬,也正是基于此種背景,馬才可以在詩篇之中起到反應某種社會價值的意義,與此同時,還具備獨特的價值。在《詩經》中,馬的出現主要體現為以下兩種形式,首先,就是具備物象特征的馬。其主要是對周代社會中馬的作用進行了深入的描寫,例如日常生活、狩獵、戰爭等,而且對于馬本身而言,其具備功用性的價值;其次,就是具備意象特征的馬。在我國古代的詩歌藝術中,意象屬于應用廣泛的一個重要理論,而且出現的時間也非常早。在《易經·系辭》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而且經常用“象”來進行意的表達。在藝術的創作中,還要用“象”來表“神”,也就是說將具體的物象應用進來,對作者的思想情況進行表達。在《詩經》中,對于動植物的描寫非常多,孔子也曾有言,學詩的過程中,就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特別是在《詩經》中,其在對大量的動植物進行描寫的過程中,甚至已經達到了“擬人化”的程度,不但對人們的情感起到了承載的作用,還對人們的思想起到了表達的作用。而且對于當時階段而言,其已經認為一部分動植物就是意象,成為了人們自身情感的一種符號,食物更是成為比、興、賦的載體,比如桑、木瓜、魚等。而且在《美學十論·論美與自然》中,陳望衡表示:“人類對自然認識的第二個階段是‘比德階段。”由此可見,人們不再將以往物質功利的觀點應用進來,而是將自然物與人們的道德觀念和精神生活結合在一起,并且對自然物的自然屬性重視起來,將其對生活以及社會中一些美的存在進行比喻和象征。特別是在《詩經》中,其對于“比”“興”的應用量非常大,而且其中還有一部分“比”“興”的應用是對自然美進行了社會化的賦予。此外,普列漢諾夫也表示過:“以歷史的角度來分析,將有意識的觀點深入進來,對事物進來看待,通常情況下,是先于以審美的觀點來看待事物的。”而在當時階段,馬本身就具備實用價值的特點,在詩篇中被頻繁地寫入進來,而且基于作者的進一步審美轉換,將馬的豐富文學和美學價值全面地體現了出來。雖然在早期階段的《詩經》中,其存在嚴重的發育不成熟問題,而且實際的表現也非常粗糙,更有甚者,可以用模糊這一字眼來形容,但是對于實際的思想表達以及現有的構建而言,其獨特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詩經》表現形式中,最常用的三種方法就是“賦”“比”“興”,而且在運用這三種方法的過程中,都與“物”脫離不開關系,特別是“比”和“興”。此外,《詩經》之所以對賦、比、興進行大量的應用,其根本原因就是將某一種對應物作為基礎,進而將某種情感激發出來,并且通過作者的恰當取舍,將作者自身的感受與理解融入其中,進而在詩中將人們微妙和豐富的內心世界表現出來。在詩歌中,將一些“物”作為意象則是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詩經》中,一些與馬相關的比喻句,都存在描寫隱晦的特點,而且后人在對其意思進行闡釋的過程中,也各有不同。例如,在《小雅·角弓》中:“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后。”對于這句關于馬的描述,雖然歐陽修、鄭玄、朱熹等均認為其屬于取譬之句,但是實際的解說也是各不相同。歐陽修在《詩本義》中這樣表述:“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人在其后則辯是非。”鄭玄則有言:“喻幽王見老人,反悔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后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朱熹在《詩集傳》中表示:“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后,將由不勝任之患也。”
二、馬在《詩經》中具有烘托的作用
舉例來講,在《周南·卷耳》和《詩經原始》這兩篇中,方玉潤發表了這樣的看法:“此詩當是婦人念夫行役而憫其勞作之作。”在該詩中的第一篇屬于寫實,主要是對女子在采卷耳的過程中對遠行丈夫的思念之情進行直接的描述。在之后的二章、三章以及四章中,則改變了對自己懷念行人的直接敘述,以對方為出發點,對自身的思念之情進行想象。而且作者將一匹兵馬運用進來,將其作為意向,對自身的感情進行表述,例如,“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陟彼高崗, 我馬玄黃……。陟彼砠矣, 我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該詩將此種復沓的形式應用進來,不僅如此,還將層層遞進的形式應用進來,可以最大化地將自身的懷人之情表述出來,并且間接的表述了自身的憂傷之深,詩篇既婉轉又曲折,十分感人。此外,還有另外一篇思婦詩,即《小雅·杕杜》,其中有這樣一段描寫:“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主要通過破舊的車和疲病的馬來將自身的相思之情烘托出來。在戰國末年,屈原的《離騷》詩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即“仆夫悲余馬懷兮, 蜷局顧而不行”。其與此種表達方式極為相似,而且不論是仆,還是馬,都對故國有著迷戀之情,而其不愿意離去,從側面的方式將屈原的愛國之情烘托出來。此外,蔡琰有一詩篇,即《悲憤詩》有言:“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也是將車馬作為主要的意象,對自身的情思進行全面的烘托。而到了唐代,大部分詩人在進行創作的過程中,都會將馬形容為瘦、老、病,進而對自身的壓抑之情和難言之隱進行側面的烘托。杜甫曾有詩名為《病馬》,“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其中,對于馬的形象而言,其已經不僅僅是對氣氛的烘托,更多的是將人的一腔壯志不得展的自我畫像描述出來,對作者壯志蹉跎的郁憤進行抒發的同時,還將更加豐富的內涵賦予了進來,使馬的意象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
三、馬在戰爭詩篇中的烘托作用
對于馬這一動物而言,其在古代與戰爭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在《說文解字》一文中,東漢許慎就曾闡釋過,馬又可以解釋為“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不僅如此,在后漢書中,也有相應的闡釋,即“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 國之大用”。由此可以進一步發現,馬與戰爭的關系極為密切。在古代,對于一個國家強弱以及力量的衡量,除了對戎車的多寡進行看重以外,還要對戎馬的多少以及強弱進行看重。在戰爭中,馬是戰爭的工具,也正是因為此,才使馬的形象更加飽滿,將剛健豪邁之氣囊括了進來。在《詩經》中,有很多詩篇都是對戰爭的描寫,而且在描寫戰爭的過程中,都將馬的形象體現了出來,除了對馬在戰爭中的作用進行客觀的描述以外,馬本身還能起到對戰爭的烘托作用,因此,在實際的詩篇中,馬本身就具備了雙重的含義。
對于《小雅.·六月》這一詩篇而言,其主要就是贊美宣王時代尹吉甫北伐獫狁獲勝的一篇詩,而且整篇詩中,在獫狁興兵就進行了描寫,“獫狁孔熾,我是用急”。與此同時,宣王聞聲,則開啟了緊急備戰的模式,并且以車馬為喻進行描寫:“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骙骙,載是常服。……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在出征抗敵之前,必須重視戰馬的挑選,在挑選戰馬的過程中,必須將訓練成熟的戰馬選取進來,還要對毛色齊、雄壯的戰馬優先挑選,詩篇中則這樣表述:“四牡修廣,其大有颙。薄伐玁狁,以奏膚公。”而且在實際的戰爭過程中,也是以馬為主要的描寫對象,對于軍隊的實力和威武則以馬的高大健壯進行相應的烘托,不僅如此,在描寫戎馬倥傯的過程中,也是對統帥尹吉甫奔赴國難勇往直前的氣概進行了間接的烘托。
四、馬在狩獵篇中的作用
在周代社會生產勞動中,狩獵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而且通過相應的狩獵,人們可以獲得生活的來源,此外,當時的統治者還將其與娛樂結合在一起,進而演變為一種演武或者是練兵的活動,將制度化實施進來,使其成為誠征的“歲時常典”。在《詩經》中,其也屬于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例如,在《小雅·車攻》中,對周宣王的出獵進行了描述,而且還將諸侯匯集與東都。在該篇的前三章中,主要是對狩獵的準備工作進行描寫,即:“我車既攻, 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 田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不但將準備工作的充分性描述了出來,還以車盛馬壯為意象對懸望的赫赫聲威進行了側面的烘托。此外,還有“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其主要以馬行疾徐有致為依托,對諸侯在朝見的過程中絡繹不絕和井然有序的狀態進行烘托。此外,在田獵一章中,還有這樣的描寫:“四黃既駕, 兩驂不猗。不失其馳, 舍矢如破。”在前兩句中,主要是對四匹黃馬的并駕齊驅進行描述,而后兩句不但對騎馬人的高超射藝進行了精準的描寫,還對其百發百中猶如神人的齊射技藝進行了重點的表述。實際的藝術效果非常好,不但達到了人馬嫻習有度的程度,還達到了相互映襯的效果。在狩獵完成歸途的過程中,則有這樣一句膾炙人口的詩句,即“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根據該詞句,就可以進一步想象出當時的場景,馬聲蕭蕭,以馬聲為烘托將軍營的整肅側面地表現出來,而且達到了虛實并舉,情景相生的效果。在《歲寒堂詩話》中,張戎曾這樣表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此語非為創始之為難,乃中的之為工也。”不僅如此,當時非常有名的詩歌作家更是對“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兩句進行了大力的贊賞,稱之為“動中見靜,靜中見動”,此種手法堪稱為絕妙。在《詩經》中以“馬”為烘托意象進行相觀場景狀況的描述以及此等絕妙的描寫手法,還起到啟迪后世的作用,在唐朝時期,在《后出塞》中這樣描述,“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廖”。也是進一步受到了詩經的點化。而且近代著名作家錢鐘書也對其進行了大加贊賞,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正所謂詩人體物,早具會心。寂靜之幽深者,每以得聲音襯托而愈覺其深;虛空之遼遠者,每以有事物點綴而愈見其廣。”
五、結語
本文對《詩經》中“馬”的文學價值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詩經》這一偉大的作品中,最早出現的就是馬,而且在實際的詩篇中,馬不僅起到了比興的作用,還起到了重要的烘托作用。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對于馬而言,其本身的文化內涵也越來越豐富。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會將馬比作軍人,而且在進行詩篇敘寫的過程中,還會采取以馬喻人的手法,將自身的懷才不遇之情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不僅如此,在當時,馬還成為了人才價值的重要象征。到了春秋戰國交際之期,“馬”又實現了進一步的升級,上升到了人格的意義,孔子曾有言:“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與此同時,鄭玄則對其進行闡釋,曰:“德者調良之謂,謂有五御之威儀。”由此可見,在當時的孔子心中,馬已經不僅僅屬于自然界中的動物物種,而是一種人的象征,并且賦予了德才兼備的內涵。在《列子·說符》中,在對九方皋相馬進行講述的過程中,則提出了相應的道理,即“識人于牝牡驪黃之外”,而且在當時起到了發人深省的作用。在《戰國策·燕策一》中,也將郭隗不棄千里馬之骨全面地描述和體現了出來。到了魏晉時期,“馬”的意義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升級,而且其不再局限于對人才價值的象征,更多的是體現在文人墨客的筆下,將馬象征為英雄的精神。在眾多的詩篇中,以馬進行詠懷的詩篇不在少數,比如,劉義恭的《白馬賦》、郭璞的《馬贊》等。到了唐代,在這一時期所有的文人墨客都對馬有著極度的偏愛,與馬相關的詩篇也非常多,比如,韓愈的《馬說》、李白的《天馬歌》等。總的來講,在中國古代的文學中,馬有著非常豐富的文學價值,特別是在《詩經》中,對馬在不同的場景和不同的環境中均進行了深入的描寫,將馬的不同烘托作用全面表述出來,通過對《詩經》中“馬”的文學價值進行深入的探究,可以進一步了解到,在古代時期人們不僅將馬單單作為一種自然界的動物,而是賦予其更多的價值,給予其更多的尊重,而且在實際的詩篇中,將馬大量的應用進來,或是借馬對人的相思之情進行烘托,或是借馬對人的壯志難籌進行側面反映,又或是借馬對軍隊的肅然莊重進行反饋等,隨著時代的更迭和發展,馬在文學中的含義也在不斷的深化。
參考文獻:
〔1〕張細進.先秦時期“君子”意涵的三次轉變及其意義——以《尚書》《詩經》《論語》為中心[J].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34(5):105-111.
〔2〕鄭偉.“詩可以觀”與《詩經》的文學闡釋學——以歐陽修、蘇轍的詩經學為中心[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5):172-180,192.
〔3〕樹常青,劉春.《詩經》中文學與政治價值之抗禮——以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二《氓》選篇為例[J].語文建設,2018(26):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