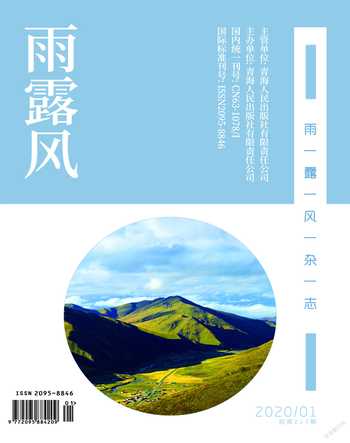屈原《九歌》對楚巫文化的傳承
彭俊華



摘要:屈原生長在南方,通過其作品,可以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楚巫文化,特別是在《九歌》這一作品中。其洋溢著非常濃厚的楚巫文化,而且不論是楚巫文化的形成,還是到后續的發展,都受到了殷商巫文化、江漢的土著文化以及“戎”“祀”文化的相應影響。而楚巫文化之所以形成,其最為關鍵的影響因素就是殷商巫文化,其不但對屈原《九歌》的精神面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還決定了其文化的特質;而《九歌》產生的重要土壤就是江漢土著盛行的巫風文化傳統,其對《九歌》的不同藝術特點起到了直接的影響作用;在春秋戰國時期,對祀文化非常重視,進而使屈原對于《九歌》的創作提供了更多的發展依據。基于此,本文主要針對屈原《九歌》對楚巫文化的傳承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關鍵詞:屈原 ;九歌; 楚巫文化
對于“巫”而言,其屬于一個概念,而且隸屬于宗教范疇,為人與神之間的溝通搭建了一座橋梁。對于當時處于南方地區的楚國而言,其存在著祭祀鬼神,而且達到了虔誠至極的程度,進而使一種巫文化得以形成。在屈原生活的時代,楚國不論是君臣,還是百姓,都“信巫覡,重淫祀”,而基于這種時代背景,屈原也受到了耳濡目染,因此,使其自身的形象思維方式和詩歌表現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在屈原的大腦深層中,不僅存在巫風習俗,還存在各種各樣的神話傳說,因此,在其進行創作的過程中,則不知不覺地被引入到詩詞中,在《九歌》就能感受到非常鮮明的楚巫文化特點。與此同時,《九歌》與巫文化的關系還牽涉到了文化傳承的問題。自東漢時期的《楚辭章句》,到清代時期王夫之的《楚辭通釋》,又到近代學者梁啟超先生的《屈原研究》,均對《九歌》與楚巫文化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如今,可以肯定的是,在屈原作品中,巫有著重要的地位,而且《九歌》對楚巫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傳承作用。
一、楚巫文化的來源
(一)先楚時期的巫文化
所謂先楚,就是指周王朝對殷商取代和楚君熊繹受封丹陽的一段時間。在當時的殷商時期,楚先祖對殷商文化進行了自覺的接受,而且與殷商之間的交往也非常密切,因此,對巫風習俗非常重視,進而對楚文化產生了嚴重且深遠的影響。
在研究楚巫文化來源的過程中,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楚族的來源,在如今的學術界中,對于楚族的來源一共有四種說法:第一種是殷商說,第二種是西來說,第三種是土著說,最后一種就是中原說。而對于不同的學說而言,其實際的側重點也各不相同,當然也有相互補充和結合的部分,但是當前認為最為可靠的就是殷商說。
楚部族在實際活動和發展的過程中,受到殷商文化的影響非常深。楚部族的活動范圍是中原地區,基于部族的不斷融合和進一步發展壯大,在夏末商初階段,商相繼滅掉了祝融部落的分支韋、顧、昆吾。而且在《詩經·商頌·長發》這一詩篇中,就將殷商對楚部族的征伐記錄了下來,“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在當時,由于受到商的威懾,羋姓季連部被迫南遷,并且與當時的土著民族融合在一起,一個新的民族得以誕生,在當時的商周文獻中,稱之為“荊楚”“荊蠻”“楚蠻”民族。而且自殷商王朝在整體的政權全部穩固之后,就對荊楚地區開展了大范圍的征伐戰爭。在《詩·商頌·殷武》這一詩篇中,則有相應的記錄:“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 其主要是對武丁時期,殷商對于荊楚地區開展的軍事戰爭。以軍事的角度來分析,軍事對殷商文化在楚地的傳播起到了促進的作用。而且根據現代的考古工作發現,最有利的證據就是在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發現的盤龍城遺址群。商代的早期城市遺址就是盤龍城遺址,其不但是迄今為止商王朝建立的最大軍事和政治據點,還有著非常濃厚的商文化作風,基于此可以進一步推斷,商文化的發達源地就是黃河流域,而且已經到達了長江之濱。根據考古出土的商代墓葬可以發現,青銅禮器非常多,由此可見,在當時的南方,曾經舉辦過規模非常大的宗教活動,而且對當時的居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于荊楚這一國家而言,其屬于被征服的國家,則勢必會受到殷商文化的影響。此外,對于楚與華夏而言,其不論是文字,還是語言,均屬于同一個系統,而且其與甲骨文字均一脈相承,也可以進一步說明,楚文化受到了殷商文化的重大影響。而在商文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巫文化,則其也勢必對楚文化產生了同樣的影響。
基于此,可以發現,對于楚族和殷商而言,這兩者之間的接觸具備頻繁性的特點,而在實際的戰爭中,殷商作為勝利者,則最不可避免的就是文化的輸出,而且在殷商的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巫史文化,因此,其對后來的楚巫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奠定基礎的作用。
(二)江漢土著文化與楚巫文化
楚族逐步遷徙到了江漢流域,在此之后,其不但與土著民族進行了文化的融合,還進行了政治的融合,進而將真正屬于自己的文化建立了起來。楚人興邦的地域正是江漢流域,而且其也是當時苗蠻集團的最中心位置,在當時經常與楚發生關系的土著民族主要有濮、越、巴、蠻等。其中,在《左傳·莊公十八年》和《左傳·莊公十九年》中,均將楚滅巴的事件記載了下來。基于軍事手段的實施,當時楚的領土范圍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到了楚武王時期,則已經出現了“始開濮地而有之”。基于這些記載可以進一步了解到,楚與土著之間進行著連年不斷的戰爭,想要征服對方,最終勝利者為楚人。但是楚在實際征戰和發展的過程中,也會受到土著文化的影響,最終實現了融合。當時的土著文化也盛行著巫文化,與中原地區相比,其對于“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習俗信奉則更為濃烈。
對于當時的巫風習俗而言,如今也有相應的保留。根據相應的調查可以發現,如今的苗人對人間禍福極為信奉,而且認為主宰的對象就是鬼神,因此非常畏懼鬼,對其表達敬重的同時,也會將相應的祭祀活動開展進來。對于苗人的這一習俗而言,其最為直接的影響來源就是楚人的習俗。對于當時的楚族,其具備對多神崇拜的特點,比如《東君》祭太陽神、《山鬼》祭鬼神、《云中君》祭云神,而對于如今的苗族而言,其不但存在《燒湯撈油巫詞》,還存在《榜媧歌》,均是當時楚族習俗的傳承,而且充滿了崇神的浪漫主義氛圍,與此同時,其也正是《九歌》的格調。
由此可見,楚文化受到了江漢土著巫文化非常深的浸染,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苗族的巫教文化就是當時楚巫文化的源流。
(三)“戎”“祀”文化與楚巫文化
在《左傳·成公十三年》中,有這樣的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由此可以證明,在當時的整個國家生活中,戰爭與祭祀活動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以當時的習俗為主要依據,在開展大型的軍事活動之前,都要進行相應的占卜,其主要目的就是將這一方式產生的心理暗示作用利用進來,使將士的戰斗力得以增強。在當時社會,不論是祭祀,還是相應的卜筮,均由巫覡主持,進而進行相應活動的開展,因此,巫覡的地位非常高。其中,在《國語·楚語下》中就有言:“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 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 未償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又有左史倚相,……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在當時的楚國,觀射父以及左史倚的地位就非常高,就連當時的楚王也時常向觀射父請教。而且當時的觀射父還這樣評價過巫咸:“古者民神不雜。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 其智能上下比義,其圣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 如是則明神降之, 在男曰覡 , 在女曰巫。”由此可見,在當時的楚人心中,巫咸的地位極高。
基于此可以發現,楚族之所以對巫極為重視,就是受到了三方面的直接影響,即殷商巫文化、江漢土著巫文化、先秦時“戎”“祀”文化。而且對于當時的楚巫文化而言,其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文學作品,而且正是源于此,才使得當時的楚文學呈現了與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色彩。
二、《九歌》對楚巫文化的傳承
(一)原始《九歌》與巫文化
(1)原始九歌的娛樂性
對于原始《九歌》而言,其具備娛樂性的特點。而且在《離騷》中,就可以看出來,“啟 《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娛樂。陟升皇之赫戲兮, 忽臨睨夫舊鄉”。戴震注:“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由此可見,在當時,夏啟的淫樂工具就是《九歌》,而也正是由于其過于沉湎其中,才將五子之亂引出來,最終以亡國而告終。而且在當時夏啟在對“萬舞”進行觀看的過程中,會聽《九歌》,由此可見,《九歌》娛樂性應該是非常強,而且實際的內容也相對荒淫。
基于以上材料,可以進一步發現,《九歌》本身具備極強的娛樂性質,對于此種娛樂而言,其本身并非是對個人的娛樂,而是對神祗的娛樂,其主要緣由就是在以往的上古祭祀過程中,都會將娛神的音樂歌舞利用進來,進而達到娛人的目的,而對于這兩者而言,其并無任何本質性的區別。對于上古的“葛天氏之樂”就將巫與巫術的活動包含了進來。而且當時的農民在求神賜農業豐收的過程中,也會將相應的舞蹈和音樂形式的巫術利用進來,進而達到娛神的目的。對于此種音樂而言,不但可以娛人又可以娛神,因此,當時的夏啟用來進行自娛的歌舞也具備娛神的作用,而且在當時極有可能就是祭歌。
(2)原始《九歌》的祭祀性
《九歌》具備祭祀性的特點。在《山海經》中,有言:“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郭璞注曰:“ 嬪,婦也 ,言獻美婦于天帝。”《天問》中也言“啟 棘 賓 商 ,《九辯》《九歌》。” 陳子展認為:“夏啟趕忙上獻三美人給天帝,得到了上天的音樂《九辯》和《九歌》。”諸如此類的以美女對太平進行換取的事例在后世中的遺留也并不少。對于此種風俗而言,也就是如今人們常說的“人牲”,在當時屬于一種祭祀行為,而且非常典型。
在當時的楚族,巫的職務就是巫祝占卜一類的工作,因此,人主與巫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針對此問題,陳夢家先生曾有過相應的論述:“由巫而史,而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雖為政治領袖,同時仍為群巫之長。”而且在《中國青銅時代》中,張光直也曾有過這樣的言論,其認為,對于夏侯啟本身而言,其雖然身份為人主,但是兼有著大巫的身份,而且在很多傳世的文獻中,都有相應的描述,即楚王本身就兼具了巫覡身份。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進一步斷定,對于夏的《九歌》而言,其在當時勢必屬于一場祭祀活動,而且由其本身親啟。對于實際的《九歌》祭祀方式以及內容,如今已經無法進行相應的考究和正式,只能通過一些間接的線索進行推斷,即在《竹書紀年》中有言:“(帝啟)九年,舞九韶。”基于此可以展開想象,在古代,對于此種類型的音樂鼓舞場面而言,其具備公開性和大規模的特點,因此,實際的氛圍熱鬧非凡,而古代在開展娛樂活動的過程中,也會將其與宗教結合在一起,因此,夏啟對歌舞進行大規模公開舉行的過程中,也會將隆重的祀典開展進來,達到同時進行的目的。而且聞一多曾有言:“啟曾奏此樂以享上帝,即所謂鈞臺之享。正如一般原始社會的音樂,這樂舞的內容 頗為猥褻。 只因原始生活中,宗教與性愛頗不易分,所以雖猥褻而仍不妨為享神的樂。”由此可見,對于《九歌》而言,其最初就是祭歌,不但起到了自娛和娛神的作用,還具備狂歡的特性。
(二)巫文化對屈原《九歌》的影響
(1)屈原《九歌》的性質
就《九歌》而言,歷史以來爭議最多的就是“性質”,主要有四種觀點:首先是寄興說;其次是民間祭歌說;接著是國家祭典說;最后一種就是人身戀愛說。因此,《九歌》的性質則難以定論。《九歌》本身與祭祀相關,但是具體祭祀的種類則存在著一定的爭論,筆者認為最為可信的就是國家祭典說。在《九歌》中,除了將《禮魂》拋除在外,在對其他的神祗進行祭祀的過程中,不是天神,就是地祗,又或者是人鬼。其中,天神有《大司命》《少司命》《東皇太一》等;地祗有《河伯》《湘夫人》等;人鬼則有《國殤》。從本質的角度來分析,在對地祗進行祭祀的過程中,就是祭祀山川,此外,對于相應的天神和地祗的祭祀則屬于天子的祭祀禮治,而并非屬于平民的祭祀。由此可見,對于《九歌》而言,其主要的祭祀對象就是國家祭典。
(2)巫文化視野下的屈原《九歌》
第一點就是祭祀對象。周王朝在開展國家祭祀的過程中,以嚴格的禮儀制度為依托,而且具備非常明確的功利性,其開展祭祀的目的就是為了對某種利益進行獲取,或者是想要達成某種目的。而且在當時的周王朝,其在祭神的過程中,最主要的就是對于祖先、神進行祭祀,根本原因是其與江山社稷息息相關,而且實際的宗旨就是為了使后人得到教化和激勵。此外,對于《九歌》中祭祀的神祗而言,其本身就具備巫覡色彩,而且十分濃厚。正是由于巫文化,才使屈原的創作題材進一步受到了影響,而且在大部分的屈賦中都可以看到神靈意識隱藏其中,比如在《離騷》和《招魂》中,就引入很多與巫有關的人物,不僅如此,還引入了一些地名和怪物,如羲和、應龍、河伯等。
其次,就是迎神的方式。對于《九歌》的祭祀場面而言,其遍布的是香草氣息,詩人屈原為了對神祗的到來進行迎接,則將一個芳香四溢的環境營造了出來。比如在《湘夫人》中有這樣的描述:“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 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為帷, 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由此可見,不論是整個房屋,還是整個庭院,均由香草支撐,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才能對神祗進行迎接。
最后,就是娛神的方式。在《說文解字》中,許慎曾釋“巫”為“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 者也 , 象人兩袖舞形”。其對巫的本事和神樂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明確的闡釋,即其與神祗之間交往的手段之一就是音樂。經考古證明,在殷墟中出土的甲骨文中,“舞”與“巫”屬于同一個字,歌舞是最為古老的一種娛神方式,不論是當時的楚地,還是中原,都將其作為最主要的娛神方式,而且由心而發的重要情感表現就是舞蹈。
三、結語
根據以上論述,可以進一步發現,對于《九歌》最初的性質而言,證明了其就是巫文化最重要的根基,雖然到了周代出現了相應的轉變,但是對于整個楚國的文化氛圍而言,《九歌》對于文化的傳承則是以原來的方式為依據,進而進行生長,不論是其祭祀的方式,還是其祭祀的對象,都受到了巫文化的深刻影響。
參考文獻:
〔1〕徐雅卓,萬紹芳.針對屈原作品《九歌》在民間影響的研究[J].黃河之聲,2020(16):24-25.
〔2〕吳欲曉. 《九歌》中的巫文化研究[D].湖北工業大學,2020.
〔3〕張雅.《九歌·云中君》究竟是誰?[J].中國圖書評論,2020(6):78-84.